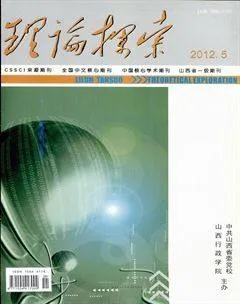关于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法律规制
2012-01-01吴胜利
理论探索 2012年5期
〔摘要〕 当前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面临补偿目的不明确、补偿相关主体难以确定、补偿标准不统一、监管乏力的困境。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在于现有研究无法为实践提供正当性基础、未考量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对地力提升的重要意义、漠视基本农田保护补偿中的国家责任。为此,应从明确补偿目的、充分考量补偿的经济激励功能、凸显补偿的国家责任、维护直接从事基本农田保护者的合法权益、健全监管机制等方面完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 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困境,原因,完善
〔中图分类号〕D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5-0125-04
基本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保护基本农田对于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维护农业生态以及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土地管理法、农业法规定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国务院依据土地管理法的授权专门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范基本农田的划定、保护、监督管理行为。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基本农田保护提出了两个全新理念,其一是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其二是建立保护补偿机制,以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各地积极推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对基本农田保护行为进行补偿。与实践的积极推动相比,基本农田保护补偿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现有研究对其存在的困境明显缺乏关注,笔者以“基本农田保护补偿”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仅搜索到6篇相关文献,现有研究显然无法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面临的困境,探究法律规制面临困境的原因,最后提出完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的思路。
一、当前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面临的困境
(一)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目的不明确。2008年以来,国家一直在积极推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建立保护补偿机制。但当下关于基本农田保护的补偿目的仍存纷争。汕头市《基本农田保护补贴资金暂行管理办法(暂行)》规定补偿的目的在于平衡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间的巨大利益差距,以此增加农民收入,激励农民保护基本农田,保障粮食安全;广州市《基本农田保护补贴资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补偿的目的是要落实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从而形成基本农田保护的激励机制;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保护补偿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耕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这些地方性规范文件来看,其规定的补偿目的过于笼统,并未认清基本农田保护与一般耕地保护的本质区别,使法律制度构造缺乏科学性与可行性,必然导致补偿效果欠佳,徒费纳税人资财。
(二)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相关主体难以确定。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相关主体可分为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基于基本农田在维护农业生态和粮食安全的功能,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负有补偿的义务。但具体承担补偿义务的主体为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并不确定。实践中,地方政府负担全部补偿资金的方式对于基本农田保有量较多的地方政府无疑会增加其财政负担。而从受偿主体来看,补偿给集体经济组织抑或承包经营权人,亦难以确定。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后,确定适格的受偿主体则会更加困难。
(三)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标准不统一。现行各地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标准并不统一,成都市规定对于一般耕地保护补偿金额是每年每亩300元,基本农田保护补偿金额为每年每亩400元;广州市规定根据地域不同分为每亩每年500元、350元和200元;汕头市规定的补偿标准较低,每年每亩仅30元,同时,规定补偿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每3年原则上调整一次;佛山市《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实施办法》规定不同地区设定每亩每年500元、200元等不同标准,并与汕头市要求相同,需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每3年原则上调整一次。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标准应在激励农户保护基本农田的积极性与不对政府财政构成过重的负担之间寻求平衡,补偿标准的不统一,造成受偿主体之间的不公平,十分不利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
(四)对基本农田保护监管乏力。实践中对于基本农田保护行为的监管,受偿主体一般要与补偿主体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但所谓的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往往是一种软约束,受偿主体履行基本农田保护义务的行为难以监督。众多分散的农户是否在维护基本农田的质量,在有限的执法资源之下,执法部门面临沉重的执法负担,导致执法部门实际上根本无力监管基本农田保护行为。基本农田补偿发放之后,受偿主体是否按照法定和约定的义务履行基本农田保护义务,亟需健全基本农田保护监管机制。
二、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现有研究无法为实践提供正当性基础。基本农田补偿目的的研究在于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有意义的导向,有学者认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属于对土地发展权的限制,基于此种限制应给予农户补偿。〔1 〕 (P104 )此观点可称之为“土地发展权受限说”。有学者则认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土地权利人丧失土地开发机会,承受本应由全社会承担的土地开发机会丧失的成本,构成管制征收,土地权利人因其“特别牺牲” 应有权获得额外的公平补偿。〔2 〕 (P77 )此观点可称之为“管制征收说”。此两种观点显然皆无法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实践提供正当性基础。
主张“土地发展权受限制说”的学者注意到我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利用土地的行为受到限制,但我国的农用地是否存在所谓的“土地发展权”?如果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并不存在土地发展权,何谈土地发展权的限制。一般认为,土地发展权指的是土地所有权人发展或开发土地的权利,是为保护农用地、环境敏感地区而实施的政策性工具。〔3 〕 (P133 )但在我国土地使用权利生成之时,权利人并没有取得所谓的改变土地用途以获取更大收益的权利,一旦土地规划之后即产生权利内涵明确的土地使用权,权利本身界限已经明确。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仅取得该幅地块当时的法定使用类别、强度的权利,并未包括未来变更使用的土地发展权及其所带来的发展价值。〔4 〕 (P2-35 )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皆不可能改变土地的使用用途。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土地权利人并不享有土地发展权,更谈不上对土地发展权的限制,“土地发展权受限说”无法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提供正当性基础。
农用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限制是否超出特别的界限而构成“特别牺牲”,达致与“征收”同样的效果,从而构成“管制征收”?美国经过司法判例逐步发展的管制征收理论认为如对不动产的管制已达到类似征收的效果应考量是否予以补偿。管制性征收理论认为必须衡量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衡量的本质是评估公共利益和加诸财产所有权人的负担,具体可以分为四点:管制性的法律是否为了合法的公共利益,此种法律是否合理地促进此项公共利益,加诸财产所有人的负担是否过大,此种负担是否不成比例。〔5 〕 (P159-167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7条第2款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是否使权利人承担远超过农用地社会义务的负担,有否侵害农户的经营自主权?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条和2007年颁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可知农用地根据土地的地形、灌溉设施等情形,具有不同的农业用途,基本农田作为耕地中的精华应在其上种植农作物,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应在林地、园地和养殖水面上进行,方符合土地的最佳利用。因此,对基本农田施加的限制并没有超出社会容忍的限度,本身属于基本农田社会义务范围之内,并不会构成所谓的“管制征收”。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的“永久”是否会达到过度的限制呢?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2条规定,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不会影响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即使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并不会对土地权利人造成不可容忍的负担,不构成“管制征收”。 “管制征收说”显然同样无法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实践提供正当性基础。
(二)未考量基本农田保护补偿对地力提升的重要价值。基于基本农田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国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对基本农田保护法律规制的方式,主要包括通过规划确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严格保护,将基本农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的一项内容,并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对基本农田的转用和征地审批不考虑数量多少一律由国务院批准;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地方,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与下一级人民政府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通过层层目标责任分解,明确具体的保护主体。《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还设定禁止性行为规范,严格禁止在基本农田之上进行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通过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监督检查机制,收集基本农田保护的信息。但总体而言,现行立法仅注重从基本农田数量的维持上保护基本农田,而对基本农田地力的提升这一攸关基本农田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的因素熟视无睹。从法律实施来看,我国土地法律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重要问题,一是建设行为违法占用耕地,另一个就是耕地地力下降,两个问题对粮食安全皆会带来极大威胁。城市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现象是建设行为不断挤占农业用地的空间,在耕地数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确保耕地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确保耕地数量可保障粮食安全,通过不断提高基本农田的地力,保障耕地的质量,同样亦可保障粮食安全。现行基本农田保护法律对于基本农田地力的提升缺乏规范,必然导致在受偿主体的确定、补偿标准以及基本农田保护行为的监管等方面出现困境。
(三)忽视基本农田保护补偿中的国家责任。基本农田保护补偿不是政府的恩惠,而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基本农田保护所负载的利益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之外,更多的是其产生的农业生态利益和维护粮食安全的社会利益,此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全社会所享有,而作为利益的生产者的农民并未从利益享受者处获得其应支付的对价,形成正外部性。对于正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一般认为有征税和补偿,对基本农田保护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征税并不适用,因此,对承担保护基本农田的农民进行补偿是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合理途径。从基本农田保护中获得利益的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不可能与作为利益生产者的农民达成补偿协议,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应负有补偿农民因产生农业生态利益和社会安全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在具体补偿主体的确定上,不可把补偿的责任全部推至地方政府,基本农田保护是全社会的义务,若仅由地方政府承担补偿责任,势必造成拥有基本农田数量较多的粮食主产区为其他拥有基本农田数量较少的经济较发达地区承担责任,形成区域间的不公平。忽视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国家责任必然导致补偿主体难以确定、补偿资金投入不足,难以形成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长效机制。
三、完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法律规制
基于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所面临的困境,“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修改时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制度,以推动永久基本保护区划定工作,实现基本农田保护的目标。
(一)明确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目的在于提升基本农田的地力。耶林指出“目的是整个法律的创造者,并不存在不源于目的(即一个实际动机)的法律规则。” 〔6 〕 (P54 )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既不是对农民土地发展权限制的补偿,也并未因为过度管制基本农田利用行为而构成“管制征收”。以“土地发展权限制”和“管制征收”作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目的的实质是以私人土地所有权的保障作为基点,而进行法律制度的构造,与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国情并不相符。因此,若盲目引进以私人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西方经验,不仅忽视了我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必然会导致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范在行为调整上的困境。以地力提升作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目的,有利于塑造基本农田保护的长效机制。依此目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法律制度构建应以地力提升为价值目标,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亦应以地力提升程度作为考量因素。
(二)充分考量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经济激励功能。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是对农户所为保护基本农田公益行为的利益诱导,内含有经济激励功能。利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克认为,“立法者必须探究、关照及评价需要规范的生活关系及利益冲突,这些探究、关照及评价在每个规范都不相同,因为它取决于不同的利益状态。我们应该去寻找个别的利益,并且认识到是何种冲突处于对立状态,这可以说是一种信息搜集工作。” 〔7 〕 (P251 )基本农田上负载有农民的生产利益,通过在基本农田之上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有物质基础;基本农田之上亦负载有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其中既包括每一个人获得粮食安全的保障,也包括良好的农业生态、优美的农业景观等。一方面,农业生产中农民维护基本农田地力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如果农民过度追求自己的生产利益,一味削弱地力,将有损公共利益。认识到农户的行为选择与公共利益实现密不可分,就涉及到如何选择规制农户行为的手段问题。在命令式和激励式手段之间,命令式手段在规制农户维护地力行为方面效果不佳。因为对于基本农田质量的保护不但要求农户消极的不为,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励农户积极的为。因此,应充分考量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这一利益诱导机制,激励农户选择提升地力,从而更好的实现公共利益。
(三)凸显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国家责任。基本农田保护产生的农业生态利益和粮食安全利益受益者为全社会,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承担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补偿责任。补偿不是政府对农民的恩惠,而是农民基于其提升基本农田地力的行为而应享受的合法权益。中央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应将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金投入列入预算科目,保障补偿资金的来源。国家还应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金的增长机制,以使基本农田保护者获得的补偿资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增长。中央政府承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金投入的主要部分,地方政府应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相应的比例投入到基本农田保护基金,以调动地方保护基本农田的积极性。
(四)维护直接从事基本农田保护者的合法权益。依据地力提升理论,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受偿主体应是切实有助地力提升的基本农田保护者。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负有基本农田保护职责的主体包括地方人民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承包基本农田的农户。首先,地方人民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承担的为法定的行政职责,其不得放弃保护基本农田的行政职责,否则会构成行政失职,地方人民政府不可能作为受偿主体,而应是补偿主体。其次,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本农田的发包主体,对基本农田保护具有管理职责,但在家庭承包经营制下,基本农田一般已经发包至本集体成员,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将其作为受偿主体激励效果不彰,无法实现地力提升的补偿目的。最后,承包基本农田的农户直接在基本农田之上从事农业生产,是基本农田地力的“养护者”和农业生态利益和粮食安全利益的生产者,而农户从农业生产中所获的收益与由其生产的为全社会所享有的利益相比存在巨大利益差距。因此,应将其作为受偿主体,维护直接从事基本农田保护者的合法权益。
(五)健全完善的基本农田保护监管机制。基本农田补偿发放之后,必须通过完善的监管机制,监督农户在基本农田之上所为的农业生产行为有利于地力提升。首先,完善基本农田地力分等定级制度和地力档案制度,根据地力分等定级情况确定补偿标准,相同地力等级应统一补偿发放标准。其次,应在现行受偿主体与补偿主体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的基础上,设计完善的基本农田保护合同条款,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依据地力分等定级标准,明示受偿主体所承包地块缔约之时的具体质量等级并约定补偿期间应达到的质量等级。最后,建立地力等级抽查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受偿主体的地力提升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对未达到基本农田保护合同约定地力等级的农户,要求其限期治理,治理期间内暂停补偿发放,若经治理仍难以符合地力等级标准的农户取消其基本农田保护补偿资格。
参考文献:
〔1〕蔡银莺,张安录.规划管制下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研究综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7).
〔2〕杨 惠,熊 晖.农用地管制中的财产权保障——从外部效益分享看农用地激励性管制〔J〕.现代法学,2008,(3).
〔3〕John C. Danner. TDRs——great idea but questionable value〔J〕.The Appraisal Journal,1997,(4).
〔4〕许文昌,等.土地政策〔M〕.台北: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
〔5〕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Rudolf Von Jhering.Law as a means to an end〔M〕.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1999.
〔7〕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