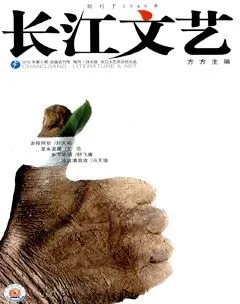冷议清宫戏
2012-01-01冯天瑜
长江文艺 2012年5期
近些年来,只要打开电视机,几十个频道里呈现的画面,大约有三成是“古装剧”,虽然偶有《大汉天子》等较古远题材的,更多的则是演绎清代宫廷故事的剧目,其中大约又可分为两类:一为“戏说”,如“戏说康熙”、“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还珠格格》均属此类;二为“正剧”,先后在中央一台播出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演员阵容强大,摄制精致,收视率颇高,为此类代表。我基本不看《戏说乾隆》、《还珠格格》之类“戏说”,但《雍》、《康》两剧却兴味盎然地看下来,原因是焦晃、唐国强、陈道明等的演技和导演叙述故事的能力,均颇有可观之处。然而,两剧欣赏下来,心中的沉重感却又挥之不去。
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前台人物和关键人物,故历史题材的剧目较多表现他们,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表现什么,如何表现?这关系到历史剧在提供娱乐的同时,给我们的观众留下怎样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
有些影视作者宣称,他们的使命是为大众提供娱乐,博观者一笑,收视率上去足矣,进行历史教化非所计也。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老百姓的历史知识乃至历史观往往来自戏曲和讲史小说,因此“讲史”的影视作品总会给老百姓提供或正或误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这不是影视作者宣称没有教化职责就可以搪塞过去的。而大众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的实际状态,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想象,在一个弥漫着中古式历史观的民族那里,能够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文明。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教化功能,是无可推卸的。
笔者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有时步行在珞珈山盘山道也会遭遇路人提出这样一类问题:康熙收复台湾时,郑成功之子郑经真的坚拒清军,阵前自杀了吗?纪晓岚真的与和■斗了半辈子吗?显然,这些问题是电视剧误导所致(如《康熙王朝》写郑经在施琅舰队抵台时割颈而死,《铁齿铜牙纪晓岚》大篇幅铺陈纪晓岚与和■的“正义斗争”)。非史学专业的大学教师尚且被电视剧弄得真伪莫辨,更不用说此类情节会被一般民众当作“史实”加以接受了。而真实的史实是,清朝收复台湾时,郑经早已亡故,郑经之子郑克爽降清,并接受清廷的册封;纪晓岚并非和■的政敌,终生与和■关系良好,纪氏的主要功绩是修纂《四库全书》,主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一代文宗,并非耍嘴皮的东方朔式滑稽人物。朋友们听我解释后,笑称电视剧“瞎编”!我想,历史剧并非历史学著作,“编”,或称艺术虚构,是允许而且必须的,但史剧情节不一定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却必须是可能发生的,即必须符合特定的历史环境提供的可能性,否则便是“瞎编”。上述两例都属“瞎编”之列。我以为,《康熙王朝》关于郑经自尽以拒施琅收复台湾的虚构,不仅完全违背史实,而且其引申含义也很不合适。
此外,史剧对话中的知识性错误更不胜枚举,如将皇帝、皇后、太后死去方追赠的谥号、庙号用在生前,如反映唐代生活的电视剧中,李世民在世时,臣子称其“太宗皇帝”;反映清代生活的电视剧中,清顺治帝的母亲自称“我孝庄”,剧中人物也口口声声称这位在世的太后为“孝庄太后”。若这些人物地下有知,真笑掉大牙。“奉天承运”是明太祖时方开始使用的诏书用语,而在表现汉、唐、宋的史剧中一再滥用。
当然,历史知识失准,还不是当下史剧存在的主要问题,历史观念陷于偏误,才是症结之所在,这集中表现在对专制君主的评价上。
中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度早成而又晚退的国度,自秦汉至明清,专制君主政治一以贯之,长达两千余年,而西欧诸国只在中世纪晚期才确立君主专制,历时不过二、三百年。中国的专制帝制的历史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曾经发挥过维系国家统一,发展经济、文化的积极作用。中国古文明的辉煌,从广土众民国家的建立,万里长城的兴筑、南北大运河的开掘,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修纂,都是专制君主制度的产物,因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永乐康熙们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的英俊人物,表现这些英俊人物的历史勋业,当然是史剧的任务。不过也不可忽略,那些文治武功是依凭亿万生民的智慧与血汗方得以构建的。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政治从诞生之日起,便有压抑人民基本权益(包括精神自由)的罪孽,秦皇汉武既是英主,又是暴君;此外,专制君主政治还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如果说,专制帝制在其前期较多发挥过历史进步作用,那么,随着时代推移,其阻滞历史进步的惰力则愈益彰显。而时下大量涌现的清宫戏,恰恰表现的是专制君主政治晚期的情景。下面以《雍正王朝》为例,剖析某些清宫戏描写晚期专制君主政治所显露的历史观。
《雍正王朝》通篇为一位专制帝王作全面辩护,与民本、民主的时代精神走向相去甚远。本来,雍正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堪称典型的专制帝王,无论就其励精图治、雄才大略,还是就其阴鸷可怖、深文周纳而言,都是一个值得书写的人物,透过这个人物,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距今并不遥远的专制帝制的种种内幕,了解雍正豪强、隐忍而又残暴、刚愎的性格,进而揭示这种性格的制度性根源和文化土壤,是颇有历史认识价值和现实启示意味的。应当说,《雍正王朝》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其艺术水平在今日中国艺坛均属一流,全剧起承转合,丝丝入扣,故这部电视连续剧确乎好看,据说其热播时万人空巷。但遗憾的是,这部近年少有的好看的历史巨片,其题旨却是为雍正“洗冤”,全片用力于驳斥以往传说的种种关于雍正“篡位”故事。我并不认为清中叶以来流传的那些雍正“篡位”故事都是可信的,这些故事本来便是专制帝制体系内部斗争的衍生物,争辩的无非是继位的“正统”性,对这些故事加以适度辨正,无论就史学研究还是就文学创作而言都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雍正王朝》以反驳雍正“篡位”作主线,将同情心倾注在雍正身上,如此一路演绎下来,“驳正”后的雍正便被塑造成一个正大光明、深得民心的“明君”,不仅得位甚正,而且几乎成了民意总代表,正如《雍正王朝》主题歌反复吟唱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此表现清朝最为专制、残暴的皇帝,恰当吗?须知,清朝是专制君主集权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朝代,是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走势的直接对立面。
人文精神的弘扬,并非一定要靠现代题材的作品来实现。其实,现代题材的作品也可能悖逆于时代趋势,历史题材作品则不乏伸张人文精神的良例。如那些富于人民性的,对宗法专制力加揭露、谴责的历史题材作品,便洋溢着人文精神。《海瑞罢官》、《狱卒平冤》、《徐九经升官记》、《张居正》等作品作过有益的尝试。以长篇小说《张居正》为例,它通过描写明朝万历年间一位改革家起伏跌宕的人生,揭示宗法专制时代的本质特性。作品展示张居正改革的成就及其限定性,张居正被万历皇帝掘墓焚尸的悲剧性结局,都是时代的产物、制度的产物。这部小说的人物、题材是历史的,因其对宗法专制帝制取深刻的历史批判态度,故而作品的价值取向是现代性的。惜乎,这样的好作品,往往被众多的正说、戏说宫廷戏所淹没,那种充满中古式情趣的高分贝喧哗,使得我们的历史剧领域呈现一种人文精神隐而不彰的局面,实在令人遗憾。
自秦汉以降,总的趋势是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愈演愈烈,至明清则达到登峰造极程度。明太祖朱元璋废除沿袭千余年的丞相制,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成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集政、军、财、文大权于一身。清承明制,发展了明代的绝对皇权,又强化了严酷的民族压迫。这种帝王的的集权专制,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日本中世、近世的天皇不掌实际政权,地位类似欧洲的天主教教皇,实权在征夷大将军手里,这也是天皇能够“万世一系”的原因所在。欧洲中世纪,政权与神权是分治的,前者归国王,后者属教会,欧洲谣谚云“上帝的归上帝管,恺撒的归恺撒管”,即说的欧洲的政教分离,思想文化大权游离于王权之外。即使在中世纪晚期王权极盛之际,掌管神权的教会对君主仍有相当强大的制约力,王权须获神权认可,帝王必须经由教皇加冕才获得合法性,加之中世纪晚期市民社会的崛起,欧洲的专制王权是颇有限度的。欧洲的著名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哥廷根等)创办于中世纪后期,均自外于王权,由此形成学术独立的传统。中国则不然,皇帝在教主之上(由皇帝向宗教首领颁金册),又通过科举考试,皇帝成了天下士子的老师(殿试便是士人直接到帝王面前应试)。皇帝集政权、神权(或称文权、思想权)于一身,这使得中国的专制帝制失去有效的制约机制,其为祸社会的一面便无法阻遏。明末的矿监、税监对工商业的巨大破坏,清代康、雍、乾盛世发生的令人毛骨耸然的文字狱,便是明例。这些都应当是史剧表现并力加批判的关键点。
至于中外皇室内部斗争(特别是围绕继统展开的争夺),更充满了阴谋与血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李尔王》对此作了深刻的谴责,使人文精神得以高扬。我们应当循莎翁故迹前行,决不要从莎翁那里倒退,对专制帝王作自然主义的描述,乃至流露出对极权与富贵的欣赏、赞颂。
在清宫戏“热播”之际,略陈以上“冷议”,供当事者参考。
责任编辑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