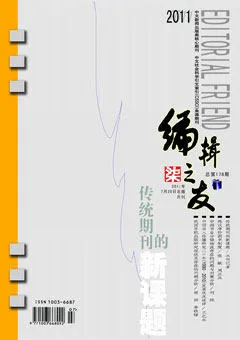日日新的一课
2011-12-31吕晓东
编辑之友 2011年7期
有人说做编辑是带着薪水去进修,是天下最美的职业。多年的编辑生活确实让我感到日日新的进步。那是五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像往常一样伏案编稿,任火老师的一篇《关注陌生》(见《编辑之友》2011年第6期)让我兴奋不已,编辑希望看到那种“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的稿件,更向往那种人人心中也很少意识到的内容,任老师的文章就属于这类。在他流畅的语言中,职业的“敏感”让我发现其中两处句式用词上需要斟酌,一处是“我们是否可以说编辑审稿其实就是一种‘拿不准审稿’呢?”另一处是“那些具有真正价值的学术理论、观点,出现在编辑面前的时候,都是一副陌生的面孔”。我挑刺地认为这样表达太绝对,不符合实情,是否可以改为或然判断,如两处文字中“其实就是”和“都是”可否改为“多是”或诸如此类的限制性词语,如第二处这样表达:“那些具有真正价值的学术理论、观点,出现在编辑面前的时候,多是一副陌生的面孔”是否更客观?
我满怀信心地打电话与任老师交流,任老师听后很高兴,出于对编辑的尊重,马上肯定了我的建议,还将文中的肯定表达改为“在很大程度上”;并大大表扬了我。由此话题,他感慨地诉说了作为作者的苦恼:在他的《编辑独语》中有安造计先生的《任火是一只鸟儿》,其中有一句“在正午的喧嚣中很难听懂他的旋律,只有在尘埃落定的空山雨后,净心侧耳,才能听懂高山流水般的丁冬激越”,不想编辑将“净心侧耳”改为“静心侧耳”,意味大变,作者要表达的那种虔诚、纯净之感消失了,作者潜心锤炼的文眼也因此被堵塞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苦心,古人令人无异。
任火老师曾满怀热情地写过一篇对地方性文献资料的评论,没想到发表出来后,编辑保留了他对文献的阐释,却删去了一段他与此地的渊源,这让他感到很难受,那段文字不长,但是一段心语。剪去了它,就剪去了作者的情感,剪断了文章的气脉。“那篇文章我不愿意打开再看它了”,他说。
是啊,多少编辑的“辛勤劳动”让作者苦恼不已,多少编辑忠职尽责,却与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任火老师以“塑造第二生命”为题的讲话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发言激情昂然:“一个人,不管他官有多大,如果没有第二生命,到头来也就那么回事了;一个人,不管他多有钱,如果没有第二生命,到头来也就那么回事了。”发表时编辑改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第二生命,最终也会碌碌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第二生命,最终也会成为过眼烟云。”从编辑的修改中能看出其孜孜砣砣,那倾其积累为作者做嫁衣的认真样儿,仿佛也跃出纸面;但任火老师认为修改后不仅丢失了讲话的现场感,他讲话时的气势、态度、性格也无从体现了。
任老师说,李白诗句“白发三千丈”幸亏没有编辑后再发表,如果改为“白发一尺长”,李白本应该有的空灵想象、飘逸风格就不存在了。那会多么残忍!多么荒唐!承续其风格的“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等等的惊世妙语也难见天日了。
“李白风格”让我想到“作者风格”,我突然意识到,任火老师对编辑工作、编辑规律很有研究,他记录的一篇篇编辑感悟正是他对编辑行业的熟悉和热爱,他常用的肯定判断也是他戏称的“编辑狂人”的风格,如果改为或然判断,他那种自信的“狂格”是否也在修改中踪影难觅了呢?任老师思考片刻后说,此文是他一气呵成的,不改更能体现他的个性。
放下电话前,任老师几次表示感谢,几次表达今天很高兴;我能从任老师侃侃而谈中感到他真的高兴,我想他更高兴的是编辑放下武器没有修改他的形象。这是他的收获,也是我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