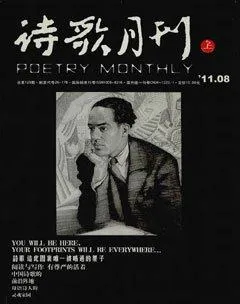许敏:手握青草在宣告的诗人
2011-12-31梁小斌
诗歌月刊 2011年8期
中国的乡土诗写到许敏这个份上,依我看已是相当成熟了:
泥土的心跳藏在蚂蚁细微的呼吸里
一条路的缰绳牵出一座村庄
牵出尘世广阔的牧场
——《吹送2》
许敏,似乎在登高望远,看到自己的村庄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有更广阔的牧场,也由一条路的缰绳牵引而出。诗人许敏深深地知晓乡土和一条路的因果关系,从表面上看,有点像人文地理杂志上的解说词,但是作为一种诗人的自觉,它涉及诗人心灵深处最为静谧的关于村庄起源的讴歌。
诗坛目前还没有真正理解从一个地理方位的角度来写乡土将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看到许敏的乡土诗歌写得很大气,大气还蕴藏着细微,甚至包括蚂蚁的心跳。
许敏是位善于写蚂蚁心跳的乡间诗人智者,他在观察蚂蚁驮着巨大的米粒从灶台上路过的时刻,似乎是蚂蚁的瞳仁在放大,许敏逐渐看到了乡间景观里的所有亲人,对于乡间亲人的捕捉以及塑像般情态的描写,这也使诗人成为一个颇为懂得心灵透视的画人。
风从长城以北吹来
走累了也不肯在许楼村的树杈上
小歇一会儿外婆迈着小脚
去灶间煮鸡蛋谨慎地取出花瓷大碗
往里面加一勺黑乎乎的红糖
母亲已经不那么惊慌了
这是她的第三次生育
——《1976年的大雪》
阴雨天。火柴皮湿了。
母亲擦了两根,没擦着
就心疼得不忍去擦第三根了……
她去邻居家引火,攥紧一把柴禾
又从柴堆里抽出一把,以作酬谢。
看着母亲匆匆的背影
转过墙角,那么低矮
像一朵由泪水构成的暗黑的火焰。
——《简单的一天》
最为感人的是许敏的外婆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外婆迈着小脚去灶间煮鸡蛋,谨慎地取出花瓷大碗,往里面加一勺黑乎乎的红糖,许敏的童年是在红糖尚很金贵的年代度过的,他的目光自然也离不开灶台,灶台依旧,后来换成了母亲的神态,许敏叙述道,母亲擦了两根火柴,都没有点着柴禾,便舍不得再擦第三根,她于是去邻居家借火,顺便扯一把柴禾作为对邻居的酬谢。许敏母亲的节俭和宽厚自然已经历历在目,但从诗的取向来看,这个关于母亲借火素材的深意却没有被敏锐地表现,素材挖掘当在母亲借火的过程中,而不是在美好素材后面加上议论的絮语。这一位母亲到邻居家不是借火柴,而是到邻居家灶台里引火,“引火”也想到了酬谢,一个中国乡间母亲的心灵思索暂时还没有有力地展现出来,但许敏的诗已接近禅机。
许敏乡土诗歌感人至深的奥秘的确尚未得到明确揭示,我读他的诗,也绝不轻易放过他的诗歌字里行间任何闪光,因为他的语言在各处闪光,如同蟋蟀在各处蹦跳,有时语言的闪光蒙上了口语的懈怠,但我仍然不把它放过。
格外地要说一下,当读到许敏的《夜曲》里这么一句:“三间茅草屋,有了一些松动”,心便被揪紧了,在另外一首《燕子又回来了》,许敏写道:
牧牛,拔草,除虫,担粪,然后写下炊烟
然后松动——松果样坠落
这两处出现的“松动”,可谓是诗意在无意间迸发的精品,“松动”,有时代表着茅屋可能倒塌,有时却代表着紧张劳动后,更为紧张地松果般坠落,许敏在暗示着对于既往景观的一种总结,“松动”一词鬼使神差地用上,关键是,当发现了茅屋和牧牛生活在咔咔作响时,真正的松动、阐发其实则刚刚开始,是的,许敏当加固业已松动的既往生活。
许敏乡土诗歌语言的精美和时而滑过的恰如其分的“口语”,准确,实际上不用我多说,读者即可享受到它的好处,并感受诗意盛宴,问题是,许敏抛弃了心灵的傲慢之后,他长久地沉浸在乡村的景观中,他可能要面临着什么,另外,许敏的诗从客观上,他究竟向诗坛贡献了什么?
多年前,文学界曾有过《白鹿原》、《平凡的世界》那类关于世代乡村的小说,乡村在沧桑变化中给人造成了心灵矛盾和渴求至今仍没有答案,“乡间”是一个哲学命题,是一个非有大智慧才可涉入的近在咫尺的、欲说还休的永恒话题。
乡村变迁的时尚主题在许敏情愫中,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焦躁和不安,他先是在合肥郊区父亲的粮站工作过了些时日,后来他当上了警察,派出所就在一座“公厕”的旁边,这个农村青年当时并不是在戏弄派出所,而是表达良好的平凡心态,这就是警察也融于乡间,在中国,任何新鲜职业都将染上农村的土气和方言,乡间,它将融化一切,合肥的乡间甚至比许敏所钟情的白雪和黑夜都更加广阔,乡间令黑夜置于乡间,而不是包围着它。
许敏的诗与乡土水乳交融般的契合,让许敏的诗歌少走了不少弯路,避免了流行的浮躁,这几乎是土里土气订下了许敏诗歌心路历程的终身。
诗歌贵在沉浸,沉浸中看到的合肥乡间的山水图,许敏是这样描写的:
像驱逐盲人眼中持久的白雾和黑夜,
大地刚刚侧身,压扁的乳房——山峦
有寂静之美,湖水与之并排躺下。
——《孤岛》
中国文化的奥秘在合肥山水间被许敏无意揭示着,中国山水图,最讲究令我们梦回的合肥乡间在整个图画里它究竟在什么位置,乡间是怎么形成。但是,往往形势是这样,中国山水景观令人感到亲切的描画并不多见,在离我们最近的乡土之外,如果继续透视,我们亲切的山水河流,并不能流得很远,特别是文人画,把亲切的山水画成了陌生的山水,令人感到这是孤独的山水。同样,在诗歌中,我们尚没有读到真正地面向乡间的乡土诗歌,因为乡间到底是陌生的,还是亲切的呢?乡间到底有多大,它的疆域在哪里?它是无限还是有限?
许敏,至少在思考这些问题。讲到许敏对于乡土诗歌的确有贡献,我是有把握的。
暮色依旧,燕子又回来了
衔着湿泥,沿着灯火的方向回家
野地里,你多次拾到腐朽的棺木
那是大地的胃液尚未将逝者的亡灵消化
——《燕子又回来了》
这就是许敏对于亡灵的贡献,他将生者与死者连为一体,我相信这绝不是偶然的,顺便也说一下,拾到了棺木,怎样精确地表达,可能将预示着诗歌经典的诞生,但许敏确与经典诗歌擦肩而过。不要轻率地进入大地的胃液当中,不要轻易让棺木腐朽,让棺木进入虚空,那是文人的情感,农民不是这样想问题的,棺木实则就是一种建筑,后人看到朽木,是后人看到了本不该看到的形态,棺木没有腐朽,它在大地的胃液中继续形成宏伟的建筑,乡间也就是中国人永恒的殿堂,我们当依从许敏的思路,我们当活在乡间的宏伟坟墓,而不是消亡,变得无影无踪。
乡土诗歌写作写到灵魂出窍的时候,这将带有人文地理的特征,许敏肯定有这么一个体会。许敏早期所接触的外国诗,那些带有铜质的地理方位般的诗歌取向,也深深地感染着他,外国诗为什么能标出乡间与周围景观的关系呢?这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不是单纯的显示大气磅礴而为,这是因为,在基督教的世界,乡间之外的景观是庇护乡村的,因此在基督教世界里,乡村再广阔,诗人均不感到陌生。咱们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的乡村走不了十里,我们就感到陌生,如同方言,我们走不了十里,就语言全变。许敏心情大致也会在陌生和亲切之间徘徊。
诚恳地说,一条路牵引出广阔的牧场,是诗人心灵所爱所至,许敏没有刻意地去指责大路对于乡间的陌生感,这非常珍贵地指示出诗人乡间疆域的宽阔和无限,但我们的确也不放弃这里面的哲思。
我记得,汪曾祺小说曾经写过,在日本鬼子轰炸重庆大学的“间隙”,有男女学生偷着跑回校舍打开水,并趁机谈恋爱,汪曾祺小说无意地告知了好像日本人的敌机在呵护青年学生的浪漫生活。沧桑巨变对于合肥乡村的侵蚀,却让许敏的诗在时光的“间隙”中显得更加欣欣向荣。
还有一位小姑娘来到井边打水,装满水桶的水清澈照人,刚刚在井台上放了一会,便有牵牛花爬过来,爬到水桶上喝水,并在此生根,这个美一点的例证,与严峻的现实道理,异曲同工,后者因为美,我们忘却了真实的严峻。牵牛花准备生根的地方,恰恰是小姑娘准备拎桶就走,扯去花朵的“间隙”,而牵牛花全然不知。
还有许敏的诗也写到:
虫声,细柔了下来。被月光碰碎之前,
它们是锃亮的黄铜、绚烂的丝织品,
是一群穿花裙子的小姑娘挤在槐树下躲雨。
——《忆桂花》
如同牵牛花一般的寓意,这个“躲雨”的镜像,在一群小姑娘全然不觉地完成。趁着虫声未被月光碰碎之前。许敏的诗虽说诗意承接尚不十分精确,但他深晓,一个“碰碎之前”,足见其诗意有其匠心,当然,也可能这是笔意和朦胧的深邃所致。
这样看来,许敏的诗已经概括着中国乡土诗发展至今的全部成就和全部疑点和难点。中国乡土诗和许敏的诗,其情感的真挚和语言状景的透彻早已不成问题。许敏和许多乡土诗人一样也面临着他们家乡究竟有多大的遁世挑战和诘问。
有一句解说词,我记不清什么时候听到的了,但仍记得:“当洪水将鸟蛋冲向下游,这些鸟蛋将开始独立地生活了。”许敏的诗也如同奇异的鸟蛋,被洪水冲到下游才会真正开始诗歌的独立写作。
往往好的句子,我们想拼命思考,它到底好在何处,因为一般情形是这样,生命只有真正诞生,才会走向独立,生命尚在孵化,怎么就被冲走了呢?我们现在的思维习惯是,我们能很快地发现生命的悲剧,因为我们的家乡疆域过于狭小。
我们欣喜地认识到,许敏的乡土疆域正逐渐地扩展,他从一个个碎片似的美轮美奂中脱颖而出。他说,他越来越感到合肥民俗里有很多人生的秘密,它们是民间耐读的精妙部分。
在中国,诗人能说出这样的关于民俗的感悟是很不容易的,譬如我,至今对合肥民俗知之甚少。诗人由碎片似镜像的观察和回忆,走向融入合肥民俗的日常人情世故中。这是一个值得珍视、称道的巨大转变。我相信,许敏的确率先实践着一种诗性的大转变,心灵中的家乡疆域在许敏平和真诚的道白中,他的心灵将变成无限。因为合肥的民俗在与其他民俗的共融中是否能独占鳌头,还有待许敏使之能够生花。
风一次次地把目光,刮到树上,碰出声响
村庄,鸟巢一样。树顶的星群,像一个内心
紧抱信仰的人开始平静下来。那些白日里
穿越林梢的麻雀,斑鸠,灰喜鹊,白头翁
它们都到哪里去歇息,它们把夜晚交给了萤火虫
一粒,两粒,三粒……有着这么美而易亲近的距离
仿佛漂亮的卵石露出水面,所有的灯火都黯淡下去
而我是村庄唯一的孩子,杉树一样举着自己
手握青草,持续地高烧,把夜晚看成是一垛堆高的
白雪
——《献诗》
这不是傲慢,也不是乡间孩子的偏见,这是许敏为中国新诗活着而选择的道路,我预祝许敏成功。
(梁小斌:朦胧诗派代表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