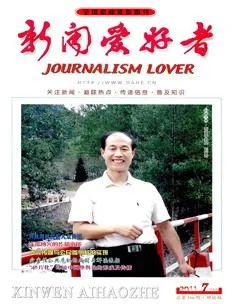“事”和“实”的断裂
2011-12-31高跃丽
新闻爱好者 2011年14期
新写实小说是继文化寻根小说、先锋小说之后,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小说创作流派。其最大的阅读魅力在于用客观的笔法表现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你我他一样的人物,还原生活的原始风貌和原生质态,也就是“不篡改生活”,只做“拼版工作”但肯定“不动剪刀”。①池莉1987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短篇小说《烦恼人生》便是这方面的典范文本。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轰动的关键在于它的求真性,即在文本中表现出生活“纯态事实”②。然而,同样是写当今世界中人们在世的状态,池莉在散文《真实的日子》中对于真实的呈现却与《烦恼人生》大不相同。
“事”和“实”的互悖不谐
所谓“事”,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实”则指真实。它们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本质,因此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并不能等同于揭露了生活的实质,这就是“事”和“实”的互悖不谐。池莉的《烦恼人生》和《真实的日子》便是诠释这一概念的典型文本。
《烦恼人生》以“流水账”一般的形式叙述了一个普通的武汉工人印家厚郁闷而烦恼的一天.池莉对印家厚诸多烦恼的客观描写以及零度情感介入的写作方式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批评家认为,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全盘揭出一种生活,一种被大众普遍接受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共鸣的“不容置疑的刻骨真实的生活。”③但是,当我们抛开种种心理背景只是单纯地细细研读文本就会发现:这种由一个一个烦恼叠加起来的生活其实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原始的真实生活,而是由经过作家刻意加工和提炼后的事实片段堆积起来的生活表象。
和《烦恼人生》相比较,池莉在1994年所写的散文《真实的日子》中对生活的书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接近于平凡人物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作品《真实的日子》与《烦恼人生》有相似的开始,作者起床后首先要去看看女儿,要哄女儿吃饭穿衣服而且她认为自己的时间“给谁都没有给孩子值得”④。而对于印家厚,孩子只不过是他诸多烦恼中的一个。下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在池莉看来这可是件美差:在草坪上和还不愿回家的孩子玩耍,和其他家长交谈,让人身心都感到舒畅。而在印家厚却丝毫没有下了班的感觉,接孩子仍是一件让他劳心伤神的事。晚上,池莉精心准备了丰富而简单的晚餐,晚餐过后和女儿一起看动画片,或者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顺手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而印家厚的烦恼却还在继续,他烦恼自己的工资不够菜钱,看不惯老婆吃饭看书的恶习,不得不刷碗也是折磨他的烦恼之一,更不幸的是在刷碗时听到拆迁房子的噩耗。
通过分析以上两个文本可以发现,池莉并不是用普通人的眼光观察普通人,用普通人的心态揣摩普通人的心态,事实上,她是用作家这一身份来书写鸡毛蒜皮的凡俗人生。而作为一个作家,她在不同的时期是带着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精神体系来切入生活,因此,这种面对同一事件却互悖不谐的情况难免不会发生。
“事”和“实”的相互审视
现象和本质本应是一个整体,但因为人类认识和处理表象的方式不同便造成了两者的断裂,在文学领域来讲这种断裂所造成的后果是“当我们说‘真实’时,永远不可能是在整体意义上来说的。这种真实只能是某一点或某一部分的真实,而远不是全部的真实”。⑤即我们从文本中所看到的只是真实的一个侧面。从《烦恼人生》和《真实的日子》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层面的真实,我想这种真实层次的差异性和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池莉本人的写作观有很大的关系。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为了创造符合标准的英雄人物,作家突出表现英雄们的光辉品质,而彻底滤清英雄们身上的缺点,再加上当时“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倡导,“写实”实际上被作家按照理性原则和理想需要进行过严格的修补剪裁,甚至扭曲变形。同过去的那些“指点江山的慷慨激昂”相比,新写实小说显得平凡而琐碎,它不再美化生活、拔高生活,不再塑造英雄,而是将笔触紧贴生活,真实地描写小人物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蜕变与挣扎。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是新写实可贵之处,但是由于新写实作家、批评家以及大众读者对于文学真实的极度渴望,使得实质上只反映出部分真实的新写实作品被误以为是绝对的写实。因为,所谓写实在英国作家福特·马多克斯·鬲特看来就是“抓住读者,用一个事件将其淹没,使他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读小说,也意识不到作家的存在,这样,最后他会说——而且相信‘我走过那里,我去过’”。但是对于《烦恼人生》我们都能明显感到这是一篇小说,因此它所呈现的真实性是有缺陷的。
池莉最初也受这种意识形态的鼓动并深信不疑,那时的她用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写高大全的英雄,美好的情操。然而,随着整个80年代的突然转型和池莉个人在生活中的磨炼,意识形态宣传中那种被神圣化了的人、事物、思想与价值观在池莉这里都变成了不实之辞。这时的池莉,要反对和纠正70年代的假大空,要检讨和指责被意识形态逼入窘迫境遇的现实生活。就如池莉所说,“正因为秉承着这样的写作观和真实观”,她才坚定认为《烦恼人生》就是真实生活的写照。但是,《烦恼人生》读起来感觉就像是“按先入的理念或既定的原则来截取生活,并让笔下的人物基于那些密集得过度的戏剧性细节负载起某种历史的哲学的使命,成为某种作家急于表达的观念的‘传声筒’”。⑥《烦恼人生》中故事性、戏剧性事件的堆积反映出的只是池莉对于生活真实的单一侧面的认识和理解。
《真实的日子》所写的虽也是生活的表象,但是池莉不再用一种情绪化,抽象化的先入为主的概念来写作,而是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完整表达出来,这种来自于真实生活的感情体验远比那种间接的生活认知真实得多。或者可以说两种生活皆真实,只不过印家厚的生活是经过提炼的真实,池莉的一天是平凡的真实。而企图用前一种真实来代表纷繁多彩的现实生活未免显得单薄和片面。我们有理由相信池莉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情感和评价是真实的,但是这种情感和评价并不等同于真实的生活,也就是说包含着作家主观愿望的文学文本不可能走向完整的真实。
“事”和“实”的文学呈现
生活真实,即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和事,是客观现实;文学的真实是作家提炼、加工、改造过的真实,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更鲜明,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它的真实是作家提炼、加工、改造过的真实,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更鲜明。文学是对生活形象化的反映,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况且,韦勒克曾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最初的定义‘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中,就已经暗含和隐藏着训喻性。从理论上说,完全真实地再现现实将会排斥任何类型的社会目的和社会主张。而,现实主义的理论困难,它的矛盾性,恰恰就是这个简单的事实。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这种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人类的同情,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批评,后者又常常演化为对社会的摒斥和厌恶。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和训喻之间的张力。矛盾无法从逻辑上加以解决。”⑦既然如此,同样是写实主义范畴的新写实怎么可能完全不带情感地对现实生活进行原生态的还原?
其实,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不可能对存在做绝对的还原,因为只要是经过人的主体所认识和表现的东西或多或少都已经包含了主体的阐释和判断。同时,在对感知到的客观存在的还原同时也是对主体感知的还原,它包含着主体的全部感受能力,还原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一种相互作用和融合。所以,新写实的作品也不可能是个例外,它所还原的只是部分的真实,某种层面上的真实而已。
注释:
①《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3)。
②陈思和:《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钟山》,1990(3)。
③李强:《从池莉的〈烦恼人生〉看新写实小说》,《文学教育(上)》,2008(8)。
④池莉:《池莉文集》,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⑤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⑥陈旭光:《“新写实小说”的终结——兼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命运》,《小说评论》,1994(1)。
⑦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批评的诸种概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