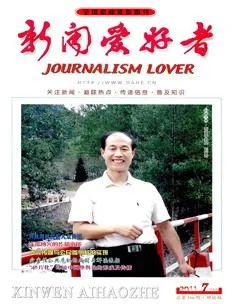浓重的悲情质感和强烈的理性批判
2011-12-31高剑芳
新闻爱好者 2011年14期
周喜俊,一个从农村走出的女性作家,从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一路走来,成就斐然。至今,她已出版《辣椒嫂》、《周喜俊剧作选》、《周喜俊说唱戏曲集》等专著7部,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曲艺》等发表文学、戏剧、曲艺、电视剧等各类文艺作品600余万字,多部作品获省级和全国奖项。因创作成绩突出,她先后被评为河北省管优秀专家、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文联优秀青年文艺家等。2004年,由她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在荧屏亮相,好评如潮,成为当年重播率相当高的电视剧。随后,她创作了电视剧本《当家的男人》、长篇小说《当家的男人》和戏曲《七品村官》,反响强烈。
许多人看过周喜俊的作品后,认为她属于主旋律作家。很多人说到“主旋律”时隐含的意思是:其政治性大于艺术性,主观的东西会让位于政治,是短期的,艺术上是粗糙的、僵硬的,人物是类型化的。实际上这是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揣摩其作品内在的深蕴。周喜俊的剧作也有着浓郁的悲剧性,有着对人生深刻的把握和对人性深层的挖掘。尤其是《金匾泪》和《宠儿泪》两部作品,悲情质感、理性批判精神还是很浓重的。
河北梆子《金匾泪》是作者写的第一出大戏,石门寨村青年姜盼旺是村电工,与冯月兰中秋佳节喜结良缘。洞房花烛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将村里的高压线刮断,引发火灾。姜盼旺抢修电线,不幸遇难,新婚的月兰瞬间成了寡妇,喜事变丧事,洞房变灵堂。痛不欲生的月兰还没从悲痛中缓过神来,自私的二婶就图谋姜家的财产,提出让月兰按照当地的风俗“停灵就亲”,让自己儿子、盼旺的堂弟兴旺与月兰结婚。老支书为盼旺请功,盼旺被追认为烈士。在各级领导和全村人参加的隆重追悼会上,月兰在老支书和全村人热切的目光中表示决心:“今生今世不改嫁,伴你英灵过生活。”老支书代表石门寨党支部和村委会送来金匾,以鼓励月兰:“愿你为妇女做榜样,自强不息永向前。”月兰病倒,她高中同学也是盼旺的好友杨德平作为医生负责给月兰看病。在治病过程中,二人萌发了爱情。但是金匾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折磨着两个年轻人,并且差一点就造成了悲剧。在县妇联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相爱的人终于得以结合,但老支书非常不解,挂了金匾的寡妇怎么可以再嫁。《金匾泪》写了一出寡妇再嫁的悲剧。造成月兰婚姻悲剧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老支书的“好心”,把月兰树为为英雄守节的楷模。老支书的行为起码说明三方面问题:1.封建时代的贞节烈女观念在现代仍然有着存在的土壤,而且根深蒂固;连老支书这样一个正直善良,一心想帮助、保护月兰的人也未能幸免,给了月兰一种无形压力。2.在那个时代,烈士金匾意味着至高无上的道德,容不得月兰的背叛,这是扼杀人性的。要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守着金匾过一辈子,这与封建社会要女性守着贞节牌坊过一辈子有何区别?作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表现作者理性的批判精神。3.老支书有私心,正如杨德平说的:“说什么全是为我好,分明是为了保典型。”这句话道出了老支书内心深处的私心:保住了这个典型,就保住这个村的名声,保住了村的名声,就保住了老支书的声誉。为了村子的名声、个人荣誉而牺牲月兰的幸福,是不人道的。
二是乡村中一些民风、民俗也是差点造成月兰悲剧的重要原因。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肥水不流外人田”,“要为夫家留下血脉、传宗接代,以免断了家族的根使夫家成为绝户”,这些思想在乡间十分兴盛,有浓厚的乡村土壤。姜老海儿子盼旺死了,他很悲伤,悲伤发自内心,老年丧子,无论对谁都是人生重创。但他悲伤的内心里还有更深一层内涵:没有了儿子,不能传宗接代,成为绝户,在村里不能挺胸抬头做人,无人为自己养老送终。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当二婶说把自己儿子过继给他,让兴旺娶了月兰,延续姜家这一支香火,使他不至于绝户、并且老有所养,他动心了,把二婶的“停灵就亲”的想法向老支书提出来。这种封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思想也不只是乡间民风民俗,而是整个中国的一种文化使然,在农村,在城市,在现代,这样的思想仍然是常见的。这种文化观念深入人心,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土壤一时不能消除,月兰的悲剧在这样的土壤上是必然的。
欧洲文学中一直贯穿着一条理性精神的主线,从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到启蒙文学都在作品中强调理性精神。在不同时期,文学中的理性表现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肯定理性,反对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蒙昧主义;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者崇尚理性,强调理性是文艺的基本主题,是评价艺术作品好坏优劣的主要标准;18世纪启蒙主义者更是高举理性大旗,用理性精神去启迪人们的蒙昧无知,认为人类现存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接受审判,合理性者存,违理性者亡。“理性”成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在我国文学发展中,虽未有如此明晰的对理性精神的推崇和发展的脉络,但在不同时代作家创作中,也不乏对社会、人生、艺术的理性思考和理性批判。周喜俊在她的创作中有着对生活的理性思考和批判,体现出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她的《宠儿泪》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宠儿泪》舞台上穿着古代衣衫的演员表演了一出中国现实中常常见到的悲剧故事。砍柴为生的穷苦老汉单老桂,年近半百才有了儿子,百般溺爱,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就连女儿孝敬的鸡蛋和肉也只是闻闻香味舍不得动筷子。在他的溺爱下,他的儿子游手好闲、赌博成性。正是在他的一次又一次姑息、放纵中,儿子胆子越来越大,最终成为败光家产、拦路强奸、杀人害命的罪犯。结局当然是单老桂不愿看到的:犯罪的儿子最终逃不过法律的惩罚。这时的单老桂呼天喊地,但已无济于事,一出由他自己导演的悲剧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反思这出悲剧,谁之过?很多评论者对这出悲剧的现实意义作了深刻的解读。赵志华在《玉不琢,不成器》一文中,深刻剖析道:《宠儿泪》以通俗质朴的语言,鲜明生动的形象,回环曲折的剧情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养儿不教终成祸的故事,为世人敲响了警钟。①
《宠儿泪》的现实价值毋庸置疑,有评论者从戏曲中看到了它更为深层的含义:评论者刘永杰认为:“《宠儿泪》从表层来看,是一个父亲娇纵儿子酿成大祸的普通故事,而仔细琢磨,却发现该剧的深刻内涵是情大于法引出的悲剧。”这样的判断没有错,在作品中,单老桂因为溺爱,使得儿子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他稍有法律意识,法的概念,都该认识到他的教育方法的错误,一味地溺爱只能造就逆子。评论者刘永杰还用具体的“三跪”的分析来剖析单老桂的三跪,使法为“情所退却,三跪跪走了法律的尊严,跪来了家破人亡。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②
刘永杰的评价非常中肯,但是笔者认为,在剧中,这种情大于法实际上正是理性精神缺失的表现。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必然是不断进步的民族,而理性表现在社会秩序中则是法律应有的价值体现。法律是调整社会正常秩序的,一个社会没有了法律,没有了公序良俗,就会走向价值观混乱,而价值观混乱必然使社会走向混乱,最终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国是人情社会,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处事做人以情为准则,而不是以理性、以法律为准则,所以中国社会当情与理发生冲突时,总是情大于理。因此《宠儿泪》的悲剧在更深意义上是理性缺失造成的。笔者认为《宠儿泪》中表达的是理性精神缺失带来的悲剧。作者在强调法律意义的同时,是在呼吁人们要有理性,不要让“情“蒙蔽了双眼,最终酿成悲剧。在现实中,许多违法犯罪的贪官就是因为迈不过人情“关槛”,在人情的狂轰滥炸下迷失自己,理性精神在情感冲击下荡然无存,最终导致发生不该发生的事。还有,类似于《宠儿泪》中养儿不教的悲剧在现实中还在不断上演着:河北大学“飙车案”的李启铭,陕西大学生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挥刀捅死被撞着,富二代的公子们在不断上演着一幕幕社会悲剧。这难道不是这个时代的《宠儿泪》吗?
所以,重读《宠儿泪》这样的作品,提升人的理性精神,有深刻现实意义。理性精神的重建是这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喜俊创作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HB11WX004)
注释:
①②《周喜俊剧作选》,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47页,第559页。
参考文献:
1.赵慧芬:《悲歌一曲寄人间——看河北梆子〈金匾泪〉》,《石家庄日报》,1989年9月8日。
2.黄宗健:《论剧作〈曲江情〉的思想艺术价值》,《河北师大学报》,2003(3)。
3.赵慧芬:《深恋这片沃土》,《大舞台》2003(5)。
4.周大明:《走入大众戏剧层面》,《大舞台》2003(5)。
(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