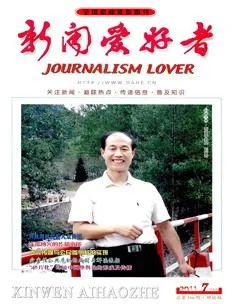评电影《山楂树之恋》唯美的爱情
2011-12-31李慧
新闻爱好者 2011年14期
摘要:《山楂树之恋》是张艺谋着力推出的一部新影片,被称作“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对此,各种评论褒贬不一。在人物和情节的塑造上,影片处处彰显出一种静美。同时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在电影人物的选择上比较成功,尤其静秋的饰演者将那份纯洁与美丽完全演绎了出来。总体看来,影片着力传达的爱情的纯美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它值得当今时代的每个人去深思。
关键词:《山楂树之恋》 纯美爱情 “文化大革命”荒谬
《山楂树之恋》是让观众期待已久的一部电影,见海报上赫然写着“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很想一窥真正的纯情是怎样借助影片来传达的。该片是一部安静得能使人灵魂出窍的电影,惜墨如金的背景音乐虚无缥缈,让人完全沉浸在影片所营造的淡雅氛围之内。拨开薄雾,是一个叫“西坪村”的乡间,映入眼帘的是老三跟静秋的影子,还有他们那流传于世间,永不褪色的爱情。
纯美的爱情,忧伤的情感
《山楂树之恋》表达的情感是很多人想有但不曾有的,无论是放在现在这个色欲横行的世界,还是置于彼时那个思想相对单纯的年代,这样的纯情都显得有些过分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它符合爱情最根本最原始的特质,而且张艺谋通过对这一爱情有意的纯洁化,达到了动情但不煽情的效果。
老三和静秋的爱情虽然被张艺谋故意纯洁化,但这种纯洁化仅仅是在意境上的纯洁化,两人不敢拉手不敢约会等情境都是真实的,都可以从上一代人的切身经历中得到验证,两人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欲说还休的情感正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具有真实性。当年,有无数情意相合的人因为成分和出身的问题,因为政策的问题,而落得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所以在影院中的中年人暗自垂泪正是对过往的自伤。这种情怀岂是已经丧失了爱情基本原则而被“锤炼”得百毒不侵的当今新新人类所能体会得到的?正因为现实中的爱情是如此物质和如此肉欲,所以那传说中的爱情才显得如此纯美如此珍贵,并且这种传说的爱情的的确确真的存在过,倘若脱离了影片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而单纯地去计较张艺谋的个人艺术追求,那实在是强人所难和吹毛求疵。在我看来那是个贫穷而坚强愚蠢但可爱的时代。因此,那种纯美的情感值得向往。
这种纯美还体现在静秋与老三的笑容中。《山楂树之恋》的故事基调起得很低,将一段生涩朴实的爱情始末搬上了银幕。没有多少喧嚣欢闹,没有多少缠绵悱恻。有的只是一如既往的平平淡淡,和多次定格的甜美笑容。片中窦骁饰演的老三,相信他的笑容一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伊始,一口闪亮的白牙就分外耀眼,诚恳、热情、真挚等的褒义词都仿佛能从这些笑容里显露出来。老三有一颗不羁的心,渴望自由自在的爱情。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他既迫切地希望冲破旧政策的牢笼,又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静秋“循规蹈矩”的宿命。在如此矛盾与坎坷之下,想必笑容能战胜一切,至少能营造出暂时的二人世界。
静秋的笑容就稍不同于老三,命运多舛的她事事小心谨慎,时刻保持着与“错误”的距离。她几乎是一见钟情地爱上了老三,她的笑容代表着幸福,懵懂爱情的滋润让她芳心悸动,但又不知所措。大多数时候,只是傻傻地接受给予,当爱的分量到了一定程度,她的笑容变得更单纯,并开始懂得去“付出”。老三与静秋,从第一次见面的笑容里开始,到最后一次离别的泪水中结束,其间错落的黑夜,见证着这段随风而去的不朽爱情。
老三的悲剧,似乎贴上了一般爱情电影生离死别的俗套标签。但要想到,毕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那么就丝毫没有理由去抱怨这所有的一切了。“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了,我也不能等你到二十五岁了,但我会等你一辈子……”老三的这句话,到最后的字幕也一并沿用。要是出自旁人之口,可能会忍俊不禁,但经过了100多分钟的洗礼之后,观众已经彻底地被折服了。最后留在手臂上的那条疤痕,其实是烙印在内心里,早已刻骨铭心了。
借助爱情反映荒谬的“文化大革命”时代
影片对时代背景的复原相当考究,贫穷凋敝的农村生活,淳朴甚至有些傻里傻气的人物,随处可见的革命标语和口号,以及那种盲目的战天斗地的豪情,都有一种很强的时代感。尤其是静秋排练的那段戏,对领袖的热情而机械的崇拜之情跃然眼前,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十分可笑的歌舞正是当时的时尚之举,相信这样的场面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一定能把特定观众群体立即拉回到那个百感交集的年代。从这个细节上看,张艺谋的目标观众并非仅仅是网络时代的年青一代,还包括愿意和电影一同怀旧的必定是60后70后甚至更早的人,只有这个时代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个头脑发热年代的人们的普遍情怀。而更加年青的一代或许更愿意对照原著来讨论影片中的爱情究竟是否“纯情”,因此,看《山楂树之恋》是属于特定群体的怀旧之旅。
相比《唐山大地震》在商业上的成功,完全是因为32年间两场自然灾难对中国人的心灵伤害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母子亲情催发的,对于两场地震背后的人祸,根本不能也无力去批判。比之于《唐山大地震》,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显然没有那么多的现实政治因素的羁绊,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看到的一定是个体爱情在混乱年代和残酷生活面前的无言与无奈。片中人物多次提到“万一政策变了”这句话。今天的人们可能根本无法深刻体会这句台词背后隐藏着的那个时代国人的辛酸和悲苦,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被激情填满胸膛的集体又充满着集体的迷惘,政治的动荡导致了民众对政策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怀疑,而与之息息相关的是个体的不能自决的命运,天堂或地狱都取决于这个“政策”发生的变化。影片没有过多也无法揭示时代背景中的种种阴暗面,但是从电影中的某些惊鸿一瞥式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事件中,依然能感受到深烙于中国民众心头的时代之殇。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观众在谈论《山楂树之恋》时,竟然忽略了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于是得出了一个“无知”的结论:认为影片中静秋对生理知识的无知乃是这段纯真爱情的基础,其实懂点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剧中人的无知乃是源于那个无知的社会。
其实,《山楂树之恋》的意义不在于要告诉人们什么是纯真的爱情,因为你的纯真不是我的纯真,而是要通过静秋和老三的爱情悲剧,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荒谬与险恶。恰恰是这个被许多影评人有意无意忽略的政治背景,才是《山楂树之恋》的眼睛,如今你悄悄地蒙上了这双眼睛,又能猜到什么?所以只好人云亦云,一股儿脑地拿“纯真”开刀。在媒体的采访中,出品方口口声声为这部电影加上“纯情”、“纯真”的标签,结果遭到很多人诟病,也是活该。
因此,评论《山楂树之恋》是不可能抛开“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个神奇的年代,之所以说神奇是因为80后的几代人都无法体会到长辈所经历过的疯狂和惨痛。张艺谋没有在叙事中引入诸如《芙蓉镇》那般的人性扭曲和身心摧残,对于“左”与右、红小兵与牛鬼蛇神、组织与老大哥只是轻描淡写。对神奇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在如今是不可能有经典的电影作品的。这样,本片就只剩下青春和爱情了。奇妙的是,静秋所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或多或少能在80后的童年中找到相似处。原因是对于爱情的理解穿越了数个世代而没有过多的变化。
整个故事的细节建立在我们陌生又熟悉的时代之上。那些写不进历史教科书,但是那些从未在父母的唠叨中被丢弃的道理、在装破烂的小盒子里丧失活力的物件,也能透过镜头,一再向我诉说着它们的珍贵和见证。而且,这些东西,很多是可以被一代代复制甚至跟随时尚卷土重来的。比如那时候编钥匙链,有些观众看到的时候,就有些共鸣。当然,这些算做轮回的细节,包括我们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时才有的学习情节说话方式,都属于我们其实不常记起甚至不曾经历的“共同回忆”。
淳朴的演技与静美的色彩的融合
应该承认就整个故事而言,存在着局部过分美化的成分,但两位新演员尤其是周冬雨的单纯而干净的表演严重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并没让人感觉到做作,让人愿意相信那份纯美。银幕上的这个周冬雨绝对要比银幕下纯净得多也美得多,静秋的娇小柔弱与小说中的丰满有些分别,但她的纯洁青涩、稚嫩和羞涩一定是属于静秋的。
张艺谋选角时说他相信自己的眼光,肯定周冬雨在镜头面前一定光彩照人,事实证明张艺谋的结论。老三的演员选得很恰当,身材修长挺拔,笑容灿烂,笑起来牙齿整齐洁白。另外,张艺谋对于画面的控制能力还是很有特色也很见功力的,这是他的长处。但是难以理解的是,影片频繁的字幕切入,影响了影片的节奏,同时也暴露了影片叙事能力的不足。幸亏这部电影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舒缓的过程,这种处置不当也并没有对影片观赏性形成致命伤害。
影片中的那棵山楂树,这个被用作影片片名的象征物,在故事中多次被提起,并不是仅仅为了切合主题。静秋刚来到村子的时候,老师给他们讲山楂树的故事,它本是开白花的,后来被烈士的鲜血染成了红色,静秋一直想知道这棵树到底是开红花还是白花,结果呢,影片的最后,导演给出了答案,可惜很多观众已经准备起身离开了,于是错过了山楂树开花的时候,也错过了影片的真相。
张艺谋一直被人戏称为“色彩大师”,在这部他一改往日风格,几乎没有“色彩”的电影中,他把所有的色彩都放在了那一树的山楂花上。山楂花本来是白色的,却被意识形态渲染成了红色,于是人们一直活在红色山楂花的幻想中,这红色也就更加绚丽。影片最后,静秋去见病中的老三,穿的就是红色的衣服,也预示了他们的爱情,一件红色的祭品。所以,影片结尾还原了山楂花本来的面目。质本洁来还洁去。愿各位都能找到自己的纯真的情感感觉。
总之,《山楂树之恋》是一部安静的电影,演员静静地演,观众静静地看。即使流泪,也想静静地任其流,因为擦拭的声音会打破这种安静。电影中除了静静地讲述静秋和老三的爱情,没有多余的色彩没有煽情的音乐。有的就是心底这份由衷的感动。任何影片都是一个谜,因此我相信这样一句话:“在电影里,你看不到的永远比你看到的多得多。”
参考文献:
1.钱智民:《论精神分析与电影艺术受众的心理关系》,《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9)。
(作者为河南大学硕士生,南阳理工学院文法学院院长,副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