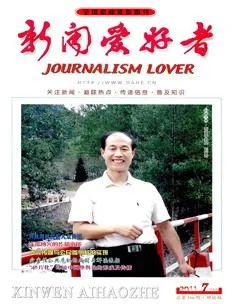广告中的伦理失范现象
2011-12-31崔书颖
新闻爱好者 2011年14期
时下,很多广告主和广告商因为不避忌讳,有悖世俗人情,甚至伤害国人情感,而被舆论推到了伦理道德的风口浪尖上。而文化与社会批评学家更是将“广而告之”喻为“广而诱之”、“皇帝的新衣”,认为“广告在我们文明的门面上打上了‘烙印’”。①作为现代传播技术环境中的广告,其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出现了一系列利害冲突。从伦理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广告道德问题,它显示了广告活动所呈现的道德危机和伦理困境。在这里,笔者把它归纳为七种表现:
第一,广告对紊乱的伦理观念的宣扬。伦理观念的紊乱是现代广告活动的伦理问题之表现,这种紊乱主要表现在道德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的盛行和泛滥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现代信息传播环境为这些观念的生长和繁衍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
在哲学中,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立场,道德相对主义者坚持不存在评价伦理道德的普遍标准,认为道德价值只适用于特定文化边界内,或个人选择的前后关系。极端的相对主义立场提议其他个人或团体的道德判断或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否定权威,排斥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的统一性。现代信息传播环境的非中心化、多元化和全球性的特点正契合了道德相对主义的观念诉求,而现代信息传播环境尤其是Web2.0时代媒体传播方式的转变,自媒体的诞生——借助于互动性、实时的平台,所有人的独特需求、个性、追求和消费习惯,即这些独特的生活形态和生活经验通过自媒体呈现出来,并不断生产、积累、共享和传播他们的独立空间。这个空间是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需求与欲望,而无须也不可能对整体负责。传统的社会道德标准的统一性和确立性在现代信息传播环境中模糊了,社会伦理道德的统一性标准似乎遭到了颠覆性的策反。
与道德相对主义相伴随的,必然是个人主义的泛滥和多元价值观的盛行。个人主义伦理观的核心就是否认道德的绝对性,强调道德在本质上是个人的。其根本原则就在于善与恶的主观评价,个人行为若只关乎个人,那么个人就是行为善否的评价者,而无须诉诸任何高尚的伦理原则。在我国,漫长的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占有重要地位,大众文化却已轰轰烈烈地到来,而消费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全球化力量渐渐取代了大众文化,其价值观正在对我国进行新一轮的冲击,多元化的价值观纠结,形成了现代人道德行为的多元评价。在这样的多元价值观背景下,我国社会和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以信息生产为基础的“仿真”阶段,广告就是一种仿真,一个没有原创、没有客体指涉物的复制。广告的目的就是在叙述称心如意的生活方式时令人联想到一个能指符号。在广告张扬的世界里,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我”的存在、“我”的喜怒哀乐、“我”的体验与感受成为主角,“我”的需要与欲望、个性化的体验、快感与愉悦,成为生存的基本追求。在广告的世界里,传统的宏大叙事结构里的中心主体消失了,权威被扯下了庄严的外衣,偶像也走下了神龛,消费文化强调回归自我。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权威,意味着人人都是权威;没有中心,意味着人人都是中心;没有主角,意味着人人都是主角;没有统一的道德行为评价标准,意味着人人都是标准。在现代信息社会里,很难准确地区别虚拟与真实的界限,这为个人主义的极端膨胀提供了良好的滋生环境。
第二,广告对诚信体系的消解。道德观念的紊乱使现代广告活动中出现了大量的不道德行为,导致广告活动系统的熵值增加,使广告活动系统充满冲突、混乱和无序。广告对诚信体系的消解主要表现在虚假广告与恶意比较广告上。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虚假广告的法律概念及其构成要素,依据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有关虚假广告的规定,我们可以认为:虚假广告是指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在广告活动中对商品或服务的内容作不真实的带有明显欺骗性的或误导性的表述,导致或足以导致消费者做出错误判断从而对其产生高期望值的广告。恶意比较广告是指在广告中采用不公正、不客观、捏造、恶意歪曲事实、影射、中伤、诋毁等不正当竞争手法,损害他人商业信誉或商品信誉,进而削弱其竞争对手实力的广告。
第三,广告对受众的暴力传播。有人曾说,我们每天呼吸的不只是空气,还有广告。尽管由无数法律和自律力量禁止在电视和广播上短时间高频度播放广告,但是由于媒介本身的外溢性,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广告的侵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叫做“可行能力”的概念,意思是指一个人能够免受痛苦,能够识字、有尊严地活着的自由。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越大,那么他就能越享受到他所珍视的那种生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要是有人活动的地方,就会有广告的身影。广告的无限制发展突破了时空的界限,达到了极为膨胀的境地。在现代信息传播环境中,广告无孔不入,呈现出一种暴力化的传播倾向。
这是一个媒介越来越发达、广告表现越来越丰富、广告发布越来越不受限制的时代,如果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与广告发布者无视受众的接触体验,简单粗暴地高频度投放广告信息,无限制地骚扰甚至损害用户体验,直接导致的后果可能是逼迫消费者拒绝接受广告信息的强制洗脑,这种广告效果其实并不好,可以说是广告主花巨资精心制作的广告,自以为投放在了组合适当的媒体上,收获的却是广告被忽略甚至广告商品或服务惨遭抵制的后果。
第四,广告对特殊受众群体的侵犯。广告对弱势群体的侵犯突出表现在广告对儿童的侵犯以及对女性的刻板化的表现上。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儿童是脆弱的市场,他们对自我、时间以及金钱的辨识能力尚未成熟,因此并不能理性地利用经济资源来满足自己。广告主针对儿童的广告,很容易让儿童对广告商品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望。如果广告主利用儿童操纵家长购买东西的心理而制作广告,就会引起家长和社会的普遍愤怒。电视广告的内容高雅与低俗、是否重视伦理道德、其所体现的价值观无疑会对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女性是广告中的主角,而女性的角色形象在广告中有被刻板化的倾向。亚特兰大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斯库林说:“人们不愿意承认,但只要有生物,啤酒广告中就会有性。”也许他说的是对的,现代广告中的年轻女性形象总体上呈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被物化,即作为成功男人的陪衬被比附于酒、车等某一物品上,实际上是对女性尊严与个性独立的一种蔑视;另一种则是被作为性对象凸显出来,如果性与产品相关,那么性诉求会产生良好效果;如果没有关联,则会严重损害广告主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但不管怎样,都会对目标市场之中的女性以及目标市场之外的儿童造成伤害,他们可能会受到间接的影响。
第五,广告对社会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广告总是包围着我们、侵入我们,它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说话时可能参照广告语言,我们通过广告向我们凸显的模式去看,我们的味觉喜好可能由于广告的展现而游移,我们的穿着可能比照广告模特所指引的时尚潮流,我们对人、对事的判断可能潜移默化地沿着广告中所张扬的标准来评价……“广告甚至能在不破坏我们购物习惯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决定我们的价值观意识走向。‘广告可能导致人们牺牲其他价值观,一味赞美获取和消费的态度与生活方式’。”②广告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其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美德的颠覆和过分强调对物质的享受上。广告中的“一切理想和价值观都服务于、从属于商品的购买和物质满足的生活方式的获取”③。广告在不断地重复着它的价值观:我购买,我消费,我快乐!由于广告质量本身的良莠不齐,其过于露骨和不雅的表现,对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是一种伤害;而其对消费至上的鼓吹则导致了享乐主义的滋生和物质享受的过分依赖,从而引起奢侈消费的蔓延,违背了勤俭和谦让的传统美德。
第六,广告对人本身的异化。人的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在当今世界,消费文化呈蔓延趋势,这些都彰显着我们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时代。消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被物所包围并以物的大规模消费为标志。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物的消费已不仅仅止于物,而是通过消费来实现物本身被赋予的符号意义来实现自身,从而进行自我的身份定义、文化认同以及价值观的实现。在这里,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体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实际上表明,个人已经被完全物化了。而批评者认为广告由于其巨大的神秘影响力,对制造消费文化负有主要责任。广告孕育了一个非真实的世界,它通常只显示生活中积极的一面,而不显示生活中冲突、消极和紧张的一面,而且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孤立来神化商品,制造虚假的需求,使人盲目崇尚消费与流行,并且通过广告强调:已经都流行了,而你还没有跟上,你是落伍者。在广告的神秘王国中,广告使消费者神魂颠倒。独具匠心的广告,被注入了物恋性质,借助于物品实现自我的能力,帮助消费者获得满足感甚至是狂喜而受到崇拜,其“所激发的是一种类似于物恋的、人与物的关系。在以形象、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作为置换、机能紊乱以及变态行为的恋物癖,乃是将产品和心理满足、情感满足以及性满足联系起来的一个庞大计划”。④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生活的意义仅仅是疯狂地购物,奢侈地、无益地、无节制地进行消费,为了比附而消费,为了认同而消费,为了消费文化中制造出的层出不穷的虚拟需要而消费……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再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不再是主宰自己欲求的、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意识的主体。人的主体性已经丧失,广告把个体与他人的生存的真实条件间的关系再现为一种想象的虚拟的关系,使个体产生幻觉或者错觉而浑然不知。在广告所塑造的消费文化中,精神让位于物质,灵与肉相分离,人成为被动的受制于物的东西。
第七,广告导致的文化冲突。2004年在国内各电视台播放的名为《恐惧斗室》的最新耐克篮球鞋广告片,男主角在广告中逐个打败身穿长袍的中国老者和飞天妇女以及中国的图腾“龙”等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元素。此广告引起了国人的愤怒,并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其实,类似这种广告引起的文化冲突并不鲜见,尤其是在现代信息传播环境下,从技术上讲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村落,但却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村落,由全球化的广告传播引发的文化冲突此起彼伏。这就给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广告传播提了个醒:作为广告传播者,无论是在广告的创意还是发布上,都应该考虑其目标受众所处的文化语境,把握其文化情感状态,以符合目标受众群体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背景的方式传播,才能实现广告的良好效果。否则不仅不能实现广告的目的,还有可能引火烧身,遭致广告发布区域受众的反感甚至抵制,严重降低品牌价值,损害品牌形象;更甚者还会引发法律纠纷甚至种族矛盾与文化对立。
注 释:
①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③米切尔·舒德森著,陈安全译:《广告,艰难的说服》,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④乔纳森·E·谢勒德、珍妮特·L·柏格森著:《隐秘的欲望:当代广告中的恋物癖、本体论和表征》,转引自罗兰·巴尔特著《形象的修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系)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