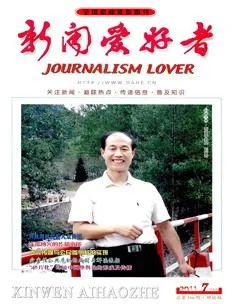公共突发事件中电视人的把关标准
2011-12-31温凤鸣刘兢
新闻爱好者 2011年14期
摘要:公共突发事件由于影响面广、影响力大而需要媒体严格的把关。那么,在我国特殊的媒介环境下,电视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把关标准是什么?本文采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结合把关人理论与我国电视媒体所处的现实环境,试图从理论层面和电视把关实践层面的对照中得出我国电视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主要把关标准。
关键词:电视 公共突发事件报道 把关标准
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从采编到最后播出需要经过层层把关,有多个把关人。本文所指的把关人特指直接从事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电视新闻记者、负责报道播出的节目监制、总监和部门主任。
把关人理论与把关标准
“把关人”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传播学创始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他指出:信息流动的渠道中总存在某种“关区”,即根据公平的原则,或者根据把关人的个人意见,而决定信息或食品是否可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①随后,传播学者怀特从社会学角度认为,大众传媒把关的标准主要来自作为自身原有经验、看法、兴趣等总和的预存立场。同时,也受到周围环境如上级、同僚以及受众等的影响。②国内学者陆晔从宣传管理、媒介组织、消息来源三个方面来分析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揭示了中国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几种重要的把关力量。③张国良则在媒介把关行为的共性中发掘出了个性,认为宏观层面上媒介组织基本按照相同的标准、原则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和处理,而微观层面上各家媒介在对抽象标准的具体理解和运用上却不尽相同。④国内外学者对把关现象的探讨和研究大多集中在媒介运作的宏观层面,而对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特别是电视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把关及其把关标准的微观研究却难觅其踪。
卢因的把关概念是建立在“渠道理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把关的除了把关人之外,还有一些规则⑤,正是这些规则构成了新闻报道的把关标准。研究“把关人”实际上就是研究导致把关人作出某一决定的因素,也就是探析隐藏于“关”的开、闭行为中的各种因素。⑥
当代中国电视人对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把关标准
根据澳大利亚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的研究,公共突发事件是指对全国或部分地区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共秩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重大威胁和损害,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急需快速作出决策的紧急公共事件。⑦公共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时间紧迫和影响力大等特征。⑧而按照学术界较统一的解释,所谓公共突发事件,是指瘟疫、洪水、地震、事故、恐怖活动等可能影响到人类整体或局部生存利益的灾害灾难。通俗地说,就是指一般带有负面性质的“坏消息”。所以,在受众眼中,许多所谓的突发事件在一般意义上就成了坏消息的代名词。⑨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公共突发事件报道和一般的新闻报道相比就多了一些特点,需要更加重视和强调报道的及时性、客观性、准确性、全面性和正面引导。
电视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中,最直接的把关人是电视记者和负责播出的节目监制或总监,除此之外,部门主任则作为更高级别的把关人,也在电视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中起着把关作用。本文所研究的就是记者、节目监制或总监以及部门主任对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把关标准,这些标准既有来自把关人个人的主观认识,在我国现有的传媒体制下,更多的且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来自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压力。
专业标准:公共突发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当一个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电视记者首先根据自身已掌握的新闻专业的价值标准,判断事件值不值得报道。公共突发事件,常常意味着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从新闻专业理论上说是值得报道的,那么,是否所有在记者看来值得报道的公共突发事件都在电视上报道播出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对一个公共突发事件,记录和播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因此,对电视新闻记者而言,决定报不报某个突发事件的首要标准是突发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而决定播不播出突发事件则再由把关人去把关。正如某省级电视台的一位新闻节目监制(首先是记者的身份)所说:“在决定报不报一个突发事件时,我们优先考虑的是突发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这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最应该做的事情。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突发事件,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只要事件本身具有新闻价值,我们都应该去记录下来,至于能否在节目中播出,就不是我一个人(作为记者)能决定得了的了,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上面(主要指宣传部门)没有特别要求的话我们都会播出的。”
在对公共突发事件报道进行把关的过程中,一线电视记者的把关作用主要体现在事件的记录上,而突发事件的播出则需要更高层次的把关人根据其他标准作出决定。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政府及行业部门的宣传口径、收视率及受众需求、社会影响及传媒责任这三个分别代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标准成为决定突发事件能否播出的主要因素。
政治标准:政府及行业部门的宣传口径。政府和相关行业部门的宣传口径成为电视公共突发事件报道把关的一个标准,并在电视节目监制、总监和部门主任等把关人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由我国电视媒体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目前,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成为电视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相对负面”的公共突发事件中更是如此。某电视台的一位中层领导认为,电视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的一些限制主要来自上级(政府宣传部门)的指令,“对于特别重大的公共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政府部门的宣传口径,而对于一般的突发事件我们才可以更多地考虑新闻事件本身的价值取向(即新闻价值)”。另外,政府及行业部门反过来又是电视媒体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电视媒体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经常需要从政府及相关的行业部门那里获取消息,而政府及相关的行业部门又往往设有自己的新闻发言人,“由于他们这些行业部门经过了一层把关,有他们自己部门的利益考量在里面,对于我们电视媒体所做的新闻(报道)在真实性和客观性上就会有很大影响”,用这种方式获取消息所做的突发事件报道的立场自然就跟政府和行业部门的立场及宣传口径保持一致了。而事实上,对电视把关人而言,报道和播出的公共突发事件只要与政府和行业部门的宣传口径一致,就不会受到惩罚,就不用承担风险。
经济标准:收视率及受众需求。塔奇曼(Tuchman)认为,新闻是有组织的生产活动,是媒介组织制造出来的产品,新闻生产必须符合媒介组织的需求与标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我国电视媒体特别是省级及以上的电视台都将收视率作为衡量新闻报道好与差的标准,对于突发新闻,无论是选题意义及其社会影响力还是报道的角度和形式都会影响到该条新闻报道的收视率高低。因此,电视把关人在决定突发事件能否进入电视渠道传播时也经常把收视率及受众需求作为把关标准。正如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所认为的,世界上同时发生的非常态事件太多,媒体往往选择那些有更多人关注的,也就是说能影响更多人的事件进行报道。⑩因此,对于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也一样,只要有人关注,就能带来收视率。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现在的电视媒体特别是省级及以上的大台,都在向企业化改制,这就意味着包括新闻节目在内的所有电视节目都要依靠广告和收视率来创收。一些电视台新闻记者的收入与节目收视率挂钩,记者所做的报道未达到台里规定的收视率则要扣除一定数额的奖金。因此,收视率和受众需求也成为电视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一个很重要的把关标准。
社会标准:社会影响与传媒责任。传媒具有协调社会的功能,社会责任理论要求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这在中西方的新闻生产中都一样。我国电视媒体也把社会影响和传媒责任作为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一个把关标准。某电视台的一位新闻节目监制认为,“做突发事件报道时,首先要看突发事件报道之后是否会有负面效应,比如罢工、示威游行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报道之后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所以我们就不报;其次要看媒体所做的报道是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如缓解与疏导民怨等;再一个就是要考虑我们播出之后可能会产生的结果,主要指社会影响和传媒公信力方面”。
在访谈中,多位电视新闻记者与新闻节目把关人提到传媒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并认为一家有公信力的媒体一定会把传媒的社会责任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去考虑,因多数公共突发事件都是民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媒体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媒体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仅不利于突发事件的解决,还可能引发社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正如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媒的功能理论中提到的,传媒除了具有雷达、教化和娱乐功能外,还应该有社会功能,承担协调、沟通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因此在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中,社会影响成为电视新闻把关人选择报道事实和报道角度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结语
在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把关过程中,是存在着“主观偏向”的,这种“主观偏向”可以是记者、节目监制或总监个人,也可以是电视媒体组织,或者同时包括两者。但在实际的把关过程中,个人往往要服从于媒体组织,也就是说记者个人对公共突发事件新闻价值的判断往往要让位于电视媒体组织的报道要求与标准,而电视媒体组织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报道要求与标准又往往受制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
行文至此,我们很容易想起美国当代著名媒介批评学家和新闻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提到的观点,他认为,在所有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我国电视新闻媒体既有事业属性,又有企业性质,这就决定了我国电视媒体既有政治依赖性,又受到市场和经济的约束,因此,电视在对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把关过程中,既有来自政府及行业部门的利益考量,又得顾及自身的生存问题,还得考虑电视作为传媒的社会责任,但作为新闻工作者,电视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把关人仍然坚守着心底对新闻的最高理想——以“客观公正、自由独立、服务公众”为主要内容的新闻专业主义,电视新闻人特别是电视新闻把关人,仍然坚持着对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不懈追求。(本文为广东省教育厅2010年度育苗工程项目海外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丹尼斯·麦奎尔著,祝建华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陆晔:《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形态研究》,第二届中国传播学论坛,2002年6月。
④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⑥黄旦:《“把关人”研究及其演变》,《国际新闻界》,1996(4)。
⑦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⑧管文娟:《公共突发事件媒体危机传播策略探析》,《高等函授学报》,2008(12)。
⑨文新国、姚伟民:《电视传媒在重大新闻及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三大优势》,传播学论坛,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1968
⑩赫伯特·甘斯[美]著,石琳、李红涛译:《什么在决定新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刘行芳:《西方传媒与西方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
参考文献:
本文部分直接引用的观点来自深度访谈某省级电视台新闻节目“把关人”的谈话内容。
(温凤鸣为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硕士生;刘兢为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