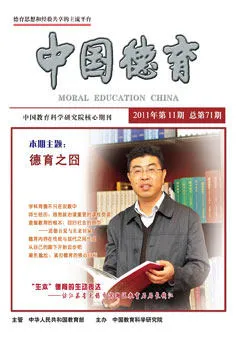德育内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生成
2011-12-29李长伟
中国德育 2011年11期
[摘要] 在学校德育生活中,传统道德是德育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现代道德也是德育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不过,由于时代与社会的复杂,德育内容陷入尴尬之中,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难以融为有机的统一的德育内容,二者呈现为一种紧张和冲突。如何化解这种尴尬,是德育需要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
[关 键 词] 现代道德;传统道德;德育内容
[作者简介] 李长伟,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道德的存在。进言之,人是自由的和理性的,自由使道德成为必需,理性使道德成为可能。不过,道德人的造就与道德共识的形成,根本上离不开教育,因为无论是自由意识还是理性能力都必须且能够经由后天的有目的的培育。这就必然涉及一个无法绕开的教育问题:如果道德是可教的,那应该教什么呢?从教育理论的角度说,应该教什么取决于道德是什么;从教育现实的角度讲,应该教什么取决于时代与社会的精神和氛围。下面只从中国教育现实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传统道德是重要的
就当前的学校教育而言,道德是重要的,但传统道德是重要的吗?在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看来,传统道德是一种压迫自由和进步的反动力量,应当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是,自近代我国国门被轰开以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传统道德的革命是时代和社会的潮流,从“五四”时代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时代的全面反传统,都以革传统道德之命为最高使命。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存在,人无法与传统道德决裂;人是历史性的、寻根性的存在,传统道德塑造着人性,人性内在地寻求传统道德。倘若将传统道德完全从社会、人与教育中革命掉,剩下的将是一片道德废墟和普遍的人性虚无。保守主义者希尔斯在论说西方传统时说:“没有哪一代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范型和各种制度,即使生活在现今这个传统空前地分崩离析的时代的人也不例外。这一论点适用于现在活着的几代人和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无论这一代人多么有才干、多么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他们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表现得多么轻率冒进和反社会道德,他们也只是创造了他们所使用和构成这一代的很小一部分东西。”[1]50所以,希尔斯认为,一切人都“生活在过去”,“即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 [1]64。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则针对自由主义者的反历史的道德个人主义,提出人是故事性的存在的观点,认为人们生活在宏大的故事之中,故事决定了人们如何行为。他说:“我从我的家庭、城市、部落和国家的历史中,继承了各种各样的债务、遗产、正当的期望和义务。这些构成了我的生活中的特定成分和我的道德起点。”这意味着,叙事性的自我观与个人主义的抽象性的自我观明确区分开来,“因为我的生活故事总是内嵌于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从这些共同体中,我获得了我的身份。我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个人主义模式中的那种试图隔断我自己与这种历史的尝试,就是破坏我现存的关系”[2]。 总而言之,无论是希尔斯还是麦金太尔,都强调传统道德对于人性的塑造和教化作用。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行为方式的独特性究竟体现在那里?或者,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独特的道德文化标识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严峻问题,因为它涉及个人与民族的“自我认同”问题与“归属感”问题,倘若不知道“我是谁”,那生存的意义、价值和尊严将荡然无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回归到中国的道德传统,回归到儒释道那里去,是它们规定和塑造了我们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老庄、孔子、孟子、董仲舒、王阳明、朱熹等人的道德思想和实践完全从中国人的记忆和生活中抹掉,那将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显见的答案是,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中国”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空洞的无意义的文字符号而已。也许有人说,绵延近百年的中国反传统主义浪潮不是一直在革除传统的道德文化,建立现代的新的道德文化吗?而且,这样的反传统似乎也没有导致社会道德秩序的崩溃和瓦解,社会仍旧在运转,这证明了现代社会可以与传统道德告别。但正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危机》中通过对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个案解析,证明了“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并未如他们声言的那样做到和传统彻底决裂。好像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始终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在中国某些文化倾向中所体现的某些传统(如‘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已牢固地形成了反传统主义者的观点。”历史学家陈旭麓在谈到左的思潮时也谈到:“‘左’的思潮抛弃了传统,而在‘左’的思潮笼罩下形成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却来自传统社会的土壤,我们既为抛弃了传统而苦恼,又被传统捉弄了而愤慨;被抛弃了的要回归,被捉弄了的要解除,我们陷入了对传统的抛弃和反抛弃、捉弄与反捉弄的困境”。[3]
叙说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意识到,在“教人做人”、“以道德社会化”为己任的学校德育中,传统道德无法被抛弃,它必然成为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说,通过由教师对传统道德的消化和传递,学生成为叙事性的存在,获得生存的价值和自我认同。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前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回归热潮,如学校教育中的“读经热”(很多孩子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诵读《三字经》和《论语》)以及传统“礼仪热”(如跪谢父母和老师),这证明了传统道德在遭遇了一百多年的打压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强势反弹。传统道德从未彻底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和人性,它寻求的只是复兴的时代机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道德在教育领域中的复兴没有任何问题。
二、现代道德是重要的
就当下的学校教育而言,现代道德是重要的吗?笔者认为,现代道德是重要的。
首先,道德不是抽象的、与生活绝缘的存在,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能够满足人们过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而对于何谓美好生活,古与今有着相当的不同,由此就产生了道德的差异以及现代道德产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于美好生活,古代人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们强调按照有差异的“自然天性”生活,强调社会等级秩序的正当性,所以道德的等级性就非常明显。中国古代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以及对至上皇权的尊崇,就是明证。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教改革运动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由、平等、权利成了美好生活的标准,“自然”与“等级”被人抛弃。就中国而言,自鸦片战争后开启的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自发的,而是西方推动的,所以西方所强调的自由、权利、平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道德观的建构。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道德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天命”,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由西方促动亦同时被卷入的现代性运动之中了。返回封闭的古代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非理性的,譬如说,与古代道德相连的“皇权社会”和“臣民社会”已经“烟消云散了”,强行回去,只会导致人们的普遍抵制。面对现代性的不可逆转的浪潮,梁启超基于传统中国有私德和私民而无公德和公民的状况,提出培育具有公德意识的“新民”,是必要的;同样,“五四”一代反对传统道德,提倡现代道德,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同样,新中国成立后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比如关心集体和他人,也是必要和必须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是“小圈子伦理”,不具有公共性和民主性,不能适应现代生活。
其次,若从传统而论,传统并不仅仅指由古代孕育并流传至今的古代传统,也包括由现代孕育并流传至今的现代传统。这意味着,作为现代传统之构成部分的现代道德,必将因为传统自身的绵延和无法抗拒性而成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方面,崇尚古代传统但又客观对待反传统的现代文化的希尔斯说:“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之所以一直在破坏实质性传统,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已经以多种形式培育了某些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有害于实质性传统的理想,而这些理想已经反过来成了传统。人们一直用这些理想来督促统治者和公共舆论。”[1]384对国人来说,更多的是把传统视为古典意义上的传统,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学者高瑞泉评论道:“希尔斯不喜欢近代传统,但并不因此抹杀近代传统;不像汉学界的某些学者,因为憎恶‘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传统,便一味指责‘五四’造成了传统断裂,拒绝承认中国近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已经形成的某些近代传统。它虽然可能不如西方近代传统那么条贯有序,那么成熟,甚至还没有从现实冲突中挣扎脱身,但它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共同意识和习焉不察的共同心理。”[4]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说,由于时代精神的变化,使学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识和能力,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现代道德对学生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在德育内容中,现代道德不仅仅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公民教育”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又重归人们的视野,也可以理解在德育的过程中对学生尊严、人格和自由的尊重和保护。
三、德育内容的尴尬:
传统与现代的紧张
一方面,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传统道德是德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人是现实性的存在,现代道德亦是德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整体性的角度看,历史感与现实感并不冲突,传统道德理应与现代道德融为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遗忘传统而专注时下是不对的,但固守传统而忽视时下也是不对的。当前,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并没有融为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紧张和冲突,笔者称这种现象为德育内容的尴尬——两种道德都是重要的,但它们却无法实现有机整合。这种尴尬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就传统道德来说,它一方面是且应该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但另一方面它自身的特质又使它作为教育内容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具体来说,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不是一种大众道德,而是一种精英道德,并且蕴含着浓厚的官僚政治色彩,其社会化主要依赖于政治制度。不过,中国自晚清以来一系列带有断裂性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尤其是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社会逐步带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人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个人自主意识被唤醒,精英伦理日渐被大众伦理颠覆,国家作为道德的立法者和实施者的角色逐渐遭遇挑战和质疑,国家与道德逐渐呈现分离的态势,这直接导致了传统道德在教育领域这一重要的社会化途径中的衰落。所以,尽管当前的学校德育强调传统道德的重要性,也出现了“国学热”和“读经热”,但传统道德并未真正落实为德育内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道德就失去了通过教育社会化的可能,只是需要知识人对传统道德加以反思和“创造性的转化”,寻求新的社会化基础。
其次,就现代道德而言,它内涵的普遍性也遭遇了传统道德所内涵的特殊性的“抵抗”,这种抵抗使得现代道德难以与传统道德融为有机的整体。
现代道德之为现代道德的根本标识在于它的普遍性,因为它形成并服务于“开放社会”;而传统道德之为传统道德的根本标示在于它的特殊性,因为它形成并服务于“封闭社会”。虽然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性完全取代了特殊性,事实上,尽管经济开放与一体化在逐渐形成,但文化的封闭性与特殊性——文化是民族的——却被人们加以强调。这是可以理解的,“文化就是洞穴”,布卢姆如是说。他分析道:“人需要为自己找个位置,需要给自己定位的意见,那些强调根基重要性的人强烈地表达着这种愿望。与外来者和睦相处的问题,不如成为内部人,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来得重要,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跟个人或民族的健康不相容才是极大的偏狭,而大开放的思想难免会让文化解体。把至善与一己之善牢牢地绑在一起,拒绝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一个民族有着特殊意义的宇宙观,这似乎构成了文化的前提。”[5]12由这种分析,可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封闭”与“开放”之间的紧张,或者说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之间的紧张。
这一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是突出的。众所周知,自我国国门洞开,传统的特殊的道德文化就长期遭受现代的普遍的道德文化的“压迫”和“解构”,但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极大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的逐步确立,传统的民族的道德文化日益被人重视和强调。季羡林先生曾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6]。 事实上,这些年,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而由西方推动的现代性运动与弘扬的现代价值观遭遇质疑。人们相信,道德文化都是相对的,不存在超越的普遍的道德文化,即使存在,那实际也是西方的道德文化披上了普遍性的伪装而已,西方人把自己的道德文化视为普遍,然后向全世界推广,这是一种霸权主义。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世界除了有特殊性,还有普遍性,因为人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有一种追求普遍真理和至善的需求。布卢姆说:“求善与忠诚之间的对立,给人生带来难以消解的紧张。但是,对至善的认识和对拥有它的渴望,却是教化人类的无价之宝。”[5]13其实,撇开这种哲学化的论述,审视当前,自由、权利、尊严实际已经内化到人的血肉之中,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喜欢生活在没有任何尊严的专制和极权社会之中。所以,我们不应仅仅基于民族的立场,拒绝普遍的道德观。
总而言之,当前德育内容的尴尬已成为一个问题。如何反思和转化现代道德与传统道德,使二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健全人格和健全社会的塑造和形成。
参考文献:
[1] 希尔斯.论传统[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