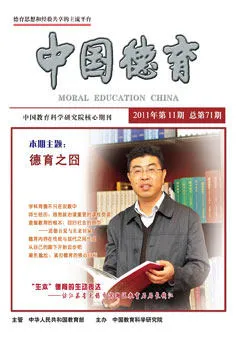道德教育的根本:回归社会的原型
2011-12-29毕世响
中国德育 2011年11期
[摘要] “社会”的原型是土地神和长老神共同形成的人民聚会,那是企求人有饭吃的吃饭教仪式,那本身就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根本是人有饭吃,社会自觉,道德自觉,长老在家,人在场。
[关 键 词] 道德教育;社会原型;社会自觉;道德自觉;长老在家;人在场
[作者简介] 毕世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人最原始的宗教——吃饭教
中国社会自从三皇五帝以来,就一直是农耕文明社会,而当下却处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初级阶段,这个过渡,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明转型,正是这个文明过渡,把我们这个时代和好几代人,都陷落在了既不能固守农业文明道德,也不能遵守工业文明道德的峡谷中。因为,农耕文明完全依靠土地和粮食,现在的人,不能完全依靠土地和粮食,工业文明又没有完全形成,工业文明的道德体系当然也没有完全形成;另外一个契机是,中国人既没有经历过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人文思想洗礼,也没有完成启蒙运动那样的革命,这意味着,中国人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公民道德体系。换句话说,中国人还不是现代化的人,在道德观念上,还处于某种封建主义状态。在生活上,中国人仍然处于“为了吃饭而活着”,或者,“活着是为了吃饭”的生态中,这是中国最原始的宗教——吃饭教。一切教育也都是为了吃饭,一切都围绕吃饭说话。
社会的原型原来就是道德教育
学术研究的一个本源是摸原型,据说社会是进化的,社会进化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社会”是啥意思了。“社会”这个词,在今天的意思大致是“天下”、“国家”、“时代”、“世界”等涵义,而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社会”却是一个带有道德涵义的词,或者,社会本身就是道德教育。社会,具有名词和动词二重性。
中国的农耕文明主要依靠土地和粮食过日子,中国人所谓的“江山社稷”之“社稷”,社是指土地神,稷是指五谷神,在所有的神灵中,这两尊神灵和人的关系最亲近。人敬他们,供奉他们,祭祀他们,娱乐他们,给他们唱戏,形成了社日。古代逐渐形成春社与秋社两个社日,间或有四时致祭者。“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熟;秋祭社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即春天的社日是为了祈求神灵下雨,春雨贵如油,催发禾苗成长;秋天的社日是为了酬谢神灵,禾苗已结果实,五谷丰登,人才会有饭吃,才会活下去。
历史上不少诗人对社日都有灿烂的感情,古代关于社日的诗文很多。
项安世诗中写道:“父老共倾同社酒,儿童齐唱牧牛歌”,老年人和儿童在社日里都沉浸在一时的幸福中。
张演的《社日》诗是这样渲染的: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而杨万里的《观社》诗,则把乡农社日的欢乐,高抬为可以鄙视王侯将相:
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虎头豹面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王侯将相饶尊贵,不慱渠侬一饷癫。
读过点古希腊文字的人,大概容易将社日和希腊人的酒神与狂欢联想在一起。不过中国人的感情是内敛的,道德是克制的,不太容易狂欢,而且老年人和儿童在一起,老年人自重身份,在晚辈面前,甚至不得不装出几分道貌岸然的样子。
社日活动,实际上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社神,就是土地神。要说还有,那就是组织社日活动的人,就是地方长老——长老不一定是年龄大的人,读书人、有家族背景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有德行的人、年长的人、辈分高的人,都可以是长老,也就是地方士绅,他们就是当地的道德权威。所以,地方长老或者地方士绅,虽然不止一个,但在人格上可以算作一个人。古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是“皇权不下乡”,即皇帝的权力,止于县这一级。县以下的乡村,依靠地方长老的道德教化,政府不会派“干部”到乡村来治理。乡村的治理依靠的是地方士绅,地方士绅对乡村的治理,主要是道德约束,因为大家都依靠自己的田地生活,地方士绅不是“国家干部”,“不领国家工资”,完全依靠自己的道德身份规范地方人民;另外一个治理智慧,则是家族伦理,一个地方有一个或者几个家族,每个家族都立族规和祠堂,既笼络族人,保护族人,又威慑族人,这些族规都是伦理的和道德的。这样,就形成了地方的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的最上端是长老,最下端是年幼者,社会清明就以老年人和儿童的生活为标准。“地保”“甲长”“里长”一类的“乡长”“村长”,多听命于地方长老,实际上,有势力的家族都不屑于子弟去当“地保”“甲长”“里长”一类的跑腿人。这样,地方长老就具有民间神灵的精神,他们要教化人民。在社日活动中,大家聚会在一起,这是一个有礼有序的活动,按照长幼有序的伦理精神进行。这是“社会”的原型。
总而言之,社会是由“神”和“人民聚会”形成,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道德教育场景。
当代的道德教育场景,往往是人为地设置,不是自然的教育。如往往把革命烈士陵园一类的地方,设为“道德教育基地”,清明节的时候,学校组织老师和学生,到革命烈士陵园那样的“道德教育基地”里“道德教育”一番,其他时间,任由革命烈士高睡,谁还会端起饭碗、生起孩子而想起革命烈士呢?实际上,应该把革命烈士陵园更多地和知识教育、历史教育结合起来,而知识教育和历史教育,本身就和道德教育是一体的。或者说,把烈士陵园的意义转化为历史和知识的博物馆,才具有真正的道德教育意义。譬如说,一座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就是中国解放战争博物馆,没有关于解放战争的知识,进入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就是逛公园,倒也能够陶冶性情。
“社会”不在场与道德的陷落
当代中国有几个致命的陷落:社会不在场——政府或者国家取代社会;道德不在场——政治取代道德;儿童不在场——教育取代儿童;教育不在场——生活取代教育。这几个陷落,肇始于科举制度的完结,科举制度结束以后,这几个陷落越来越浓烈,当前则达到了极点。
前面说过,社会的原型之一是地方长老或者地方士绅,他们具备人世间准神的人格,是活着的祖宗,是道统的象征,是道德教化的人的因素。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取消以后,读书人逐渐失去了尊崇的道德地位,取代他们的逐渐成为地方流氓式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用地方干部彻底取代了传统的士绅,即使大学校长,也往往是老八路出身。政府把士绅打成“剥削者”“人民的敌人”,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改造运动,那些士绅,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彻底涤荡掉了——这也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四维道德体系扫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体系。然而,在这个政治体系中,在很长的时间,地方干部与文化、知识、道德和教育没有关系,即使现在,地方干部仍然不以文化、知识、道德和教育为荣耀。至于现在的学校校长——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到底有没有文化、知识、道德和教育气质,那是很诡异阴暗的事情。现在的“中小学里所鼓捣的把戏,至少有70%不是教育,只是升学考试,升学考试和教育没有关系,升学考试的目的是为了考大学,考大学是为了职业,职业是为了个人的生活和生存……反而,教育致穷倒成了教育的气质。文化教育之济世救民的情怀,已经被文化教育自己驱逐出了自己的精神,这是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教育悲哀。”[1]。
当下有人呼吁地方社会恢复家族治理,未必知道其本质应该是恢复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道德地位,这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一则已经没有了地方士绅,二则地方社会已经不能完全依靠过去那种家族伦理治理,根本原因在于,在家族伦理治理的年代,人属于家族,人不属于社会。民主时代的人,应该属于社会,是社会的公民,而不应该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政权的私民或者臣民。民主社会,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担当民众的一切。“古代是家庭和父母对儿童负责,不是国家或社会对儿童负责。儿童是家庭和父母的私民,不是社会的公民。如在科举时代,国家只管最后的结果,一个人考成了秀才、举人或进士,成为社会贤达或国家官员,国家给予荣耀,却不管他们怎么上学,读书上进是自己家庭的事情。这样的意思,一直持续到近代社会。废除科举和西学东渐以后,民主思想逐步进入中国社会,学校教育思想和制度都西化起来了。然而,儿童那家庭和父母的私民身份,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发生了政治性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又回到了古代意义——家庭和父母的私民,只有父母对儿童的前途最终负责。”[2]社会一方面进步了,人人可以接受学校教育,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又巨大地退步了,因为几千年前都是家庭担待儿童,几千年以后的今天,国家仍然把儿童扔给家庭,扔给父母。国家、家庭和社会,是三个部落,国家以政治意义要求人,家庭是实实在在的供养人,社会悬空了。
在教育普及的今天,人人似乎都是读书人了,而人人都不再是道德符号,只是生存动物。政治把持的“此社会”,不是长老把持的“彼社会”。社会已经不在场,已经没有了神灵。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们对之思考得越是持久和深入,就越是能在我们心中引起惊奇和敬畏,这就是星云密布的苍穹和人类心中的道德律。”这也是康德的墓志铭。当民众的心灵中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对苍穹的惊奇,道德教育也就陷落了。
道德教育基于人的在场
当代最大的吊诡是,似乎社会越来越发达,而人的生活却越来越沉重,人生的意义退回到最基本的生存上去了,似乎社会也不再鼓励人有远大的理性与抱负,人只要考虑今天有没有饭吃,接受教育是为了考虑明天的饭怎么吃得上。这样,社会是社会,人是人,对社会来说,人已经不在场。
这个文明过渡初期的儿童,也许是历史上最沉重的几代人,他们很多人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是残酷的,因为父母为生计奔波于外,他们是父母双全的孤儿;而他们所处的社会,早已经没有了热闹与欢快。他们心灵的底子是寂寥的。对这些青少年来说,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一切,包括父母,都不在自己的灵魂之中。反过来说,这些青少年,是不在场中的人。他们中老年以后,怎么回忆自己空荡荡的童年?他们永远写不出来《社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或者说,他们永远成不了鲁迅,无论他们怎么学习鲁迅的著作。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一生作品中最激荡人心的,莫不是来自他们童年的生活经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鲁迅的教育经历,《孔乙己》、咸亨酒店、茴香豆,已经成为一般的人对绍兴甚至对鲁迅的记忆。鲁迅少年时代看的《社戏》,就是民间社日的一瞥。当代仍然有民间火辣辣的社火,不过时间往往挪到了过年期间,因为过年民众才有喘息的借口,才可以坐下来喝杯酒,社火也把年过得有些神意。社火往往以走高跷、划旱船、扭秧歌等为形式,锣鼓震天响,人们穿戴打扮得大红大绿,俗气、土气、喜气、古拙气、率真气直冲霄汉。不知道如此夸张的灵魂,有没有把神灵哄高兴,倒是人一年下来,能够享受几天人的味道。只是,现在许多人并不知道社火原来是古代的社日,是为了娱神和酬神的膜拜,那也好,倒可以娱人酬人,神为人而设。这样的浓烈,种在儿童青少年的心灵中,成为他们人生的底色。
周作人则把北京的一切,都与他童年和少年在老家绍兴的山水人物经历比拟,虽然他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浙江老家的野菜。他在《喝茶》中说的喝茶,纯粹是南方的喝茶韵味: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亦断不可少。
他在文中又谈到喝茶所配的茶食,说起他家乡昌安门外的三脚桥旁,一家叫周德和的豆腐店,所制的茶干最有名。
这样的喝茶,使读书人容易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喝茶:收得梅花上的雪,储于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埋在地下,五年以后才打开,将水取出,亲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不假手于人,用来泡茶。而喝茶的杯子,都是苏东坡等高人雅士用过的是“瓟斝”,“点犀斝”、“绿玉斗”等类珍稀。而且,喝茶讲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驴了”。
读这样的文字,虽然觉得妙玉有几分造作,倒真羡慕她的才情;至于周作人在“瓦屋纸窗”的喝茶,勉强还做得到,总觉得那才是人的生活,因为,人在场。
社会自觉与道德教育
今天有社会学,而且还是一门非常热闹的学问,可是,社会和社会学的本意,并不是那么清晰,正像这个教育普及的时代,教育的本意——做人——已经杳然一样。
早期,严复把西方的《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影响甚远。那个群学,曾经被中国学者理解为或者赋予“组织教育群众之学、拯救中国于危亡之学”[3]。有学者说:“英文Sociology,严复译为群学,现在译为社会学。从广义方面讲,包含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而当时维新派普遍使用的则是狭义的群学,即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学说。”[4]还有学者指出:“在晚清维新者心中,群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社会学……;二,由字面意义引申而来,专指合群的学问。”[5]。简单来说,当时的“群学”和“社会学”,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群,在中国学者意识里的意思,主要是合群,创办各种学会,从而把各种各样的运动如维新运动推向高峰。总而言之,中国学者早期理解的“群学”,是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然而,早期西方的社会学是一门中性学问,基本上是研究社会现象,社会学是描述性的。譬如,当年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教授,经常用美国的黑帮来讲解,这不等于中国教授欣赏美国黑帮的德行,更不等于中国教授教育中国大学生去干黑帮勾当,那是学术讲授。而一个中国大学生一辈子都不会和美国黑帮有什么交易。同样,讲美国黑帮的中国教授,一定不是美国黑帮的帮主或者喽罗。社会现象是社会现象,人是人,社会学是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学给社会建设性和劝导性的纠正和谴责,不能代替社会的道德意义。然而,它确实对社会有道德引导意义,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为迪尔凯姆,也有人译为杜尔克姆)的社会学著作《自杀论》,对整个世界有巨大教育意义。
西方当代社会学则把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行动者对社会的实践关系,人是行动者,人对社会有积极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人无可奈何于社会现象,这样的社会学,就不再是社会与人是两张皮的社会学。不过,当下社会学所理解的社会,和以前的社会,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了:过去的社会是大社会概念,现在的社会是小社会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是人不在场,西方的社会,是支离破碎。
中国学者一百年前,对社会学的初步理解,实际上就一下子击中了社会精神,而一百年以后,欧洲社会学的精神,实际上正向中国学者的理解回归呢。这应该是社会自觉,也是道德教育的自觉。
道德自觉与长老回家
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有道德传统的社会,提起中国,人们总会说,或者总会自诩为礼仪之邦,会想到礼义廉耻,想到孔孟之道。那是古代中国社会,古代中国民众,是有礼义廉耻的民众,是饱受道德浸淫的民众。中国的一切骄傲与光荣都在古代,不在现代,现代中国没有什么可以拿到世界上去说话的。中国的思想家也全在古代社会。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精神是打倒、摧毁乃至毁灭与沉沦,哲学的根本精神是批判与反思,而打倒、摧毁乃至毁灭与沉沦,和哲学上的批判反思根本是背道而驰的反道德乃至反人类行径。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四运动,就开了打倒、摧毁乃至毁灭与沉沦的先河,这个打倒、摧毁乃至毁灭与沉沦,一直延续到当下。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是中国的道德之根;“文革”打倒知识、文化与知识分子,打倒的是中国的道统担待者;现在的金钱与权力经济打倒礼义廉耻,打倒的是中国的立国之本。
中国社会传统的灾难是旱灾、水灾、虫灾(蝗虫)、风灾、冰雹、兵灾、匪灾、官灾等。灾难是社会的常态,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有善有恶的二元社会。灾难过后,仍然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现代社会,依靠政治保证人民,政治担待人民的道德和智慧。终极道德关怀则把我们带到纯善无恶的一元世界。这个时代,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回复到道德和社会的原型。其途径有二:一是道德自觉,一是长老回家。实际上,所有民族的圣人,都是以道德开启人民的眼睛和嘴巴,使人民从混沌和无知状态,进入诉说智慧和道德状态。接受了圣人教化的人,成为社会长老,他们再对人民教化。每个时代的圣人和社会长老,都对时代民众进行时代教育。进入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当代最大的使命,现代化的人民,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思想和德性——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启蒙,这个启蒙,就是人民的道德自觉,对现代化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方式的自觉。那么,谁来启蒙人民呢?仍然是社会长老——有知识、有道德的人。长老是社会的父与祖,没有父与祖的家庭,是不幸的家庭。
教育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生活本身,教育却又沦落为为了吃饭而已,吃饭,要长老带领我们吃。我们要把长老重新请回来。
参考文献:
[1] 毕世响.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新趋势之形而上臆谈——完整的“中国人”观念之积淀[J].教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