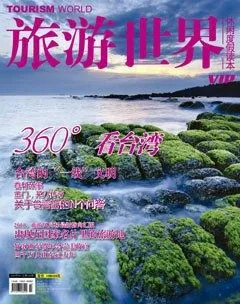《天赐》七年.胶片.鸟之恋
2011-12-29李芃芃
旅游世界 2011年3期




这是一个从小就爱鸟的人的梦想,是几个并不那么专业的人,花了7年时间驻扎在威海的海驴岛拍摄的纪录片,是一部投资700万、经历几次资金链断裂和生死考验的作品,还是一个用镜头客观记录人类之外另一个世界的鸟的故事。正如《天赐》的导演孙宪所说,这部电影也许拍得有点“笨”,但看过之后的人都被它的真诚和勇敢,以及记录的鸟的故事所深深打动。
电影开头有这么一句话:电影拍摄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我想,《天赐》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鸟的故事,和海驴岛不为人知的美丽,更传达了一种精神,一种坚持甚至有些固执的精神。
有史以来最真诚的一场拍摄
像蜘蛛人一样拍电影
拍摄周期是每年的4月下旬到8月初,岛上温差很大,5月上旬还要穿羽绒服,一进6月气温陡增,近40℃的地表温度要持续两个半月,摄制组的成员每人每年脸都要爆3次皮,这还不是最难受的,为了更近地接近黄嘴白鹭,他们必须攀爬到64米高垂直的崖壁拍摄,由于那里的岩石风化得非常严重,每一步都隐藏着危险,摄制组的小王就在崖壁上摔伤了腿,至今仍有后遗症,导演也曾让滚落的石块打破了脑袋,但为了完成目标镜头,他们都义无返顾。
“三脚架”和豆包的故事
7个繁殖期的拍摄,剧组经历了几位助手离开队伍,也遭遇资金链断裂影片拍摄无法为继,只有包括导演在内的三个伙伴坚持到最后,他们彼此形成了默契,由于三个人各守一角拍摄,大家送给他们一个外号——“三脚架”。
但凡拍摄自然环境的人都会竭力追求画面的完美,最初时剧组甚至也把摇臂带到了岛上,然而随着拍摄的深入,他们发现岛上的这些鸟大都筑巢于崖壁或者峰顶上,别说摇臂,就是一种中型的三脚架也难以平稳地摆放,因为超过1平米的机位都很难找。于是导演和摄影师苦思冥想,最终采取了一种很“土”但非常实用的方法解决了机器稳定和水平的问题,他们缝制了两个布袋,每袋装10斤豆子,它可以任意放在任何一块石头上,再把摄像机放到上面,不仅稳定,水平的调整也更迅速了,唯一不足的是不能摇镜头。黄豆袋子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豆子是圆的,变形快而轻,二是一旦没了粮食还可以炒了来吃,有一次剧组因为大风而无法返回,他们在岛上不得不吃野菜,豆子变成了难得的美味。这部电影拍摄之艰难也可想而知。
在那个世界,人只是鸟的配角
在岛上拍摄的最后三年,剧组成员与鸟实现了零距离接触,镜头拍小鸟破壳,成鸟会啄他们的镜头,甚至落在他们的摄像机上,而这种状况常常使“主角”被“群众演员”抢了镜头。7年中,他们见过许多破壳而出的小生命在呼吸第一口空气后脆弱地蠕动,也目睹了很多夭折的生命无声地化为泥尘,更遇到过几次成鸟在遭到意外伤害后躲在一隅静静等待死神到来的悲壮,在鸟的世界里,无论我们有多少情绪,用镜头记录下那生命的时刻,是《天赐》能做的唯一的事,也是最好的事。
导演孙宪:我们欠鸟很多
见到孙宪导演,是在济南首映后的影院礼堂,电影结束,灯已亮了很久,他被山东小记者团的一群穿红马甲的小记者团团包围着,一遍遍回答着孩子们稚嫩的提问,好不容易等到提问结束,孩子们又纷纷涌上来签名和合照,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
很难想象,面前这个穿着有些肥大的风衣,脸上写满疲惫与和蔼的平凡中年人,会凭借铁人一样的意志克服一次次艰难险阻,拍下这部诚意十足的电影。他身上没有大腕导演的气场,甚至普通得像邻居大叔,但言谈之中还是能捕捉到他不同常人的坚持与智慧。
在孙导的博客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常常弄不清活着和存在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对我自己而言只有活着才是存在的。这可能违背了严谨的学者对事物的科学态度,但我不是哲学家更不是科学家。仰望天空最羡慕流星划过的火焰,多年来每次见它便有了一种冲动——燃烧自己。” 有些人也许天赋寻常,但他仍旧能够完成一些事,一些大事,无论成功与否,这个过程就是一份独一无二的人生记忆。
导演Q&A
记者:为什么叫《天赐》这个名字?
孙宪: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我不想说教,只想客观地记录。
记者:这种客观,比如看着蛇吃了幼鸟,对一些观众尤其是小朋友是不是太残忍了?
孙宪:有些看过电影的人就问,你们拍摄的时候看到蛇吃鸟,为什么不阻止?我就很无奈,我回答他,我阻止了蛇,对蛇是不公平的,它的繁殖期可能就靠这一只鸟。这是一个生态规律,不是人的意志所想象的那样,更不是人的强制干预就能解决的问题,孩子更应该知道这一点。
记者:我想知道你刚刚见到成片后是什么心情。
孙宪:第一个拷贝出来的那天,洗印厂打电话让我去看颜色,当我接过5个拷贝的第一本的时候,我抱着它在洗印厂门口哗哗地哭,就抱着那么一个铁盒子。太难了,我想不管是丑还是漂亮,孩子出来了,这大概跟做父亲的心情是一样的。
记者:给我们讲讲拍摄过程中最难的一次。
孙宪:其实不止一次,有三四次。有一次为了拍雨景,我们攀到悬崖上等暴雨,安全措施就是一根绳子,那个岩石是松动的,有水还发滑,那根绳子就是我和我兄弟的生命线,后来一个雷电打过来,我的头发真的竖起来了。后来我开玩笑,谁说周星驰的电影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真的被雷击过,知道那个滋味,头发真是爆炸的,石头还哗啦哗啦掉下来,那个时候迷迷糊糊地知道不能松手,松手就完了。
记者:值吗?
孙宪: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你真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选择投入可能相对容易一些,选择放弃更难,只能说我别无选择。
记者:对你来说,梦想意味着什么?
孙宪:我没想过这么远,也没想过这个电影有什么意义,第一,我想做的事做完了,第二,做完后我身边还有这么多不离不弃的兄弟,其他的都不重要。
记者:这部电影展现了自然的赐予,那么人的足迹对鸟的世界来说,是不是一种矛盾?
孙宪:所以我在电影中一直没有提那个海岛的名字,我不希望它被过多开发。其实黑尾鸥的领地之争为何越来越激烈,某种程度上也是它们生活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我们还救过很多只因为误食带鱼钩的鱼而几乎被卡死的黑尾鸥,我总觉得我们欠鸟很多。
记者:您未来还有什么打算?
孙宪:我希望这个电影能够走得远一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做跟鸟有关系的事情,它一直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人类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那只黑尾鸥母亲为何跳崖自尽。
黑尾鸥:海岛武士
电影《天赐》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居住在海岛上的黑尾鸥,他们炯炯的眼神、黑色的翅膀和强烈的地域和家族意识都让人折服。特别是电影中小黑尾鸥的妈妈在跟别的家族打架后翅膀受伤,再也无法飞翔,也许是出于动物的习性本能,也许是怕连累小黑尾鸥,它选择了跳下悬崖结束自己的生命。
黑尾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候鸟,它只在每年3月下旬到7月下旬的繁殖季节,集中在山东和福建沿海的无人海岛上繁育,繁殖期结束后,所有的黑尾鸥都会离开繁殖地,却并不一定向南迁徙。
海岛武士:黑尾鸥喙尖似鹰,整体为黄色,但在尖端有一红斑,红斑中间夹杂有黑色环带。脚和蹼呈浅黄色,叫声像猫叫,不少地方又称之为“海猫子”。黑尾鸥体型匀称矫健,习性好斗,好像是一个个穿白衣、着黑披风的武士。
集结回归:每年春节前后,黑尾鸥就开始在繁殖地附近海岸集结,这个季节,海浪中裹挟着的蜢子虾,是黑尾鸥冬季最好的食物,集结中的黑尾鸥很遵守纪律,回归日期未到,没有一直黑尾鸥抢先飞回繁殖地安家。
练飞自立:幼鸥在还不能飞翔时就经常跃跃欲试地扇动翅膀,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成长,飞羽基本成型后就开始学飞。起初,幼鸥要借助风的力量,将自己抬起,但很快就又落到悬崖边,确切地说,它们是在漂浮,经过多次重复,它们在空中停留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而且可以在空中扇动翅膀,自己制造飞翔的动力。在学飞的过程中,父母会不停地示范,对于那些有恐高症的孩子,父母只好将它们推下悬崖,只有这样它们将来才能够独立生存。
淡水洗澡:在海岛上的黑尾鸥会经常飞回陆地,寻找淡水湖河洗澡,就好像人们洗完海澡还要使用淡水冲洗一样。黑尾鸥洗淡水澡的地方距离它们的海岛20公里以内,确保能在半天内往返,如果没有人为干扰,洗澡的地点会常年不变。
秋天告别:每年7月下旬,当小黑尾鸥都能够飞翔并自食其力的时候,黑尾鸥开始离开海岛,到8月中旬,岛上就几乎看不到黑尾鸥了。离开海岛的黑尾鸥,有的还流连于附近的海岸,但大多数都散居流浪越冬去了,直到来年的春天,开始又一个季节的生命轮回。
编辑 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