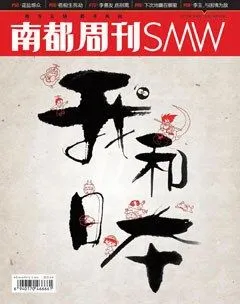联合国来了中国实习生
2011-12-29黄修毅吴思凡郑文
南都周刊 2011年11期


还没毕业,他们就已是HR眼中的香饽饽,饭碗不用愁。在竞争激烈的应届生就业市场上,他们底气十足,很大原因是个人简历上写着“有联合国实习经验”。
不培养成就感,但培养使命感
“和在国际公司干活总体上差不多,只是在工作标准上,才感受到联合国特有的使命感。”
拥有联合国实习履历,在国内高校学生中还是凤毛麟角。方玮,复旦大学2006级本科毕业生,如今是强生市场部的管理培训生;谭宗洋,清华大学2007级研究生,现在担任《China Daily》的驻京记者。陈思,复旦大学在读研究生三年级,忙于促成世界轮椅基金会在中国的慈善项目,她的职业志向是成为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他们三人受惠于“杜孟项目”,通过校园选拔,2009年、2010年先后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和曼谷的机构实习。而华东师范大学2004级的研究生潘菁蕴,早在2007年曾被上海本地媒体称为“第一位在联合国总部实习的国内学生”,并带动了两名同学相继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实习。
时至今日,他们中有人已经步入了工作岗位,有人还要继续深造,但在联合国实习的经历,已经在他们的人生中发酵。
本国文化代言人
方玮很少在同事面前主动谈起这段不寻常的实习经历。但是,这个落落大方的女生的美式口音、欧派礼仪乃至直率的眼神,都让同事觉得她“登过大场面”。
去年八月,结束了在日内瓦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总部两个多月的实习后,方玮开始学习法语。“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环境办公,只掌握一门英文是不够的。法语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在工作中使用几率也很高。基本上,见亚洲人说英语,而和欧洲同事之间则讲法语。”
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实习时,方玮小小的格子间被来自世界各国的同事所包围。大家操着带古怪口音的英文,难免会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复杂了,“最费劲的是和印度、日本的同事交流。但时间一长,也就听惯了。”
语言的障碍可以通过语言能力的提高来弥补,但在国际化的办公环境中,文化碰撞则让同事之间敏感小心得多。实习时,方玮和同事讨论一个符号设计,用于警示“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两个交缠在一块儿的小人,摆出露骨的性行为姿势。同事们颇有些为难地看着方玮,好像生怕冒犯了这个中国姑娘。
“大多数老外骨子里还是觉得中国人保守。他们怕艾滋病宣传画和中国人的审美取向不一样,就小心翼翼地问我能否接受,我觉得没什么,反倒让他们吃惊。”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在联合国自然被当成了各自文化的代言人。
这个“甲方”不好做
“不要看联合国好像高高在上,扮演着国际社会调停人的角色,其实,它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运作起来就像很多小事务所,艾滋病规划署是其中一个。”方玮说。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多采用项目制,由项目总监(Director)挑头负责。工作人员的专业级别从P1到P5,再加上D1\\D2,实习生位于整个人员架构的最底层。
方玮也曾在4A广告公司实习过,让她略感惊讶的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外宣项目,也要直接负责和供应商沟通,乃至杀价。“感觉我们就是合同中的甲方,再把工作分包给商业公司做,只是我们的项目目的是非功利的。”
方玮与同事们的工作是负责运营一个为艾滋病人服务的社交网站,类似于facebook,但有更好的私密性。这个平台还被用来推广全球艾滋病大会。整个工作的流程类似公关公司,头脑风暴、workshop等那套公司里的“惯用伎俩”在联合国办公时照样施展。
每位实习生都有一位指定导师,并向他直系汇报工作,而分派给实习生的任务通常和各自的专业领域密切相关。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方玮、陈思等人负责新闻简报、大会筹备等工作,而出自华师大英语专业的潘菁蕴和她的同学们则专攻文件翻译和术语校准。
每天上班例行的碰头会后,同事们就各自钻进格子间,一整天与电脑相对。“和在国际公司干活总体上差不多,只是在工作标准上,才感受到联合国特有的使命感。”方玮说。一份报告易二三十稿是常事,只因为一个标点的错误,就要重新建一个PDF文档。
从实习到入职,距离还很远
联合国作为决策性的国际组织,一旦进入其内部运作,首先要立足的却是做好服务性的细节工作。“工作务实却十分琐碎,可不是个容易培养成就感的地方。”这是联合国实习生们的一致感慨。但在和记者的沟通过程中,他们的不温不火、条理清晰,似乎是这段不寻常的实习经历给他们贴上的共同标签。
联合国实习归来不久,谭宗洋就把参与高规格国际会议的经验,融入到博鳌亚洲论坛的组织工作中;陈思则在世博会期间担任了印度馆的新闻发言人,并在联合国荣誉日上再次邂逅了曼谷的老同事。她的一位师姐,毕业之后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ESCAP)工作,现在已经被调任往联合国纽约总部。
“要成为一名正式的联合国员工,从实习到工作,距离还很远。”方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据她所见,大部分普通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都拥有博士以上学历,和丰富的跨文化生活阅历。而在谭宗洋看来,除了能胜任多元文化工作环境,要想成为一名联合国员工,还必须是某方面的专家,对特定的领域或行业有深入的了解。
目前联合国工作者的主力年龄段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群。“联合国同事有很多之前做的是不同的职业,最后选择在联合国落脚,也没有什么太高的理想性的东西,而是安心安稳地做好一个国际公务员。”方玮说。
还在念研究生的陈思,干脆把自己的毕业论文课题也转向了国际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慈善事业。她一边敲着论文,一边还在参与促成世界轮椅基金会在中国的慈善项目。她说,“我不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非要做成什么不可。但无论有没有经济基础,我都会去做一些公益的事。联合国的非功利气氛,给人与人之间带来的宽松感觉,才是我所向往的。”
紧张、严肃、活泼
去国外实习开销大吗?实习生的工作流程跟国内有什么不同,除了工作,业余时间都干些啥?
实习生小S,国内某重点高校2005级学生,2009年6月到8月期间赴联合国纽约总部实习。以下是他的自述:
晨间例会
九点。见面直接谈公事,没有人先泡杯茶。
所有部门同事在小会议室集合。交代昨天的工作进展,分派今天的任务。导师不时在我耳边附语。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部门专业性较强,最初几天,还会有一些听力障碍。我一手笔记本,一手电子辞典,现学现用。那些暧昧难明的缩写干脆先放一边,等会后问同事。
以下略去几百字,工作中啦。
安检
八点半正式上班,但我提早出门了。早就听说,联合国的安检最森严。这不,被形容成“一副碗筷”造型的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从纽约第1大道46街望过去,总部大厦就像一根插在水里的筷子,密密麻麻的人龙像是折了一下的大楼投影。
在联合国总部,实习生的胸卡是巧克力色,正式员工的胸牌在对角线上有红白条纹,而大使团的胸牌一色深红。胸卡的色泽越暗,要过滤的安检次数也越多。排在我们这一行前面的男女,解头发,提裤子……让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震惊了。原来,除了不允许携带液状物品进入总部大楼,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也要取下,怪不得我见到的女同事们都没有戴饰品的。
实习生BBS
十点半。饭点未到,联合国内网专设的实习生BBS已经活跃起来了。
话题只有一个:拉人,拼桌,吃饭。我扫了一圈,好评最多的是中国菜和希腊菜(莫非大家都是重口味?)。作为不多的来自中国内地的实习生,我自然被当成了饮食咨询顾问。指点鲁浙沪粤八大菜系,其实也就是画个饼。可能是鉴于我的嘴上功夫,11点的时候我已经收到了四五份进餐邀请。
工作也是学习
进入联合国实习,必修的一课是《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组织结构和安全知识。除此之外,到特定的下属机构,还需要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虽然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但在进入这个部门之前,我在上海做了一项相关研究,也算有所准备。在近三个月的实习期过后,我甚至和另一位实习同学合著了一篇论文,回国后发表在专业杂志上。
周末轰趴homeparty
工作之余,联合国同事们间的相处就像在过一个文化夏令营。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受邀到同事家吃饭,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地板上坐得到处都是人,相互品尝各自国家的风味。只是在进门要不要脱鞋这样的小细节上我一定尾随在别人后面,身怕踩到“雷”。
8小时之外
纽约同事带我去布鲁克林、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馆……逛不完的展;曼谷的同学,每天五点下班前会遭遇一场阵雨,他们习惯了在办公楼里避一避,再坐上满街招之即来的tooktook(泰国三轮车)回公寓。日内瓦的同学,在欧洲日不落至晚十点的漫长白夜里,在日内瓦湖畔漫谈,不夜不归。
Coffee Break
办公室的转角有个小茶吧。巴西的咖啡,比利时的巧克力,都是同事们从家乡带来的。我还收到过大堡礁的小段珊瑚,是一位澳大利亚同事带来的小礼物。我把随身带的几个中国结也摆在那里,想不到同事们都如获至宝地拿回去收着了。
出席大会
选举5个非常任理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