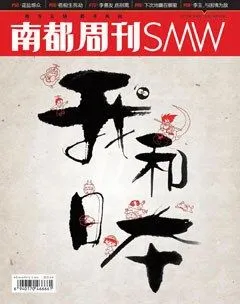东瀛往事
2011-12-29陈言
南都周刊 2011年11期

这个国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像转眼间开放的樱花一样繁盛起来。我相信日本有这个能力。
我是2003那一年,离开日本回国的。有人问起我,会不会对日本的生活比较留恋,我不知道如何作答。其实回国之后,我每年也都有数次机会去日本,这到底是“去”还是“回”?其实,我倒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日本,如果不曾离开,又何谈留恋?
写起我和日本、和日本朋友们的故事总觉得无从落笔。知道的故事多,熟悉的朋友多,从老师、同学、学生、媒体同仁,到经济学家、企业家,再到政界的普通官员、市长甚至首相一级的政治家,他们在我生命中的一些时刻进进出出,我甚至没有细想过这些人对于我的意义,只是温暖而亲近。这种情意也无从表达,只是在这次地震后,所有的感情都变成担忧。
在3月11日后的几天里,我打了几十个电话去日本,往来日本的E-mail也有数百封,知道他们都平安,才觉得安慰。尽管猜测一些离震区较远的朋友,应该是安全,但仍要打个电话过去了,才觉安心。现在回头想想,自己的朋友,从数量上,日本人甚至比中国人还多。
在国内媒体上,对于日本地震和核电站事故的报道中,日本人面对灾难的从容、有序,日本媒体在信息披露和稳定民众情绪中起到的作用,甚至日本官员的尽责都给中国民众留下比较深的印象。这些都唤起很多中国人对我们邻近民族的好奇和敬意。我在日本十多年的经历,那些感性而零碎的观感片段,也随之被唤回,那是日本于我又模糊又清晰的另外一个面孔。
“天皇不走,我们也不会走”
地震之后,我给东京的朋友吉川明希打电话,她非常的镇静,告诉我一切平安,并向我描述了地铁停运后的状态——蜿蜒的人流向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二十几公里远的自家徒步走回去。从东京周边的公路上到处是人,路两旁不时会看见不少人家的门前贴出“我家厕所对外开放”、“免费供应热水”等字样的纸条,为那些步行的路人提供着一点力所能及的服务。
那是我可以想象的一种秩序井然的状态,是我所熟悉的日本。
吉川是一个我认识了20多年的老朋友。1989年,我刚到东京大学读书时也兼职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她那时候正好开了一家翻译公司,我因此认识了她。曾经做过日本著名政治家后滕田的秘书的她是典型的日本女强人类型:平时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发起火来则会大声斥责甚至破口大骂,一旦遇到大事又是出奇的镇定、理智。
福岛核电站的核泄露事件之后,我还是有点担忧,问吉川以及一些朋友要不要离开东京,或者到北京暂时躲避一下,他们都说不用。我起初有点不解,即使不离开日本,开车去西部比较安全的地区,也很容易,为什么就不离开东京呢?后来感觉,他们还是比较相信政府。他们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天皇都没走,他们当然也不走;二是日本的精英们比如高级官员、媒体们都没走,普通人当然也没有走的必要;第三则是在东京有军事基地的美国人也没走,一旦真有什么事,美国人应该早就跑了。
信用至上
那是1989年4月,我第一次到日本,印象里就是繁华,真是不能想象的那种繁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让很多中国人羡慕的就是其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其带来的那种繁华,现在在中国也出现了许多繁荣都市,这种光环反而退了色。
当时的日本之富庶触目可及,林立的楼宇,飞速的新干线,对于从物质匮乏的中国来的留学生而言,还有一件新鲜事:随便走在街上,都能捡个电器回来——冰箱、游戏机、洗衣机、Thi4vILXMSyveY30/+UlbA==电视……当时我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朋友,就总换冰箱,捡一个回来,用一段时间扔出去,再弄一个回来。电脑那时在国内还很少见,在日本街头,也可以捡到,拿回来还都是好用的。
那时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当时中国的GDP,只是日本的1/10左右吧,人均的1/100。那种经济迅速发展的景象给我很大的冲击,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我大学时的专业是日语,毕业后在国内做了5年日语老师,后来当了两年的翻译,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时候,本来是计划学习新闻,并且已经完成了两年的学业,但后来还是决心改学经济,因为我当时深刻体会到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要深入学习和了解日本最终还是要从经济入手,所以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