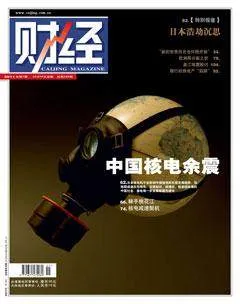核电减速契机
2011-12-29李红兵李晨蕾朱玥
财经 2011年7期
日本核泄漏事故对中国核工业界的震动不亚于日本近海的9级地震。
过去五年,中国经历了跃进式的核电建设。各省市经核准可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34台,在建机组28台,另有16台机组已在开展土地环评等前期工作。全世界的在建核电站中40%在中国。
“福岛的冲击太大了,这些天我天天盯着看日本的事态发展,我搞了一辈子核电,这次真是感同身受的教育!” 3月18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原主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华祝仍心有余悸。
日本震后最初几天,中国核电业界的反应一度较为乐观,认为国内核电站技术远较福岛核电站领先,类似的核泄漏事故不会在中国发生。但在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四项决定后,气氛很快发生变化,此前活跃的核电业内人士开始噤声。
不过很快,悲观情绪又被谨慎乐观所取代。多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在3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除了广为报道的核电“国四条”,积极发展核电的既定方针亦得到重申。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核电业界专家也表示,措施虽然严厉,但不会造成中国核电工业的停滞。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郁祖盛表示,国务院的这几项决定是及时的,这个时候有必要给中国的核电工业敲响警钟,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会因噎废食。张华祝也表示,现在确实应该“停一停,看一看”,但 “中国核电事业会继续发展,对此我很有信心”。
是减速,不是停车。“3·16”一周之后,业界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从1981年国务院批准秦山一期核电站开工建设至今,中国核电工业已走过整整30年。借此减速之机,重审过去五年的核电跃进,重思过去30年的发展之路,对中国核电的未来至关重要。
核电红利
各方对核电趋之若鹜,显见的动因是发展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的需要,鲜为人知的则是核电建设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
2010年末,全国已建成运行的核电装机达1080万千瓦,在建的有3097万千瓦,两者相加已超过4000万千瓦,提前十年完成了2007年10月公布的《国家核电中长期规划》设定的目标。
对核电如此趋之若鹜,显见的动因是发展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的需要。按照张华祝对《财经》记者的说法,“目前核电装机容量只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1.1%,规模实在太小,即使到2020年装机容量达到8000万千瓦,核电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也只能达到3.5%左右,在强大的节能减排压力下,核电未来发展潜力还相当大。”
鲜为人知的则是核电大跃进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在业内,核电站被称为“印钞机”。
一般情况下,一个核反应堆至少会配有两台发电机组。以一台100万千瓦的功率计算,一台机组一小时的发电量为100万千瓦时,如果全天满负荷发电,一天发电量为2400万千瓦时,如果两台机组全年满负荷发电, 一年发电量高达175.2亿千瓦时。
当前,国内核电上网电价实行的仍然是成本定价,核电站的投入成本越高,上网定价也越高,核电上网电价大致在0.30元-0.48元/千瓦时之间。即使按照0.3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计算,两台10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一年营收达52.56亿元。
当然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调峰需要,核电站机组通常不能满负荷发电。但即使扣除这一因素,由于核电投产后日常运营费用极少,同火电相比,核电的利润仍然十分惊人。核电站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前期设计和建造阶段。
3月23日,哈尔滨电气集团哈动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哈电集团核电事业部部长韩建伟告诉《财经》记者,核电站成本主要由前期工程费、土建工程费、设备采购费、安装工程费、设计及工程管理费、工程建设管理费等构成,其中设备采购费占大约55%,核岛、常规岛、BOP(外围设施)这三部分的成本构成比例大约为5∶3∶2。
核电站一般在15年内能回收成本,15年投资期过后,核电站开始进入纯盈利期。因此,核电站使用寿命的长短对核电站的盈利水平至关重要,而近年来国外核电站也掀起了申请延寿的风潮。就连此次出事的日本福岛核电站,原本也计划延寿20年。
随着技术的进步,延长核电站的使用寿命正在变得越来越可行。目前国内投入运营的核电站,都是基于二代技术设计建造的,运营寿命一般都是40年,随着以AP1000为代表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应用,第三代核电站的设计寿命已经从40年提升至60年。
2010年初国元证券的报告预计,保守数字,未来十年中国核电投资市场总额将为6120亿元,其中核电设备的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核电蛋糕丰盛,但有缘分食者寥寥。高准入门槛使得整个核电产业链条高度集中。目前国内取得核电设备制造资质的仅有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中国一重和中国二重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
除了核电运营商和设备制造企业,地方政府的推动,对核电大干快上的作用也同等重要。过去八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超过10%,电力需求快速增加,在那些需要输入能源的经济大省,拉闸限电更是屡屡出现。
随着增长中心的西移,核电站也正从沿海大举向内陆扩张。在广东、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加快发展核电的同时,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正在推进“东中部核电带”的形成,而地方长官带队进京跑核电项目也成一景。
对地方政府而言,核电站首先意味着稳定而便宜的电力供应。专业资料显示,1克铀235完全裂变能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3吨标准煤,一座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的核电站,年均消耗核燃料仅为30吨,而同样规模的火电厂则需消耗260万吨标准煤。
对电力用户而言,考虑到环境运输等成本,在电价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核电显然比火电更划算。
核电站建成后,年运行小时数能够达到7000小时,这一数据也远远高于火电站(4800小时)和水电站(3000小时)。中部内陆省份煤炭资源匮乏,但能源需求旺盛,修建核电站性价比之高可想而知。
核电站还意味着巨额的财政收入。秦山核电站1984年开工建设之前,其所在地浙江海盐县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但如今海盐县已连续数年跻身全国百强县行列。2004年,该县本级财政收入为3.7亿元,其中1亿元来自核电系统。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江苏连云港。 2010年田湾核电站入库税收16.84亿元,其中入库增值税9.26亿元、企业所得税5.78亿元、地方税费1.8亿元。这使得田湾核电站成为“名副其实的苏北纳税首户”。
核电站对于提振所在地的GDP也有着重要作用。2008年山东威海两座核电站开工,预计总投资高达千亿元左右。而整个威海市“十一五”期间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过1866亿元。
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国已将节能减排作为基本方针,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由此带来的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比重的压力日增,这些也都是核电大干快上的内在动因。
日本核危机之后,中国核电建设减速势在必行,但受影响的主要是新增项目。
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向《财经》记者介绍,企业拿到许可证之后,一般有个编制工程实施计划的时间,不会立即开工。另外按照惯例,获批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最后基本会得到核准,区别只是时间早晚。而受3月16日国务院四项决定影响的,主要也将是核准但尚未开工的项目和获批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尤其是后者。
接下来,业内瞩目的焦点将是核电产业中长期规划的调整。鉴于国务院已明确要求核电产业发展规划和核电安全规划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规划的出台时间必将推迟。此外,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规模也势必压缩。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鉴于2007年10月公布的中长期产业规划明显滞后于现实,该规划的调整早已提上议事日程,之所以历经年余仍无法出台,焦点有二:
其一是发展的规模目标。国务院倾向于7000万千瓦左右,行业主管部门国家能源局倾向于8000万千瓦左右,而核电业界和地方政府希望定在1亿千瓦以上。
最终,在今年1月初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报出的数字是8600万千瓦。
其二是项目遴选。由于核电产业中长期规划是一个约束性的规划,如果不在规划之内,项目基本就获批无望,因此,围绕着谁的项目上、谁的项目不上,激烈的博弈始终在进行。
日本核泄漏之后,或许会促使国内加速形成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更深层次的问题解决,则有赖于核电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九龙治水”
由于核工业的特殊性,在中国,民用核电管理体制一开始就呈现出“九龙治水”的态势
由于中国发展核电的目的是满足电力供应,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核电管理体制,一直由电力部门主导。
2004年9月出版的《李鹏核电日记》披露,1983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主持召开核电分工会议,并取得如下一致意见:“水电部管核电站总的建设和运行,并负责常规岛建设;核工业部负责核岛建设和工艺系统初步设计;机械部负责制造工艺设计和图纸;中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由核工业部归口。”
会议还一致同意,成立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设在国务院或者经委,主抓核电站国产化方案论证、核电发展规划方案、核电对外谈判。
1984年10月,国家核安全局成立,中国核电管理体制又多出一个新成员。但此后,核电管理权开始由“电”向“核”倾斜。《李鹏核电日记》记载,1985年12月李鹏又提出建议:“核电体制由核工业部拿总,运行交水电部。因为水电部事情太多,核工业部任务较轻。”
此后,水电部开始逐步向核工业部“交权”。1986年1月,李鹏对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管理体制作出如下批示:“核电站工作,包括建设、生产运行,均由水电部交移给核工业部统一管理和经营,向电网售电。原则同意水电部关于广东核电站的工作也移交核工业部的意见。整个移交工作由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但核电站常规岛建设继续由水电部负责。”
1988年4月核工业部被撤销,其原有职能划入新建的能源部,同时组建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承担核军工、核电、核燃料、核应用技术等领域的科研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以及对外经济合作和进出口业务。
20世纪90年代末,根据业务不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又被划分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前者主要负责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核燃料的开采提取以及核试验。后者主要负责核能利用开发应用事业、广东大亚湾和秦山核电站的工程承包和建设。
随着机构改革的推进,核电管理体制也不断发生变更。2008年,曾手握中国核能“重权”的国防科工委被撤销,以国防科工局的形式被纳入国家工信部,其职能被界定为从国防安全角度对核能进行管制,同时以国家原子能机构的名义执行与国际组织的交流沟通。
目前,主导中国核电事业发展的是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家局)和国家核安全局(环保部下属的国家局)。国家核安全局主管核电站运营企业的资质审批、安全审查,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发改委负责核电产业规划和项目审批。但除此外,还有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国家原子能机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诸多管理部门。
“长期以来,中国的核电管理体制可谓九龙治水,而且很多机构设置明显不合理。”3月22日,郁祖盛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他举了个例子,按国际惯例,国家原子能机构是一个国家负责民用核能的机构,而中国的国家原子能机构却长期被设置在国防科工委下面,这给人留下了中国民用核技术由国防部门管控的印象,不利于中国引进核电技术。
“这次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后,中国几乎所有的核电公司和监管部门都在搞反思,向上面打报告,这么多报告,各说各的理,高层听谁的?管理机构越多,扯皮推诿越多,真要出了事,恐怕谁也负不了责。”郁祖盛说。
行业监管多从立法开始,但中国并不缺乏法规。“在环境保护部网站上,可以公开检索到此方面的法律法规超过100部。涉及环节从设计到运营,内容从反应堆质保到人员操作管理,可谓条目众多。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正是标准不一。”2010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主任田佳树在第五届绿色财富论坛期间对媒体如此表示。
在田佳树看来,中国处于多种核电技术共存状态,不仅包括二代、二代改进型以及三代技术,还涉及引进技术和自主设计技术,其系统、堆型、技术标准以及工艺各不相同,导致其运行和管理模式多种多样,这不仅给标准及规范的统一带来挑战,也为安全监管工作增加了难度。
张华祝3月18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坦言,中国正在配合核电发展规划,编制核电安全规划。
两个规划可能同步或者前后发布,但由于核管理部门众多,职能交叉又各不明晰,以至于安全规划具体如何编制,令人“头大”。
《财经》记者获悉,核电安全规划的编制协调方,已由国家能源局换成了国家核安全局。
体制重构
“只有在巨大灾害的震动下,大家才会摈弃部门和利益之争,客观冷静地思考中国核电产业的未来。”
放眼世界,在统一监管体制下走市场化和专业化之路,是核电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世界第一核电强国美国,早已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核能技术创新体系和市场化的技术服务体系。
1947年,美国国会建立了AEC(Atomic of Energy Commission,美国原子能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