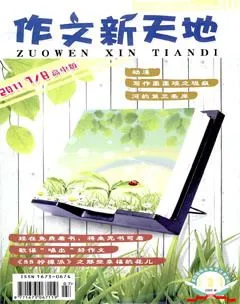岛
2011-12-29方夏燕
作文新天地(高中版) 2011年8期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住在大陆上……
吃过晚饭,矮山头上的夕阳仍在徘徊。母亲正在灶台前准备一种少见的荞麦饼。虽然每次父亲临走时,母亲都会做一些,但我从没尝过,因为饼的轮廓实在圆得有点吓人。
母亲那双长满树皮似的手,熟练地翻转着锅里的饼,并且很有节奏地不断用卷起的袖口揩去额头上的汗。我从小门旁走到灶台旁的小桌边坐下,抬头望母亲时,那日光就像神光一般绕在母亲的头上。她仍在有节奏地揩汗、翻饼。揩汗的手时不时地挡住射过来的阳光。我望着这个与金黄色将要融为一体的轮廓,一动不动。“好了!”随着母亲的话语我站了起来。“饼都烙好了,准备准备吧!”母亲说完,洗了一下手,便拎来了那个已经被塞得很满的背囊,顺手撩走我头上的松针,拍了拍我的衣服。紧接着,麻利地把荞麦饼包裹一通都塞了进去。“妈,你自己留几个吧!”“我自己再做,别说了,上路吧,到了那,跟你爸说别惦记家里……”母亲说了一大堆我无法尽数传达的话,然后一直把我送到矮山头上。
父亲是在离家有些远的海边,以我的脚力往往要走一天一夜的路。具体有多远,我也不是很清楚,而且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一直待在海边。说实话,我很害怕夜里出行,但是因为路途太远的缘故,我只能这样赶路。很快,我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一片黑漆漆的林子。我尽全力地聚焦目光也只能看见一条灰蒙蒙的小路。我吁了一口气,和以前一样小心翼翼地踏入这条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路。林子的外面月光很好,而林子里却被覆盖得一片漆黑。黑暗就像无数的冤魂围绕着我,毫无理由地找我索命。每当此时,我总希望父母能在我的身旁,但我很明白,这一段路只能我自己走。我凭着一种模糊的经验,在这个世界里摸索着道路。想要叹息却说不出话,只能努力给自己一丝希望,当我战胜黑暗,黎明便会随之而来。
整整走了一夜,也饿了一宿,身体似乎已经虚脱了,我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了最后一座矮山。若是平时,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爬上去,可现在,它是那么地高不可攀,黎明的太阳竟也变得如此地刺眼。不过,我似乎能模糊听到一点海浪的声音。每一次从家走到这儿只需要一夜,而单单爬这座山要整整一天。到山顶时一般会在下午2点左右,而看到海之后,下山到父亲的茅草屋子就得4点了。
我曾经试图在这里找一条捷径,以便能更快地到父亲那儿,更重要的是不用去爬那座每次都让我恐惧的矮山。我带上一个礼拜的大米(山里的野菜很多)和那顶破到已经无法再补的帐篷,就几乎耗去了我所有的精力。当我带着满身的泥和那顶帐篷回到家时,母亲对我说:“爬上去,那就是捷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永不磨灭。
12点的时候,我到了那曾经“救”了我一命的岩洞。说实话,这样得天独厚的岩洞实在少见。位于半山腰,旁边还长着一株野栀子。我很喜欢这种白色的花,它的香气很清新。这种清新给了我一种温暖,像是我远离好久的家的气息。碰到这个岩洞,似乎是上天注定的。上次因为下雨,我才阴差阳错地踏进这个如此奇妙的地方,我躺在里面发了一天的高烧,后来竟还是迷迷糊糊地跑到了父亲那儿。
父亲一再告诫我要对此地满怀感激,我也把它当成除了父亲母亲以外,第三个可以寄托感情的地方。我在这儿停了下来,卸下行囊,在洞口开始了一宿之后的进食。嚼着无味的米粉,就着几口水,想把这种使牙齿粘连的东西吞入胃中。即使行囊里塞了如此之多的荞麦饼,我依旧嚼干米粉。或许是因为荞麦饼圆得不敢去碰,或许是因为这是母亲让我带给父亲的。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一个在家而另一个却要在海边,让我夹在中间,如此地累。
准时得很,2点到达山顶,4点到达父亲的茅草屋。这个小屋是很雅致的。屋子顶先盖了一层瓦,又铺了一层草,茅草总是很新鲜,父亲会定时地更换。墙,也是两层,外围是根根木桩,里面则是一种竹片,削得很精致。地板是离地的,擦得很干净,父亲的生活习惯有些像韩国人,比如地板,我在家里从不脱鞋,在他这里却必须脱(这也是父亲和母亲的矛盾之一)。有几次我忘乎所以地跑进来,惹得他怒眼相视。其实父亲的脾气很好,我说过了,他像韩国人。
我到的时候,父亲已经准备好了酒和饭,下酒菜是一种很常见的鱼。我扒着饭,父亲喝着酒,找不到什么话题,父亲又开始说起上一次我在岩洞中发烧的事。我嗯了几声,又是沉默。父亲没吃饭,说要带我去看海。这个时候天已经有些发黑了,因为这片海域只能见到朝阳,夕阳是从山上下去的,所以天黑得很早。我走近海总会有一种紧张的感觉。天啊,又来了!不敢呼吸,心快停了!我畏惧海,现在又刚好起着风。沙滩边的海水,我连碰都不敢碰,一个海浪扑过来,我便拼命地往回跑,总感觉我会被卷进去,永远都回不来。它是那么深邃,看不透,就像父亲,读不懂。只觉得海的轮廓就是父亲的轮廓,风停的时候很清楚,风起的时候很模糊。父亲知道我的畏惧,跟我坐在了一块较高的小礁石上,迎面吹来的海风带着一丝温暖。父亲是面朝大海坐的,他那模糊的五官让我感到窒息,父亲真的和海融为一体了。那么地和谐,却让我有一种失去的感觉,他是只属于我的父亲吗?
我们没说什么便回去了,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闭上双眼,我脑中出现的图景是两个轮廓,一个金黄色,另一个带着海的气息,它们像是一体的,又像是分开的……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家和茅草屋之间有一条很平坦的大路,父亲告诉我,选择这条路,是为了让我独自走过那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森林。另外,我住的地方也不是陆地,而是一个岛,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岛,就像我的家是一个湮没在大千世界中的家一样,而世上又有多少这样的家呢?
(指导教师:伍献卫)
薄言说
我们不必用生活化的眼光去追究这个故事的逻辑可能性,甚至可以无所谓是否“看得懂”,值得欣赏的是实验写作的尝试,简洁流畅的笔触,以及运用各种意象引出的文外之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