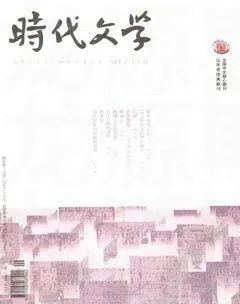平静的力量
2011-12-29李雪萌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5期
反映抗震救灾史实的电视剧《震撼世界的七日》在央视一套播出后,我们访问了这部剧的总编剧之一苗长水。当时,已经是他从四川汶川地震灾区一线回到济南半个月,正在紧张地把他在抗震一线以日记体撰写和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汇集成长篇报告文学《北线大出击》。
汶川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他即随济南军区抗震救灾部队奔赴四川彭州市龙门镇重灾区,见证了救灾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他是一名作家,同时又是一名军人,还是灾区一名普通的救援行动的亲历者,说起刚刚经历过的、堪称惊心动魄的抗震救灾经历,苗长水却非常平静、淡然,正如他在灾区写下的所有文字,没有一丝情绪的渲染,简单直白的叙述之中,却蕴含着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身为军旅作家,苗长水基本走遍了中国的版图,他说:“没到过的大地方就是西藏和四川,有几次进川进藏机会,都因为一些原因错过,没想到这次说来就来了,但却没有来得及感受四川的美丽,看到的都是伤痕。”
5月14日,苗长水乘坐军列到达成都,再换乘越野吉普车来到距汶川一山之隔的彭州重灾区。彭州也是济南军区抗震救灾主要作战方向之一。“某集团军机步旅已经先到了,到达之前,战士们还以为能像往常执行任务一样,下车先找宿营地。但是一进入灾区就知道不可能休息了,因为黑夜中到处都是地狱般的凄惨景象,到处都是呼救。部队下车就投入到救援中……”
5月18日,苗长水亲身参加了回龙沟大营救。
前一天晚上某机步旅得到消息,回龙山谷里可能有幸存者,据称还有外国人。“我们站立的地方两边都是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大地震像刀切一样把山坡切开。突然一片滚石轰鸣着飞下来,我们抬头看时,就像科幻影片的镜头,那些石头像篮球一样朝着我们飞来,眼看就无法躲避。那一刻所有人都吓傻了,躲也没法躲。石头落到河里轰轰响,没有砸到我们,但大家立刻后撤,没有人敢充大胆的了。旁边地方国土局的一个同志提醒我们,这些飞石借助空气的作用在空中会改变方向。”
营救持续了两天,5月19日,正是国务院宣布的国家哀悼日,假如这一天将几位幸存者救出来,意义不一般;假如营救成功,他们就在震后生存了9天,本身也是一个奇迹,央视记者、凤凰卫视等媒体的大批记者聚集到这里,等待拍摄“有意义的场面”。然而现实不是编排好的戏剧,“下午2点,山上传来最后的令人失望的消息:余震、暴雨加最后300米的断崖,营救不可能继续,而新塌方的土石中发现了4具尸体,也许正是他们想要营救的人。”
还是这一天,苗长水随一支队伍给断水断粮两天的董坪村送去食物,“等我赶到山顶的村子,隐约听到妇女们好像在唱歌。走近了才知道,原来那是在激动地跟官兵们讲着告别和感激的话语,质朴的山民们背着篓子,拖着娃娃,含着眼泪,小姑娘们背着竹篓一路跟着队伍。进村那一刻,男女老少都鼓掌欢迎我们,送去的面包、饼干,拿起来就吃,矿泉水咕嘟咕嘟喝。一个小姑娘,接过解放军给她的饼干就吃,那眼神都傻了……《河南日报》记者老陈把他抢拍的那张照片给我看,那个小姑娘的眼神跟希望工程宣传照片中那个‘大眼睛’简直一模一样,老陈说这张照片也许会在《人民摄影》发得很大,成为名照片。我说这张照片可以起名‘彭州的大眼睛’”。
在废墟中,让苗长水感动的,还有另外一种场面:一路走,不时还能看到一瘸一拐的小狗,大都是不错的宠物品种,看到人都特别亲,跟着你走好一段。军区摄影干事施文标是随首批救灾部队乘飞机来的,给我讲了他在都江堰市亲眼看到的一条狗,老是对着地面的一条裂缝呜呜地哭,真是在哭。官兵们给它东西也不吃。老百姓讲那原本就是一只流浪狗,没有主人的。
“陪同我们的机步旅杨西河干事也讲了很多有关动物的目睹场景:他们的官兵第一次进九峰山时,看到一辆被砸坏的轿车内,有一只小狗趴在座位上,主人不知哪儿去了。战士拿东西给小狗吃,给它水喝,它吃完喝饱,又跳回车上睡去了,似乎在等待主人归来。官兵们在扒遇难者时还看到一只老母鸡,呆在废墟上就是不肯走,因为那下面就是喂它的女主人。战士们撵它也撵不走,一直在那儿等着战士扒出它的女主人。
“公路上又遇到一片大塌方,我们从公路下河边的几户人家的塌房中找路通过,看到废墟中孤零零立着一匹马,一动不动,像雕塑一样立在废墟里。”
5月27日,苗长水离开四川飞往北京,准备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材料。当晚,他接到邀请,中央电视台和曾经拍摄过《亮剑》的海润影视公司准备做一个纪实电视连续剧《震撼世界的七日》,邀请几位到过抗震一线的部队作者参加编剧。 6月10日,苗长水再次来到地震灾区,来到设在德阳市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的《震撼世界的七日》摄制组的大本营。因为剧本随时需要修改,需要编剧随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进入汉旺镇街区不多远,就看到了那座已经闻名世界的、永远停留在下午2点28分的钟楼。水泥建筑的方形钟楼,不算太高太雄伟,大约有六七层楼那么高,矗立在街心花园的一旁。顶部圆形大钟的指针停在2点28分。当地人告诉我们那不是人为的,就是5·12大地震那一瞬间停止的。”汉旺镇是距离震中汶川最近的重镇,人口是映秀镇的20倍,强震后几乎没有一座建筑完好,全镇遇难人数达2500多人,其中学生700多人。我们从报道和电视画面中看到的那些震撼人心的图像:一名死难学生手里紧紧攥着一支笔,一位被埋在废墟中的女学生伸出一只求援的手,均摄于东汽中学发掘现场。还有谭千秋老师,‘可乐男孩’薛枭,都出在这里。”苗长水说:“面对如此震撼的真实故事,任何艺术创作都会黯然失色,我想即使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大师,也不忍再开口谈什么灾难大片,谈什么英雄、道德。所有人只能保持沉默的尊敬。”
剧组进入时,汉旺镇及东汽许多废墟已被戒严封闭。因为不仅需要对全镇进行防疫和清理,次生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上游的堰塞湖随时会崩塌,预警的警报随时都在拉响。 《震撼世界的七日》6月5日开机,6月20日关机,拍摄时长仅有15天。如此短的制作周期,如此强大的制作阵容,在中国电视史上绝无仅有。这部戏可能不够精致,可能还有些粗糙,但肯定是一部有激情、有创造、能够得到大家尊重的作品。
12万字的《北线大出击》,14天随救灾部队奔赴一线的亲身经历,令他可以以一名军人的身份给我们描述与一般新闻报道不一样的抗震救灾历程,让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来认识这场灾难与斗争。
苗长水用“空前规模的立体大机动”来描述这次济南军区的远距离快速营救行动:从5月13日凌晨4时41分第一支先遣部队出发,至5月17日22时55分最后一列军列抵达成都,济南军区先后通过空运、铁路、公路摩托化远程机动,向四川都江堰、汶川、理县、茂县、彭州、绵阳、德阳、青川、平武等重灾区投送45000余兵力。“这种远程机动距离之远、规模之大、行动之迅速,在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
苗长水回忆道,5.12大地震当晚,“济南军区指挥机关的司、政、联、装等要害部门几乎全部灯火通明,指挥系统高速运转,通信系统紧张忙碌。车辆停在楼下,司机们都睡在车内。从这个夜晚进入作战值班后,很多人都是十多天后才回家,24小时连续工作,坐在椅子上,几分钟不说话不处理文电,就能睡着。”
13日零时,济南军区某集团军“铁军”师、某集团军“新四军第一师”机步旅、“维和”工兵团等单位的官兵迅速紧急集结;13日凌晨1时52分,由济南军区总医院、456医院、军区疾病防控中心组成的5支野战医疗队141名医护人员,迅速紧急集结,携带20吨帐篷和器械等装备物资,登车向机场出发;11时25分,济南军区抗震救灾部队空运的第一梯队第一个架次东航H5000空客航班,从济南遥墙国际机场起飞……”苗长水说:“我是5月13日跟随铁路输送部队开进的,开始铁路运输速度相对较慢,铁道部还专门下了调度命令,一是所有客车,包括动车组,都要避让军列,夜里战士就穿着迷彩服,睡在车厢过道的地板上。”
“那些天的总部、军区和部队的往来电文中,多次出现像‘人命关天’这样的非公文急迫用语,都说明了这是一种非正常的军事行动状态,这是生存或是死亡的一场战争。”
尽管苗长水对于当时部队紧急集结抗震救灾的情节叙述紧张而激烈,但听苗长水讲述灾区的经历,仍让人深切感受到其“平静的力量”。第一次亲临灾区,他就开始了文字材料的收集整理与创作。“白天忙救灾,晚上趴在床板上、矿泉水纸箱上写。”那个时候他写下的文字就是平和而朴素的,包括《震撼世界的七日》的剧本创作也没有刻意煽情的东西:“在这样一场地震灾难面前,完全可以不用创作,无需艺术,就可能产生比最震撼的艺术作品还要震撼的艺术力量。”
《北线大出击》是一部日记体的长篇报告文学,“有人问我在前方为什么不想办法把积累的素材赶写出一部小说,我就对他们讲,小说的力量远不如每天的日记。我在第一时间发给各报刊的日记,评价非常不一,有的编辑几乎是愤怒地对我讲,你写得太琐碎,简直是在灾区走马观花,有闻必录,这样的东西根本不能发表;但是有的报刊却连续整版连载,比如《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文艺报》编辑冯秋子,都对我的这些日记评价比较高。李敬泽一边处理我已经发去的稿子,一边让我抓紧补充后边的及时发给他。冯秋子给我发短信讲:你的稿子是我看到的稿子中最扎实、有力的!我跟秋子编辑并不熟悉,尤其在抗震一线听到这种鼓励,感觉更为宝贵。她的两个整版处理得很震撼,《文艺报》吕先富副总编讲,这是破例的。”
苗长水介绍,《北线大出击》几天内就可以交付出版社了。“现在关于地震的各种文艺作品已经非常多,但关于这场灾难的思考远远不会停止,等沉积一段时间过后,我自己也还会进行一些创作。”
苗长水说,正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灾难中感人的故事、生命的尊严、人性的光辉,那一瞬间整个中华民族所爆发出来的令人惊叹的凝聚力,才让我们集结起来,靠的是提着一股气,进行着抗震救灾的战斗。
“包括这部《七日》,也包括我所有的创作,都有一种期望在里面。但最重要的期望也许是,因灾难当头而激发出的这股气,能够传输到我们民族未来安宁和谐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