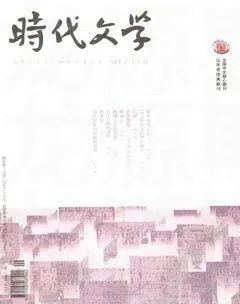似水流年
2011-12-29孙彤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5期
在当代军旅作家中,提起苗长水,大家给他的定位总是一位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在描写腥风血雨、金戈铁马的的军旅作品中,他总是带着那么一点清新和飘逸,绵柔细腻、平和冲淡地去挖掘战争岁月背后的意蕴,这种清新和飘逸中又夹杂着历史的凝滞感和厚重感,纵观早期的《犁越芳冢》、《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非凡的大姨》等,近时期的《超越攻击》、《北线大突击》、《解放的日子》、《忠诚的个性》,我们从中能体验到一个作家是怎样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担当起人文精神重铸的责任,感受到作家因时代变迁而激起的追问、奋斗和反思的精神诉求,也能感受到他水一般的情怀。
一
苗长水出生于文学之家, 他的父亲——著名诗人苗得雨先生, 其实对他的文学濡染并不多。苗长水1970年入伍后,到某师高炮连当了一名普通的战士,当时父亲正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父亲没有刻意要求他走文学道路,只是经常鼓励他写点东西。身逢“文革”动乱的苗长水并没有多少机会读书。当兵后学《毛选》也可以得到潜在文学熏陶,后来慢慢能看到的一点文学作品《牛虻》、《红与黑》等。在连队中,他也曾利用业余时间试着进行“创作”, 多是稚嫩的模仿。1973年,苗长水调到师报道组, 也有机会读到一些“违禁”名著,他看了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两个中篇小说,惊叹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作品。梅里美的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冷静的表面下隐藏着炽热的激情。 “文革”结束,世界经典名著陆续出版,可以阅读的东西越来越多,契科之夫小说的幽默语言风格对苗长水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他除了写新闻报道和为师宣传队创作节目,还创作发表了一些反映部队生活的诗歌、散文。1979年,他调入军区前卫报社当编辑。在报社里,他的文字功底得到了扎实锻炼。
1984年,苗长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在这里,苗长水得以接触从刚刚打开的窗口涌入的世界先锋文学潮流。 据朱向前在评论中写道:“……1986年初秋——我们都毕业——他回济南编报我留系里执教的某一天,顺手翻开新到的第8期《解放军文艺》,赫然有一篇署名苗长水的中篇小说《季节桥》,心中不由得一惊:噢,长水竟然发表中篇小说了。就随意浏览起来,看了不到一页吧,心里便说‘有了’。一口气读完之后,更隐约觉着:苗长水要‘来了’。”
八十年代的文坛可谓经历了众波文学思潮的洗礼, 文坛如花坛般姹紫嫣红,能够标新立异确实不易。但这个时候苗长水却在不温不火地浅吟低唱着自己的“沂蒙山小调”,而且能在新时期小说的多元化局面中独树一帜。 苗长水把笔触伸向了家乡——那片积淀着红色激情和深厚文化传统的热土。他的老家在沂蒙,但他的成长又不在那里,所以从实质上讲他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童年记忆。这里面夹杂着很多亲情的东西,1980年,他随父母回老家看望病重的祖母。那是“文革”后他第一次回家乡,重拾幼年的点滴记忆,那些熟悉的场景与家族的历史结合起来,便酝酿出天然的情愫。这为他以后叙事话语风格的形成和个人立场的确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如果说《季节桥》 中还运用了魔幻、夸张、变形等手法, 被裹挟在一九八六年的先锋浪潮里,也许它只是微动的涟漪。
1987年4月,苗长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同期被《小说选刊》转载,其主编、著名作家李国文配发评论,继而被《新华文摘》、《文艺报》等报刊转载选载。 《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用崭新的文学语言和独特的文学视角,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战争年代的沂蒙山区的故事,题材仍然是战争题材,人物也只是普通的沂蒙乡亲,但清纯温馨的感觉让人过目难忘, 从此苗长水也迈着坚实的步伐在当代文坛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随后,他又发表了沂蒙革命战争和部队现实生活题材中篇小说《染坊之子》、《犁越芳冢》、《战后纪事》、《非凡的大姨》、《御花园》等,引起文坛关注,称其为“浮躁中的一股清风,红蝗中的一片绿地”、“久违了的风雨故人来”、“以独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重新抒写的革命历史,开辟了一片属于他自己的领地”。雷达在《传统的创化》中说:“他的创作是当前文学中的一个奇迹,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他居然在对于当前读者已经普遍丧失吸引力的题材、人物和情节模式中,在一片旧的土壤上,营造出葱绿的、生机盎然的审美新地,发现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且已失却兴趣的人物身上新的精神底蕴。他的作品使我们想起一大批熟悉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但在他的笔下,不是使我们与之疏远了,而是亲近了,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回肠荡气。”(《文学评论》1990.2)朱向前在《晴空和新雷》中也说道:“无论怎样的表达方式,它们都升华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与心气。而这种精神与心气已深植于高高沂蒙山上和清清的汶水河边,她的肉体可以消亡,但她身上所蕴藏和焕发出现的人性力量与光彩却是永远不灭的。”(《人民日报》1991.1.3)
创作沂蒙山系列作品时,父亲母亲对他的帮助成为重要部分。“我父母那里有很多(关于沂蒙山的)别人没有的素材。”苗长水把这些从父母家族那里获取的、源于长期生活积累的素材融入到作品中,不仅极大提升了作品的真实性,更使作品充满惊人的亲情与乡土气息。 在“沂蒙革命历史”小说中,苗长水笔下的人物很少声名显赫的英雄,大都是些平凡的人物 。他曾经说过:“家乡的人们都曾经不可避免地加入到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去,但他们是这伟大过程中的芸芸众生,或者说他们像历史大道上的无数车前子菜、狗尾巴草一样。战争、历史以及种种不可战胜的命运力量的滚滚车轮,把它们碾轧了,甚至于把它们的叶子碾得稀碎,但它们永远还是那么倔强地生长着,秋天枯了,春天又绿了,生命的不朽之歌与壮烈旅程只铭刻在它们自己的灵魂之中。”在苗长水的沂蒙文学世界里,比历史和革命更为恒远的是人性,而比人性更为恒远的正是这生生不息的伟大生命。
在谈到“沂蒙系列”的作品时,苗长水常说自己写的东西不能给家乡带来什么变化,这时常让他心有戚戚 。红色文学同样应该是带着强烈的人文观照和悲悯情怀的。这是不是苗长水暂时选择远离了那片精神家园的原因,不得而知。似乎苗长水得到了文坛的认同,却被自己否认了。 进入20世纪之末,他渐渐从沂蒙走出来,把目光转向军人自身。
三
经过多年的准备与揉搓之后,苗长水于2006年推出了现实军旅题材长篇小说《超越攻击》,这是一部花费了近五年时间,长达70万字的小说。从《超越攻击》开始,苗长水的目光不再仅仅有诗意的柔和, 现实主义的犀利视角和对当代军旅生活的细微洞察,形成了他在已有性格下的新的文风。刨除了一贯包裹在军旅文学外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外衣,他开始冷静地梳理和平时期军队内部矛盾和价值观念的更迭,以直面现实的勇气阐释了新时代英雄主义的内涵。无论大家对苗长水的改变带有怎样的不适应或者不满足,《超越攻击》带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问世,为“当代文学现场”建构了一个良好范例。
苗长水认为, 小说的至高境界就是在细节的层面上构建起坚不可摧的真实感和物质感,成功的小说就是由这样的细节一点点堆砌起来,哪怕一个不真实的细节就可以瓦解整个作品。 在当下作家很难达到的深入体验中,他感觉官兵们的歌声和番号、队列的整齐划一、官兵的喜怒哀乐,这些本真的存在都不是纯属完美的语言所能表达清楚、描绘准确的。所以他总是写了改,改了写,直至作品出版后,他还总觉得不尽完美,留有遗憾。
四
2008年5月13日,苗长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二天,跟随济南军区部队远程机动抵达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行动。 从跟随部队踏上征途开始,他就留心随手记录着每一个别人并不留意的细节,在众多的抗震救灾题材的作品中,他写下了唯一一本日记体报告文学。
苗长水是擅长描写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