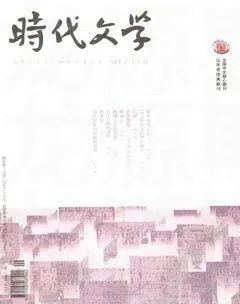王鼎钧的信仰世界
2011-12-29杨传珍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5期
王鼎钧是山东籍旅美作家,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海外中国人的良心”。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里,王鼎钧不仅拓展了散文的疆土,深化了内涵,而且在小说、诗歌、评论、文学教育领域,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的《左心房漩涡》,写尽了中国人的生死流转,四部回忆录,折射了几十年的社会史。他自称是基督徒,佛经读者。我们从他已经出版的40多部作品中,所感受的是超越所有宗教的信仰,即以虔诚之心善待生命的普泛信仰。当然,他的信仰世界,是通过文学展示的,他信仰上帝,通过文学关爱具体的人。
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作家、世界、作品、读者是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作家是社会的人,是关注人生、用心灵感受历史风云、表现世界真相的人。他所表现的生活,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所谓主观,因为有他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客观是指作家不能一厢情愿地解读世相人生,而是最大限度地揭示世界真相,文中有史,史中有思,思中有境界,境界中蕴含天机。在这个意义上,天赋、经历、学养、自我期许和神秘因素的巧妙组合,是成就作家的综合条件。王鼎钧自称“阅历不少,读书不多,文思不俗”,既是自谦,也是自信和自诩。在中外文学史上,尽管在书斋中成长的作家代不乏人,但是,他们的文学成就总有次生的感觉。王鼎钧是靠阅历成就的作家,命运强加给他的生活经历,他是被动承受的,可是,选择哪些内容表现,怎样表现,主动权却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在《左心房漩涡》的序言里,王鼎钧把作家的生命比作礁石,把生存环境比作海水,礁石受海水冲击的强度与形式,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可是,生命的内在质量,却决定了礁石的形象。他在评论电影《海角七号》的时候说:“大江东去,浮萍不能西上。”看似不经意,却饱含着对众生的理解和欲休还说的凄苦。辛亥革命以来,有着极端经历的人数不胜数,对世态作过深入思考的人也不是少数,而成为经典作家的却寥若晨星。那些写出了作品的人,尽管期望自己的文章走进不朽,可是很遗憾,多数作家的名字都淹没在时间的尘埃之中。王鼎钧对这一现象没作具体分析,可是他从宏观上指出了文学创作的正区和误区。在《文学种籽》一书里,他写道:人,可以说是在挫折中成长的,“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可与人言无二三”,有些重大的挫折造成“心的伤害”,终身隐隐作痛。在他心里有虫子咬他,热铁烙他,尖针刺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忘不了,抛不下,躲不掉。他刻骨地想,内在语言如潮海翻腾。他只好去做某些事情以减除痛苦,其中之一就是文学创作。文学有胎生和卵生之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谓之胎生;出于社会使命的创作谓之卵生。不论胎生卵生,只要写得好,都是上品,如果写不好,卵生流为说教,胎生流为牢骚,那就都失败了。
作家都是情商很高的人,有自己的是非观,无论写胎生的文章还是卵生的文章,都难免受到是非观的影响,而是非观来自对时代与人生的体验与思考。王鼎钧认为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也有相对的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就像老祖父看两个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这时候,作家没有了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没有了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王鼎钧在一篇书评中感叹道:《红楼梦》之后,中国之所以没出现一流的文学作品,作家的才情精神尽为立场消磨是原因之一。他认定,有抱负的作家,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人,别人亏待他,迫害他,他却生出美,生出价值,生出人类文化的产业来。他必须守住自己的岗位,即使受人误解,受人恶意批评,也在所不辞。虽然他从人生中汲取的是浊水,但是他能以艺术造诣、人格修养、思想境界蒸馏那水,过滤那水,变浊为清,再还给江河湖海,这样,既提高了人生,也提高了文学。这样的作家是人类的作家,居高临下,悲天悯人。在他的心目中,众生平等,世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他尽心尽力,把作品经营成高级象征,不管世人的国籍、种族、信仰,作品对他都有意义。要写出具有高级象征、不同族群的人能够共享的作品,作家必须有一颗高尚、博大、深刻、寻美的心灵,“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只要想长进,就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终生“修行”。
传统的文学观认为文如其人,伟大作品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进入现代主义之后,文学批评家借助许多个案,动摇了这一观点。这样的颠覆攻略,在破除了文学史8280e6892247b57ec0885c92dafad6e5家建构的神话、使文学活动平民化的同时,又从两个方面对文学活动构成了伤害:一是读者对作家人品的信任度降低,认为那些弘扬高尚道德的作家,其道德水准不一定高尚,说不定还是伪君子,这样,读者由对作家的轻视影响到对文学的敬畏;二是影响了作家的自律,使文学作品的生产者对文学的敬畏也打了折扣。这内外两种因素一旦形成恶性互动,文学生态即出现危机。
王鼎钧是基督徒,可是他坦言自己不是牧师所满意的那种“好信徒”。他读佛经,相信不同宗教能够异质同构,他说出来的话和别的信徒不一样,然而,他却从根本上理解了基督教的奥义,这就是惟爱为大,同体大悲,相信人人有罪,而任何罪人都能得到救赎。他认为真正的作家都是有神论者,可他不相信末世论,对人生和未来充满希望,提醒人们对爱情不要绝望,对子女不要绝望,对国家不要绝望。对文学的未来也抱有信心。对于基督教的“爱仇敌”,他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是一个作家,我爱文学,也爱读者,我总是尽心、尽力、尽意把文章写好。我总是把最好的内容、最好的形式拿出来,希望对读者有益处。我的文章登在报纸上,人人可以看见。朋友看了,就是我爱了朋友;敌人看见,就是我爱了仇敌。”
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家都提倡和认可文学的教化功能,可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甚嚣尘上,学界对文学的教育功能开始怀疑,进而全盘否定,以至“寓教于乐”的提法变得声名狼藉。那些对文学的教育功能持否定态度的人,能够举出一系列事例,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这是在某些特殊时期,某些特殊机构利用文学的教化功能,将有害的作品放进教科书所产生的恶果,我们不能因为有害内容制造了祸端就否定“文教”功能。王鼎钧先生相信,高级的文学作品,能够提升人的道德水准,能够唤醒读者的同情心。他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呱呱坠地之后,全凭本能存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顾当下,不顾久远,很自私,有时也很残忍。这是禽兽的境界。慢慢长大了,知道遵守社会规范,知道追求抽象的目标,能为别人设想,这是人的境界。智慧过人者要创造一番事业,要掌控一个局面,有时用暴力,有时用阴谋,有时也用道德感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横冲直撞,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英雄的境界。禽兽不知有法律,不知有道德,不知人际关系。英雄不守法律,不顾道德,不恤人际关系。二者近似。因此,凡进入英雄境界者要能更上一层,进入圣贤的境界,否则就是一只大号的猛兽。如何把英雄引渡到圣贤的境界而不变成大号猛兽,用文学提升人的境界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方式。他认为作家接收上天给他的讯息,向人生和人性寻根,发现和抽取人性中美好的元素,“译”成文学,如果不能参化育也要尽善美,不能尽善美也要求善求美,在有限的善美中表现无限天机。既要把某些人试图掩饰的一面表现出来,也不能把善良美好的一面挤出去。倘若为了标榜真实而自居“下流”,那是作贱自己,当然也失去了艺术真实。装腔作势,言不由衷,是作家的堕落,也是文学的末路。
作为一个靠生活滋养的作家,王鼎钧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如《碎琉璃》、《山里山外》、《左心房漩涡》和四部回忆录,写的都是自己的亲历。那些亲历都是痛苦的,他见到的许多场景是丑恶的,可是,这些作品,给予读者的是美的震撼。其秘密何在呢?王鼎钧说,文章是有病呻吟,可是谁愿意听别人呻吟呢?要使有病呻吟为读者所接受,就要把呻吟变成一支歌。王鼎钧在他的第三部回忆录《关山夺路》新书发布会上说:“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啦啦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群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具有转化的境界和功力。
王鼎钧是有高远抱负的作家,纵观他几十年的追求,与其说他是基督徒,不如说他是虔诚的文学教徒。他认为,没有文学和没有面包同样令人活不下去,人生充满危机和丑恶,文学能够从上游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文明既坚韧又脆弱,时间的推演并不意味着文明进步,保存高贵的人生经验是文化大事,那些情感方面的经验,只有依靠文学作品保持传递。他认为有酬世的文学和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国共内战,彻底改变了王鼎钧的人生走向,也在作家心灵深处留下了伤痕。这段生活遭际,始终是作家的心头之痛,也是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当然,童年生活、流亡学生的经历,却是珍贵的人生记忆,他要以史家之笔写下来,为后人留下一笔财富。他说,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结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他要通过回忆录对今生今世有个交代,对国家社会有相应的回馈。这样的回忆录,不仅要求真,还要求善、求美、求高。这样,他写出来的文字和与官方的记载就不能完全一样。他要把别人不能、不敢、不愿、不屑记下来的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世。
王鼎钧的《文学种籽》有一章专门分析文学的体裁与题材之间的关系,使初学写作者藉此少走弯路。而面对同一体裁,他对形式和内容同样看重,追求两者的完全融合,对玩弄技巧的做法颇有微辞。他认为,文章的内涵与技巧,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战略上失误,战术上不能补救;内涵不够,文学技巧不能弥补。否则空话大话人人会说,岂不提笔都是经典之作?尽管王鼎钧没有拒绝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营养,可他的精神深处,是古典主义的基因,我们从他的价值观和行文语序上,能够感觉到,深藏王鼎钧心底的文化底色,是中国的《诗经》、先秦诸子、司马迁、杜甫,世界的文化经典是《圣经》和佛经。但是,他牢记前人“良工式古不违时”的诗句,不拒绝新的知识,一生与书相约。年过七十,还在选择性地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和作品,学习使用电脑。让庞大根系所吸取的传统营养,与世界学术前沿的最新成果展开对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的学说介绍到台湾,汤氏认为,历史事件太多,历史方法处理不完,用科学方法处理;科学的方法仍然处理不完,那就由艺术家处理。他说艺术家的方法是使用“符号”。这一说法,给王鼎钧很大的启发,他由此认定,文学作品并不是小道,艺术作品也不是雕虫小技。当然,这指的是高级艺术作品。王鼎钧对文学作品的高下作了分级,他认为,初级作品写的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中级作品写出某一群人的问题,高级作品可能写出全人类的问题。要写出全人类的问题,必须用意象说话,直接表达出来的思想,无论多么深刻,都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立场”的,而高级的意象却能由有限到无限。王鼎钧用几十年努力,修炼出分离、抽象、建构、还原、驾驭复杂历史的功夫,也达到了出乎其外、居乎其上的境界,耄耋之年,在老一代人的功业成为渔樵闲话,恩怨开始化解的时候,奉献出四部回忆录,记录了中华民族一段珍贵的历史,也展示了作家自己的信仰世界。他说:“从地窖里拿出来的酒,最后拿出来的是最好的。” 此言不虚。
(作者单位:枣庄学院区域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