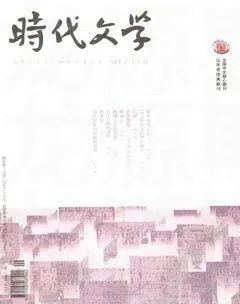当代作家的宗教性书写
2011-12-29胡书庆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5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场域,宗教性主题值得关注。当代文学的宗教性主题表现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外延层面再现与宗教有关的社会历史生活,如阿来、迟子建等作家的一些创作;另一种是在内涵层面表达某种宗教情怀及某种宗教诉求意识。这里主要关注后一种情形。放眼中国当代文坛不难发觉,张承志、史铁生、北村是作品中含有较多宗教性因素的三位作家。或者说,他们是三位较富有宗教情怀的作家。也正是因为宗教性因素对他们文本及生命的融入,使他们显示了自己较为独特的文本建构和生命姿态。应该说,他们给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人文语境带来了一些新气象。
史铁生和张承志都属于知青一代。给无数青年造成沉重心理创伤的上山下乡运动肯定也使他们迷惑过。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心灵里多了一重审美的眼睛,它使他们发现了一种与这场运动有关也无关的美的东西,一种与民间深处纯朴的自然和人文事物接触中感动过温暖过他们的东西。我们知道,史铁生在八十年代曾是“知青情怀”的第一个代言人。张承志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是写知青生活的。对当时的“知青文学”,读者热情很高,批评界也一片欢呼。但是,当“知青文学”还如火如荼地演绎的时候,他们的创作的内在精神却悄悄发生着变化。
1984年,史铁生发表有着强烈心理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山顶上的传说》(《十月》1984年第4期)。小说通过主人公(一位残疾青年)对自身不幸命运的深入思考,由个体的残疾意识联想到人类灵魂的广义残疾,将个体的精神困境上升到人类共同的心灵难题,对生命存在的意义进行了痛苦而执着的追问。之后,他又发表了《我之舞》、《礼拜日》、《来到人间》、《命若琴弦》、《原罪·宿命》、《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小说三篇》等,继续围绕命运、宿命和生死问题进行自我思辨,并开始走向宗教诉求。特别是1991年发表的《我与地坛》,以其切身的体验与思索,以其“从心灵里流出的艺术”品质,引起文坛很大的反响。这种品质在1997年初发表的唯美主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后来的《病隙碎笔》则以其切近本源的“思”使我们感悟了一种被彻底理性过滤后的宗教情怀——那种彻底的理性似乎与所谓的理性主义无关,反是理性自身用尽
后的一种洞悟,一种回归。
史铁生应当受到过法国作家加缪思想的某些影响,不唯他的文本里曾数次提到过“西绪福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表征的其实就是一种过程神学。“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这是史铁生穷尽自己的智思后所得出的结论。不过,这似乎与西绪福斯精神还是有内在区别的。西绪福斯只是机械地无休无止地推着石头,好像丝毫皈依的意识都没有;而史铁生的“过程神学”表达的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天堂的永恒的仰望。
史铁生的晚近大作《我的丁一之旅》堪称其总结性的“心灵文献”。这部作品在其思想底蕴中同时融入了某些佛教元素和基督教元素,并对这两种元素进行了创造性综合。佛教元素在于其对轮回思想的采用。基督教元素则在于其赋予那不停进入轮轮回回的不灭的行魂一个终极祈盼。他认同轮回是一种客观事实,并且,关于以轮回作为载体的“灵魂不死”的想像可能使他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残疾肉身所带来的沉重感及死亡本身的可怕,但他并没有死心塌地地领这个情,他依自己的心灵体验使轮回的客观性发生主观弯曲。行魂不断进入的轮回本身类似一个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哲学理念,是没有感情,无所祈盼的;他唤来一种基督教元素对此实施了超越,从而使轮回这种宇宙存在范式指向了一个终点。关于这个终点其实史铁生从未给出过具体的描绘,那只是他的心灵的一个祈盼,一个梦愿。那个终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会不会到来,如果到来什么时候到来,以什么方式到来,他深知这一切都是他不可能知晓的,属于他的只有祈祷。
张承志的创作在内在精神上先后发生三次蜕变。第一次是从对草原生活的追忆到朝向自然的英雄主义诉求,第二次是从朝向自然的英雄主义诉求到对自然的朝圣心理的形成,第三次是从对自然的朝圣到对人文的朝圣。对他来说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也是发生在1984年。在这之前,除《北方的河》外,张承志写的主要是草原题材和新疆题材的小说,之后转向伊斯兰黄土高原,创作思想和风格也从早期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开始转向一种民间理想主义(对一种民间宗教──折合忍耶苏菲神秘主义──的皈依诉求)。1985年,作家接连发表一批这次转向的标志性创作,如《残月》、《峰巅》、《九座宫殿》、《三岔戈壁》、《黄泥小屋》等。在这批小说以及之后的部分作品中,他对伊斯兰黄土高原的自然、人文诸事物表达了深沉的顶礼膜拜,同时他自己也仿佛感到自己漫长的漂泊就要临近终旅。
1986年,张承志发表总结性的《金牧场》。他的这第一个长篇把对他立命的三块大陆上的自然和人文事物的绘写,以及对他自己作为红卫兵、知青、学者和纯粹的自我流浪者浪迹天涯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的追忆融为一体,以传说中的五勇士对“金牧场”的寻求为主旋律,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进行了艺术总结。也是他最后决定进入大西北的内在心理宣示。作家利用这个多声部的长篇的一个小声部,追溯了自己的母族在近二百年残忍的剿杀和围困中求生存的血泪史,并触到了她的终极支撑——对伊斯兰教不灭的信仰。其实正是对折合忍耶贫穷的回民祖祖辈辈誓死捍卫内心的信仰精神的震惊和临在,使张承志仿佛找到了最终归家的感觉。他一时间远远地撤离那个依稀浮现的“家”,在大地的祭坛上漫长地总结自己,终于在自己的灵魂对那个“家”的深情眺望中发出回归的宣言。1988-1989年间,张承志又发表了《海骚》、《黑山羊谣》、《错开的花》等内在倾诉性作品,并最终于1990年写出其“生命之作”《心灵史》。而作家自己似乎也从此真正得到了精神的皈依,他自己的“心灵史”至此也似乎告一段落。
《心灵史》讲述的是折合忍耶回民祖祖辈辈誓死卫教的故事,通篇充满了宗教精神氛围。编织这个长长的故事的则是作者自己抑制不住的抒情和议论,借此,他不仅对一种九死未悔的信仰精神进行了深沉的歌颂,也抒发了自己由此而产生的浓烈的皈依之情。通过《心灵史》,他成了折合忍耶回民新的代言人;通过《心灵史》,他自己也好像最后完成了他全部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总之,张承志漂泊——回归的仪式好像在《心灵史》中激烈地结束。至此,他感到自己长期以来痛苦而执著地叩问与寻找的“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的辉煌终止,谜底全数公开”;至此,“我最后的愿望是──象他们一样,作多斯达尼中的一个人”。用他自己以前凭预感找到的词汇来说,他踏上了自己的终旅。与此同时他也宣告自己的文学“在无人的荒野登上了山顶”。
通常认为北村是作为中国先锋派作家中的一员开始出道的。他在文学方面的才气很早就展示了出来,17岁开始发表小说,而后还满腔热情地“在大学三年级开始在文学实验室里调制实验小说”。他以“者说”系列试验性很强的小说创作跻身先锋派作家之列。也许正是因为那几年北村小说所表现出的极端的叙述试验,有不少论者认为,早期的北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涌现的那批“先锋”作家中在语言运用上最富有革命性的一位(作家苏童也曾说北村是当时他们那批先锋作家中最具先锋性的一位)。对这种看法我没多少异议,不过,我认为在那“语言的丛林”下面仍覆盖着厚积的思想和精神内容,使我感触最深的成份是某种严重的形上困惑。从而我还认为,北村的早期写作实际上就是他整个“神性写作”的一部分。其中,《聒噪者说》和稍后的《孔成的生活》最明显地表征了这一点。
实际上,北村在他自己认定的那个话语之“家”里没待多久就跳了出来,并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忽然皈依了基督。对于他复出之后的创作,我们几乎可以判定为“为基督效劳”的一种工具。被公认为中国先锋派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的《施洗的河》是北村转向的标志,在“先锋叙事”中已开始传递福音。《施洗的河》中的主人公刘浪是北村的一个道具,他通过这个道具表现了一个完整的皈依的仪式。另外,在体式上,小说采用了回忆录性质的叙事模式,依时间顺序详细铺陈刘浪向杜村的传道人叙述自己过往的罪恶生活,也颇似一出漫长的忏悔仪式。小说的结尾用了不少篇幅描写主人公皈依基督福音的过程,他有过激烈的内心搏斗,不过最终还是放弃一切理性的思辩而选择了虔诚的皈依。
北村“施洗”之后的小说《张生的婚姻》、《伤逝》、《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水土不服》、《消失的人类》、《玻璃》等等,讲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绝望和救赎的故事。如果说《施洗的河》还葆有浓厚的先锋叙事色彩的话,那么北村之后的小说大多已基本不见了那种先锋性,代之以口语化的平面叙事。由于基督教世界观的决定性影响,北村的小说有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甚至可以说话语建构的事实能归约为几个基本命题):一些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人(北村选择的多是诗人和知识分子),从痛苦、空虚和绝望走向发疯、自杀或皈依。其实作家为人物指明或暗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皈依基督。
三位作家有着方方面面的不同,比如:在心性气质上,张承志更像是一位富于理想情怀和浪漫情怀的游吟诗人,史铁生更像一位约伯式的思想者,而北村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基督徒;在心灵轨迹上,有着各自的命运曲线和皈依路线图;在文本叙事时空中,张承志基本指向历史/民间,北村指向当代/都市,在史铁生那里则是“写作之夜”的自我心理时空——万事万物都可以随作家的心魂在那里汇聚。也许他们唯一相同之处只是一项重要的生命在此的指标:不懈的精神追求。
最后,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到一个对文学批评来说似乎更分内的问题:从文学的角度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评估。首先得肯定他们是作家。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作家呢?关于这一点,简单地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先来看一次民意调查:本世纪初,由上海作家协会和《文汇报》等联合发起组织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活动,据98位评论家提交的有效答卷汇总而成为推荐结果。从调查结果看,史铁生、张承志位居最有影响的前十位作家中,《心灵史》、《我与地坛》、《务虚笔记》位居最有影响的前十部作品中。虽然这种排座次的做法似有些不妥,并且,问卷调查很难说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是某种程度上还是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所评出的最有影响的前十位作家基本上还是符合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现实的。其实,史铁生、张承志在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性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他们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坛上那无与伦比的心灵品质,这种心灵品质使人们受到了罕有的感动或震动。另外,曾被不少论者认为是中国先锋作家群中最具先锋性,作品表现出对人的灵魂的极大关注,前些年又随着影视作品的烘托浮出文坛的北村,似乎也给文坛带来了些许影响。
应该说,他们都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比较重要的作家,尤其是张承志和史铁生。这主要源自他们所体现的那种精神的独异性,源自他们执拗地追寻更深广的人生意蕴的独特的生命姿态和精神力量。也就是说,在我国当代的人文语境中,他们的影响也许与他们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关系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当然,从文学的视角看,他们把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中最稀缺的宗教性因素引了进来,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表现空间,对作家创作思想的变化、对中国文学摆脱文学之外因素的长期束缚真正走向成熟肯定会起到积极的影响。毋庸置疑,他们的文学体现出某种可贵的真诚,他们的精神劳作或许也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开辟了可资汲引的精神资源。总之,这三位作家的文学劳作,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先锋文学“运动”一起,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无疑有着长远的意义。但是,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他们中有的却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好作家或大作家,并且任由发展似乎也永远成不了那样的大作家似的。他们虽然具备了成为大作家的某些内在素质,但还远不够。客观地说,从他们那里似乎也没有诞生大作品,他们要么没有大师的架构和笔法,要么没有在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他们的创作最犯文学之大忌的地方似乎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过于裸露的作家自我、观念性和说教性。透过他们的作品,我们鲜见真正的艺术思维活动和艺术劳作中那种创造的主观性的生动感性(这是作品审美品质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从真正艺术的维度上审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辩证法的惩罚(这种惩罚在张承志和北村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看起来他们自己对此并不怎么在乎。
文学的确是要表现和揭示人的实存,不仅外在的真实,而且更重要的内在的真实和深层经验。这真实本身即意味着人类精神的极大丰富性。宗教经验及诉求也许是这种丰富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远不是其全部。把文学纳入宗教,会使阅读者阅读时的精神体验空间变得狭小(美感体验肯定也会随之大大降低)。我们可以把中国当今所谓的“宗教主义写作”归为中国当代文学亟需诊治的“病症”之一(其它需要诊治的“病症”还有意识形态化写作、私人化写作、身体化写作等等)。尽管这是一种比较高贵的病症,但是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亦是有害的,就像糖尿病、肥胖症等富贵病对人的身体同样很有害一样。这一“病症”的显明症候就是使文学成为布道的或宣扬信仰精神的单纯的工具,而不是把宗教性因素(如终极关怀意识、苦难意识、悲悯情怀等)与人的精神内容本身的丰富性一起有机地化入文学。文学的力量归根结底依靠的是叙述而非说教,依靠的是对人的内心世界最真切的揭示,依靠的是通过对人的生命体验准确的叙述从读者自身精神体验的深处找到读者。一家之言,望有助于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