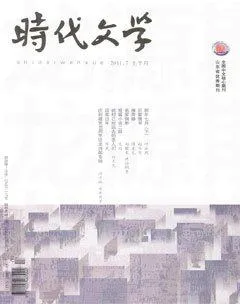刘醒龙印象
2011-12-29朱小如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7期
湖北作家刘醒龙似乎无论春夏秋冬一直留着短短的小平头,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初次见面是上海文学召开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研讨会上。那时他的小说《分享艰难》几乎成了整个研讨会的关键词。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尽管他也坦言“分享艰难”不是他的原小说名字,而是周介人给他改的,功劳还是应该记在周介人身上。但是刘醒龙这个作家就此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之列。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要求各级干部都要看根据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并要求一定要解决好乡村民办教师问题。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也的确请他来写过主旋律剧本,然而似乎又没有搞成,不知怎么回事?那几年,他一下子完成了四五个长篇小说,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还给他的《弥天》召开了研讨会。因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当然谈话的内容主要还是小说创作,从他的话语里偶然会流露出自己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上有所顾忌。他似乎更愿意人家说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
在我的眼中醒龙是个很有个性但又不是那种过分张扬的人,有一个小细节特别能看出他的为人处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坛时兴现代派小说,他在早期执着书写的一组系列小说,原本自己命题为“大别山之迷”,写得也颇有现代派风格,然而,几乎所有发表这些小说的杂志编辑,都以为是刘醒龙的笔误,问也不问就将题目改成了“大别山之谜”,于是此“谜”决非那“迷”,少了现代派的许多意味,杂志出来之后刘醒龙傻了,但毕竟木已成舟,刘醒龙只能默认而已。以至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刘醒龙的小说创作起步实际上和现代派文学有着紧密的关联。
刘醒龙的小说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海外也很有影响,美国的一位女作家翻译了他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把他看作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前几年还特意来中国,并到刘醒龙的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湖北英山,实地考察大别山一带的风土人情。为此醒龙还特意邀请了我一起参加,见到了刘醒龙的父母及家人。可能是因为刘醒龙的父亲也是县里的乡镇干部,他家的小院挺漂亮。种着的石榴树高高地悬挂着果实,还有伺弄得十分整齐的花草。醒龙在老家当过工人。英年早逝的作家姜天民在县文化馆工作时,是他的兄长和朋友。姜天民因小说获全国奖而被调走后,醒龙就被调到文化馆搞创作,就连所住的宿舍,也是姜天民先前住过的。以后,他也被上调到了黄冈和武汉。大别山一带的风土人情在我看来到也没有多少人杰地灵的环境,相反和其它山区一样,凭借那样的人文气息,刘醒龙的平步青云显然要有着超常的毅力和信心。刘醒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做任何事,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打扑克,打麻将,总有那么一股不服气和不服输的劲头,甚至是不求输赢,只要一时的酣畅。
他新出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一百万字,囊括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的厚度和复杂人性的深度,前后花费了六年时间。在我看来其动力也是出于那么一股不服气和不服输的劲头,因为当时在《弥天》的研讨会上,有评论家发言认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到《白鹿原》已是不可超越的,谁再写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想刘醒龙的那口气一直憋着,直到《圣天门口》写完才放松了。
凡见过刘醒龙“风华正茂”的模样,很难料到刘醒龙也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尤其是他讲话的语速快捷有力更显得精神抖擞。惟独他的语速放得舒缓甜美之时,那一定是在和家里的小女儿说话。我曾经建议他再写就写一本专门给女儿读的书,不要像《圣天门口》那么长,那么厚重。醒龙后来还真的这样写了,这本关于写给天下所有做女儿的人看的书正在定稿,很快就要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