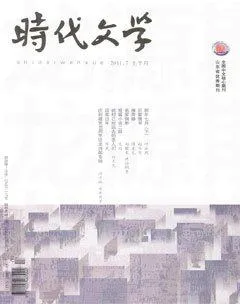故乡意象的生态美学
2011-12-29陈艳丽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7期
主持人语: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散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人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了散文研究的弱势现象,这种弱势现象与散文的大发展是很不相符的。本期的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散文发展的状况,既有宏观勾勒,又有微观探析,希望给读者展示出散文发展的总体状况和个体艺术。时代变换,潮流更替,新世纪的散文潮流千帆竞渡,令人目不睱接,文化散文、新乡土散文、新散文、新媒体散文等主要潮流既促进了散文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值得省思的问题。乡土散文以故乡为意象记录了乡村文化在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契合了生态美学的美学原则。汪曾祺、刘亮程以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解读故乡的文化意蕴。西部散文是中国散文的一处独特的景观,西部散文全力彰显的是一种极具优越感的生命精神,生命精神是西部散文的真正核心,也是它的独特魅力。铁凝的散文不愧为心灵的牧场,读来使人心境平和,我们在其中参透的不仅仅是美好的人生;林非是一个真性情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散发着人性光辉和哲理韵味。在他的散文世界中,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美,更有一种对于历史、民族和人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是我的五位研究生,对新时期散文创作的状况及作家作品的研究分析,正如古人所讲“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五篇文章,“向管中窥豹寻知外”,只是做了一个大体的分析研究,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王景科
作为绿色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新时期乡土散文的故乡意象的营造和解读在不同程度上契合了生态美学的哲学意识和审美内涵。这些作家以故乡作为切入点,把自己对自然、人类、生存,以及文化延续这些生命本体的思考表达出来,构成了生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乡是中国乡土散文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审美意象。故乡意象在古代文学中就已经成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写作范畴。自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文学中的乡土内涵不断丰富和变化,尤其是在今天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农村城镇化,使乡土的社会内涵和外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中的故乡意象的文化意蕴就有着辐射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
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新时期乡土散文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故乡的独特魅力。在这种稳定的社会背景下,作家们以在场的叙述方式,慢慢地咀嚼和品味着故乡的宁静和厚重,质朴和悲凉。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发展,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的农业传统在慢慢改变,乡村城镇化的经济模式使古老的乡村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随之消失的,不仅仅是一处处村庄,而是寄托在村庄之上的乡村文化,于是,乡村的文化意蕴也慢慢地消失,随着那渐渐远去的背影扑面而来的,竟然是以刘亮程为代表的二十世纪最后的乡村歌者的声音,他们的乡土散文以一个在者的形象急切而亲切地描摹着乡村的一草一木,一风一雨,用琐碎细腻的笔触为将要远去的乡村作工笔似的画像,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以嵌入的姿态书写着故乡的灵魂和生命的追问。村庄渐行渐远,而故乡的文学形象却以越来越清晰的姿态凸立在我们面前,引起我们对民族文化的深思和追寻,引起我们包括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在内的整个生态存在的深思。品味汪曾祺的故乡情怀,思索体验刘亮程的故乡的追问,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乡土散文叙述方式的转换和对人性的思考的变化,从而触摸到故乡意象背后的文化意蕴的传承和创新。
生态回归:童真的在场与自在的和谐
汪曾祺如此定位自己:“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他在社会相对稳定的背景下,细细回忆和琢磨着故乡的风俗文化、以亲在的方式把握故乡中的小人物、小掌故、小风情。琐琐碎碎的花鸟虫鱼、瓜果食物,在这些民俗风情中,体验着生的欣悦和自在。海德格尔认为,故乡将每一事物都保持在宁静和完整之中,它让每一事物在它的作用下自由地徜徉着。故乡就是神圣,是众乐者之源,是澄明之境,是极乐;在故乡的怀抱中,“一切纯净之物都沉浸于明澈之光华中,一切高空之物都矗立于高超之威严中,一切自由之物都回荡于欢悦之运作中。”①故乡允诺给每一事物以本质空间,使每一事物按其本性属于这个本质空间,以便在它那里,在故乡神圣光辉的照耀中,满足于本己的本质。真正要达到对故乡的理解和体会,只有在每日的日常生活中去感受生命带给我们的每一丝体验,故乡在这日常中才会得以昭显。这种哲学思想体现在生态美学中就表现为主张包括眼耳鼻舌身在内的全部感官在审美过程中的介入,这是借鉴了西方环境美学的“参与美学”观念。汪曾祺曾经说“我认为,民俗,不论是自然形式的,还是包含着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欣悦。它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互相交流,融为一体。”②这种民俗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故乡的感觉:对生的挚爱和对“活着”的欣悦,生是一种诗意的活,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一种人对自然的回归。生态美学反映审美主体内在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性,在这里,审美不是主体情感的外化或投射,而是审美主体的心灵与审美对象生命价值的融合。生态美学观将美看作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生态审美关系。突破了对美的主客二分的僵化理解,将其带入有机整体的新境界,是对人的生态本性的一种回归。将主体性发展到“主体间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这和实践美学有着巨大的差别, 实践美学特别张扬人的主体力量,这就完全抹杀了自然的价值,表现出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汪曾祺所要表达的正是自己与故乡的这种相互参与以及和谐。在他面前,故乡的自然万物和自己是有着同样的生命活力的,自己与故乡的一切相濡以沫。《葡萄月令》中的葡萄不是一棵传统文学中的仅供结果的植物,而是有着自己的生命四季循环的生物!他在叙述方式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含蓄、写意,但同时又把自己对故乡的感受和体验写得细腻婉转又明白如说话。把对故乡的深情藏于对人、景物的精雕细刻之中、渗入字里行间。是一种可感不可触摸的体验,一种延续周作人的冲淡平和之外的质朴亲切,以一种和欧化语背离的诗化口语来娓娓诉说故乡的风土人情。李陀曾经说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是一种“写话”的境界。但这种简洁浅晰的白话却传承了汉语的含蓄、诗意的传统意蕴。不讲究欧化的语法,语词极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随上下文的声气、环境而自由运用,汉语富有弹性和张力的特点使他的文章有一种“沧海月明、蓝田玉暖,不能自已”的美感(李陀语),这种文体风格使汪曾祺对故乡的描摹有了一种疏朗的亲切感。“我”在故乡琐琐碎碎的一切之中,故乡的琐琐碎碎也在“我”之中。可是你又找不出具体哪一处、哪一点!一种人生和生命的自在和妥帖在这诗意化的口语中渗出来。它超越了审美主体对自身生命的确认与关爱,也超越了役使自然而为我所用的实用价值取向的狭隘,从而使审美主体将自身生命与对象的生命世界和谐交融。生态审美意识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而且是生命的共感。生命的共感既体现了生命之间的共通性,也反映出生命之间的共命运感,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独奏曲。故乡的一切是那么真实亲切,亲切到他的多数篇幅都用了童真的视角!以一种稚子的心态来体会和琢磨故土,一种源于生命深处的陶醉浸透在字里行间,这是汪曾祺对故乡的真实感受。《端午的鸭蛋》中的“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种语言是不能用欧化的精确的语法来规范的,但字里行间的童趣和真情却以一种可感可触的形式显现。所以说,汪曾祺的乡土意象是一种童真的在场解读,同时又是一种与故乡融为一体的自在,是一种立足于生态美学的和谐,是对人的生态本性的一种回归。人的生态本性决定了人具有一种回归与亲近自然的本性,人类来自自然、最后回归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故乡孕育了我的一切,我在故乡的一切之中,故乡是我灵魂永远神游的地方。表达的是一种人际间现世的温情与欢悦。故乡和我同样以主角的形式出场。我的自在也是故乡的自在。这时的中国乡村是一种自在的生态存在状态。
生态共生:劳作者的亲在与生命的追问
社会的变化深深地影响着文学的变化。随着社会的转型,在城镇化的经济形式之下,农村文化渐渐衰落下去。与一座座村庄一同衰落消失的,是寄生于中的宗族文化、民俗文化以及有关乡村的一切文化形态。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乡村,正渐渐消失在大地之上,而与之相反的竟然是文学乡土作品中故乡的形象却突兀起来,以前所未有的具象形态矗立在这些作品之中。这似乎是文学对文化的记忆和延续功能。这些乡村意象不仅引起我们对自身与故土关系的思索,而且使我们把思索的目光投向整个民族、整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以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社会和文学的可逆性解读。这实际上就是生态美学所研究的生态整体性。生态整体主义之生态平等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抛弃,生态整体主义所主张的“生态平等 ”,不是人与万物的绝对平等,而是人与万物的相对平等,即为“生物环链之中的平等”。人类将会同宇宙万物一样享有自己在生物环链之中应有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只是不应破坏生物环链所应有的平衡。生态整体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形态就是当代深层生态学,其核心观点就是“生态平等”,也就是主张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都自有其价值而处于平等地位。
新时期三十年乡土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学形态,陈白尘、陆文夫、汪曾祺的江南水乡散文散发着水乡的灵动和氤氲;刘成章、周涛等人的西部散文带着西部的风沙和雄浑;贾平凹的西部乡村散文唱出了农村文化渐趋没落的哀歌③。这其中最让我们警觉的,应该是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散文家”的以乡村劳作者的姿态进入文坛的刘亮程的乡土散文。在刘亮程的散文中,具象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生态整体的思考和追问,故乡以一种绝对的优势的形象突兀在文坛之上,故乡的人都躲在了村庄的背后,逃跑、出走、消失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曾经存在。整个村庄只剩下一个人——《一个人的村庄》,就是这一个人也是一个耕耘了多年没有撒下一粒种子的似乎多余的存在。故乡的一切,卑微如小虫、草木,显豁如耕作的老牛和驴子,都以研究和鄙视的眼光看着“我“的存在。在渐渐衰落的乡村中,蓬蓬勃勃生长的却是有关故乡曾经存在的一切证据:老狗、驴子、老牛,还有永远割不尽的野草。作为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深层生态学中有一个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原则,其基本含义就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者都有生存、繁衍和体现自身、实现自身的权利。在生物圈大家庭中,所有生物和实体作为与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的内在价值是均等的,“生态”与“生命”是等值的、密不可分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是相同的。人类作为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把其放入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并不能得出比其他生命形式高贵的结论。用马斯洛的话就是:“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至少和自然有最低限度的同型性(和自然相似)才能在自然中生长……在人和超越他的实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裂缝。”在刘亮程的散文中,所有故乡的一切都有超越人类的人性,而寄生于其中的人性却渐渐衰微没落!这是一个文学的寓言:其实随着一座座具象的乡村消失的,不是自然的本性而是人性!不是自然的生机而是人性的生机!故乡意象在刘亮程的笔下已经不仅仅是以人为主观视角的审美客体了,而是一个对人类生存存在的追问的象征。这是一种将审美从单纯的认识领域带入崭新的存在领域生态美学观,他将不可或缺的自然的生态维度带入审美领域,使故乡意象由审美走向存在。刘亮程就以这种乡土解读方式诉说着乡村意象对于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为了达到自己诉说的目的,刘亮程以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喃喃自语又絮絮叨叨。他的语言充满了矛盾的张力,谢宗玉在《解读刘亮程》中说“写诗的刘亮程已把文字练得就像在清澈的河水里淘洗过一样,他的文字常常让你读得心尖尖像被针尖尖在挑”。实际上这段话只是说出了刘亮程语言给人的审美体验,没有说出刘亮程语言的独特之处。刘亮程的语言感受实际上和他的乡土感受是一体的。张治安、吴孝成认为刘亮程的语言有五种:白描式、独白式、调侃式、俚俗式、惊警式。其实刘亮程是以一种体验的在场言说方式运用他的语言,他把人们已经麻木和被遮蔽了的自然感官拯救出来,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世界本来是以诗化的形式存在的,西方的哲学转向就是在寻找人来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似乎解开了这个谜团。所以在刘亮程的笔下故乡的白描背后实际是关于生命和存在的哲理和诗意。在这种言说方式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生命的关联,这正是生态美学的一个突出特性。在刘亮程的乡土散文中,故乡以具象的形式渐渐衰落,但作为人性代表的我却以哲思的形式留在了这片曾经存在的土地之中。“我”以亲在的形式实际上是边缘化的、寄生在故乡之中。留在文学的殿堂中的,是虽然具象远去但依然永恒矗立的村庄和虽然曾经存在但人性和生命力逐渐衰微的那个人。弥漫在故土上空的,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追问和探寻。
文学是另一种历史,是具象的历史形态。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实际是把一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向全球开放的现代化强国,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过程中,作为历史基本因素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就必然面临着不断地选择和变化,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侧重都会以另一个或几个因素的弱化为代价的。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在现阶段是不可否认的以弱化某些文化因素为前提的。而城镇化的经济模式,对我们传统的农业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冲击甚至破坏,而这种影响又会对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前景带来怎样的变化,引起一代一代的文学家们用自己的作品来思考和追寻。作为新时期中国乡土散文的重要代表,汪曾祺、刘亮程用自己独有的叙说方式来记录和思考,以故乡意象为切入口为农村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作了生态文学的诠释,成为新时期乡村历史的具象解读。
注释:
①(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孔周兴译.北京: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