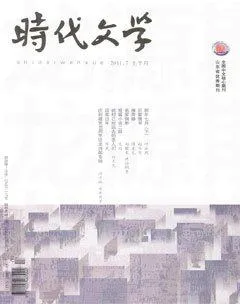艾玛:刚强而温和的慈悲
2011-12-29赵月斌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7期
艾玛的短篇小说《浮生记》,写过这样一个情节:学做屠夫的新米头一回杀猪,不仅显示了“令人叫绝”的好刀功,而且让师傅看到: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在温和的外表下,有着刀一般的刚强和观音一样的……慈悲!”如此感受,得之于一个小小的细节:单薄的新米在“手起刀落、神情专注”地行使屠夫的本分时,还顾惜到了“躺在条凳上的猪无助地将头后仰,它嗷嗷叫着,双眼潮湿而惊恐”,所以,他未忘腾出一只手来,把猪的双眼一一合上。这个不起眼的小动作让老屠夫感动得潸然泪下,也让他对死去的结拜兄弟——新米的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在六七千字的篇幅中,艾玛迂回缀合了两代人的故事:他们或靠做活谋生,或为谋生而死,在生生死死恩怨交割之中各有各的情理因由,但不管生存条件如何冷酷,“刚强”的人们总能释放出可以相濡以沫的“温和”,最终攒下合适的温度,从而达成和解。
从处女作《米线店》,到《浮生记》、《开满鲜花的土地》、《小民还乡》、《万金寻师》等一系列以涔水镇为背景的作品,艾玛在叙事上有着一贯的从容淡定、不温不火的自信与自觉,因此,她的小说素材虽然多为不起眼的凡俗琐事,但是讲出的故事却能别有一番滋味。这滋味得益于质朴而节制的语言,得益于小说的叙事氛围,当然更得益于艾玛表现出的亲和与包容,她好像总能够在不经意间将你拉入到“涔水镇”的语境中,让读者和小说人物共同充当故事的推手,从而使小说大大突破它的文本格局,获得甚为广阔的势力范围。她的小说常常就是这样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一场追魂夺魄的搏杀。
本期同时刊发艾玛的两个短篇小说《一只叫得顺的狗》和《弯刀》,依然遵行了她的“和解”路线,体现出刚强而温和的慈悲。像《浮生记》那样,艾玛还是用简短的文字讲述了两个并不曲折的故事,尤其是《弯刀》,甚至可以说近乎看不到故事,作者所做的,只是借助一个小孩子的有限视角,探察成人社会的重重隐秘。正如毛毛为桔树治病一样,他以为用铁丝从树洞里钩出虫子很值得骄傲,却不明白爸爸、妈妈为何不以为意,他只觉得他们“有些不对头”,他不知道大人们既要面对恶人,还要面对自己的内心。那把弯弯的短刀,原是可以壮胆的,在被爸爸擦拭之后,却让毛毛“头一次感觉到了恐惧”——这“恐惧”很可能意味着童年的结束,让一个孩子瞬间长大。小说结尾写道:毛毛在爸爸温暖的怀里,“重新回到了宁静”。显然,艾玛的落脚点仍是和解。虽然爸爸也说“遇到恶人做恶人”,虽然他拿出了短刀,但作者早已用神父、《圣经》、爱人等温暖的语汇阻止了他,属于我们的,必然是狂风暴雨之后的一片宁静。
《一只叫得顺的狗》相对好看一些:写的是一名酷爱食狗肉的警察,对细腻肥嫩的母狗肉尤为看重,他极其细心地饲养母狗,为的是好好地吃狗。但是,小说里的“阿黄”很走运——不仅没被吃掉,还很长寿地活了二十多岁。原因不是那位狗肉警察改了食性,而是因为阿黄怀上狗崽子——当然,根本原因还是这名警察,若非他的“成全”,阿黄也不可能成其好事。仅只这些还不够,关于该狗肉警察,重要的却是另外一笔:他亲手抓住的女毒犯在被处死前托他照顾一家老小,他由此对“一报还一报”的行刑产生了“厌恶”。正是那女犯的死,让这位酷食狗的警察有了测隐之心,所以才有了阿黄后来的幸福时光……一条狗命,照见人心。在这篇小说中,艾玛恐怕还是在揣度人心的柔韧度。善说鼓书的梁小来是一种,酷食狗肉的警察又是一种,当他们一致把阿黄叫成“得顺”时,很可能,二人的心里都极其柔软。
艾玛是学法律的,她的小说也或多或少地可见其法学背景,但她从未生硬地强调法的力量,或者装模作样地以案说法。虽然她的小说常会有非正常死亡,会有杀戮、苦难,但她不去虚张声势地渲染某种宏旨大义,而是以一颗怜恤之心,去描绘生活的肌理。她关心阿黄,也欢喜得顺;她欣赏说书人,也顾惜女毒犯。因此,她的文字刚强而温和,她的小说像倾之不尽的大碗了一样盛满了安详与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