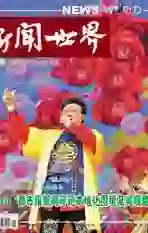论电影《盗梦空间》的叙事结构
2011-12-29马青青
新闻世界 2011年7期
【摘要】2010年,克里斯托弗·诺兰把一个写了近10年的故事搬上荧幕,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绝不仅仅是一部感官大片,“梦境”这一母题的描述多少给《盗梦空间》增添了一丝“心理悬疑”的色彩。电影未上映之前影评界的热烈追捧,剧组创作成员的闪烁其辞,都让《盗梦空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如电影本身要为我们表现的主题一样。影片的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采访中说:“这部电影,完全是克里斯托弗·诺兰对梦境的理解和想象,里面有特有的结构、规则,这些也是诺兰的创作内容之一。”如果将电影界比作浩瀚的宇宙,那诺兰一定是擅长电影叙事形式主义的一朵奇葩。
【关键词】《盗梦空间》 叙事结构 复调叙事 叙事角度
一、《盗梦空间》内容梗概
弗洛伊德说,“梦境是避开压抑作用的迂回之路,它是所谓的间接表白所用的主要方法之一。①” 14年前凭借影片《泰坦尼克号》走红的好莱坞男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男主角唐姆·柯布是一名高科技窃贼,他利用在人的梦境中窃取有价值的商业机密的盗窃手段而获利,他认为人的潜意识是可以被操控的,潜意识的能量也是不可估量的。因此,人可以在梦境中发挥几乎是全知全能的能动性去获取一切需要获得的信息。在对潜意识能量的探索中,柯布丧妻,并且被指认为杀妻凶手只能远走海外,丢下家人开始流亡的生活。柯布在一次对商业巨贾齐藤的任务中失利,却反受雇于齐藤,此次任务的内容是对齐藤竞争对手的新一任继承人植入“解散家族企业”这一意念,而相应的回报则是撤销对他的指控,重返美国和家人团聚。
二、叙事角度的糅杂与转换
普林斯认为叙事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它研究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的性质、形式和运作规律以及叙事作品的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叙事能力。如果将电影《盗梦空间》作为艺术文本来研究,那么导演诺兰的叙事功底在影片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电影作品从文字文本转化为视听语言,是导演在其统一的意志下层层铺开的过程,为了丰富作品的张力和表现力,往往会采用多角度叙事来进行展现。“在叙事作品中,视点不仅反映叙述者和人物的所知、所感和所为,他还反映叙事作品作者的心理、立场观点和意识形态。②”大体上来说,叙事角度一般分为:全知全能叙事,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由于母题是“梦境”,电影主要展现的是主角如何潜入他人梦境并窃取机密,《盗梦空间》在叙事角度上主要采用纯客观叙事,这种叙事手法,也称第三人称叙事。托多罗夫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者小于人物”的叙事视角,这种视角能充分的展现客观生活,以及客观事物发生的全过程。采取这种叙事视角,也为《盗梦空间》蒙上了一层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但本片并不是单线展开叙述,诺兰为柯布预设的感情奠基也是其中一条重要的叙述线。在“回忆”的部分,采用了以柯布为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视角。主客观多方位的叙事手法,使该片在叙述视点上转换糅杂,显得更富张力。与此同时,也给观影者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其投入更多的分析和关注去感受和理解该片意图。
三、叙事结构的交叉变异
电影《盗梦空间》在“柯布完成齐藤的任务”这个主系统和多个“每一层梦境”这样的子系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结构来构架。
在“柯布完成齐藤的任务”这个主系统的故事中,诺兰采取了传统的因果式线性结构。虽然作为科幻悬疑电影,影片在一开始并没有透露时间地点这样典型的表明因果的信息,却花费了近15分钟的时间去表现一次盗梦任务即“盗取齐藤的信息”,而这场任务的失败却成为整部电影发展的一个诱因——齐藤反雇佣柯布。随着这次任务的展开,故事线条逐渐清晰,人物心理性格也得到了充分的描绘。主线追求情节的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完整,并有相当激烈的外部冲突。比如天才造梦师阿德涅与柯布的相遇,学习如何造梦,和她得知柯布内心深处的情感秘密之后所遭受的心理冲击;盗梦团队的组建,各类人物的参与,都和整项任务密切相关,且具有明显的目的性。
在子系统中,也就是“每一层梦境”的叙事结构上,诺兰采用了“回环式套层结构”。回环式套层结构,是以多层叙事链为叙事动力,以时间方向上的回环往复为主导,情节过程淡化,讲述方式突显。这种叙事结构是一种非线性的结构,即不以时间为发展线索,强调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以理性的思维去思考建构,从而理解影片意义。柯布展开的盗梦行动这个部分,一共四层梦境,每一层梦境都是以上一层梦境而展开,深入,最后通过外部的刺激而回到上一层梦境中。每一层梦境都是下一层梦境的驱动因素,为下一层梦境提供可能,次级梦境则是上一层梦境中任务得以成功的保证。这样的套层使得影片情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并使得影片节奏更加明快和紧凑。在最后一层梦境,也就是柯布和梅尔建造的荒芜中,柯布终于走出对亡妻的愧疚,找到在梦境中死亡的齐藤并成功的将其带回现实。同时,也意味着柯布这个角色完成了对自己心灵的救赎,使得全片的感情线得以完整和升华。在笔者看来,影片中没有出口的楼梯和永远不会停止转动的陀螺,恰恰意指这种潜在的循环往复性。
《盗梦空间》中,梦境里的时间比现实中的时间慢很多,时间在这里产生了一种“缩放效应”。现实中的一小时,等于梦里的五分钟,而上层梦境的五分钟,又等于次层梦境的一周时间。在梦一层层深入的时候,时间在这个时候反而以一种相对的形式发挥作用。因此,在各层梦境同时发生深入的时候,交织式对照结构讲述了子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在首层梦境中汽车落水的几十秒钟与后层梦境时间上的畸变,以及影片开头柯布落水,而梦境被大水淹没给观众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压力,都体现出这种对照结构的魅力。
四、“复调”叙事手段的运用
在细节的处理上,导演更多的运用到了“复调”的叙事手段。
“复调”最初是一种音乐术语,后来被引用到文学领域。巴赫金用复调这一术语来开拓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即在一部完整的小说中存在的“多个声音”。后来这一术语更被广泛的应用到美学,电影学等多个领域。梦幻式复调结构具体表现为电影当中现实和梦境的对话和冲撞,以凸显人物的“心理时空”,深入刻画人物性格。电影中,意识与潜意识(梦境)的冲撞也是复调的主要体现。现实中柯布深怀对亡妻梅尔的愧疚,亡妻的意向却不断的在梦境中出现,并且犀利激烈地责骂柯布,不仅加深了柯布的愧疚,同时也延伸了他对梅尔延绵不绝的回忆。现实中柯布对儿女的热切思念,而梦境中却总是出现儿女定格的背影,可以说是柯布有意识地对自己潜意识压制的结果,却遭到潜意识的反攻,最后潜意识竟成为任务最大阻挠。在最后一层梦境中,柯布与梅尔重遇,柯布回归现实的意识最终胜利,意识与潜意识得以同化,两者由对立面达到统一。
《盗梦空间》突破了传统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多视角转换和多结构的糅合,打破了时间的固定性,扩大了时间的畸变和夸张的场面运动设计,对于导演本是一场挑战,而观众也在导演的巧妙叙事下,经历了两个半小时的奇妙之旅。影片的最后由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结尾,开放式的结局,留予了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正因如此,也加强了观众对电影文本的自我构建和解读。
参考文献
①弗洛伊德:《少女杜拉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08
②祖国颂:《叙事学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传媒系)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