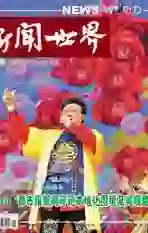《大公报.文艺》的“公共领域”雏形
2011-12-29汤菁
新闻世界 2011年7期
【摘要】本文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回溯特殊的历史时代下,近代文艺报刊从文学走向政论的转变,由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对比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并提出了这类似“公共领域”的报刊的存在价值。
【关键词】《文艺》副刊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
跨越文化和历史语境,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进中国,许多学术界研究者希望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找寻公共领域概念的普适性。
许纪霖先生认为,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的,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下,近代《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从一开始的文学性逐渐走向综合性,从创刊时的文学团体式沙龙到集体书评、编读互动,这些独具特色的报刊风格与演变过程隐约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着诸多契合点。
一、书评——另一种对社会议题的反映
萧乾认为“书评是当时文化界有待填补的空白”,“是现代文化事业里的一个新兴势力”①。他尤其重视书评的积极作用,把它看作“读者的顾问,出版界的御史”②。而书评专栏在萧乾看来也“不仅仅是报刊上偶尔设置的一个栏目,而是现代文化这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③。他自己也称书评是“介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而对“书评”的倡导,使得“书评简报”专栏得以诞生。
书评是文学作品、书籍进行评论或者介绍的文章。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期,文学作品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公共议题”的文学作品更承担着对公众的文化启蒙的重任。对文艺的理性批判,也使得《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文艺阵地。主编萧乾力求公正、独立的态度也使得《文艺》副刊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理性客观的刊物风格。从某个角度上,这也契合了哈贝马斯所提到的报刊的理性批判精神。
自五四运动起,新文化运动浪潮席卷全国,“四大副刊”承载了向封建专制思想文化开战,弘扬科学民主精神,将新知识、新思想带入人心的历史使命,而《文艺》则以推动新文学的成熟发展为己任。1935年至1939年,萧乾任《文艺》副刊主编,在其任期间,《文艺》副刊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与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是《文艺》副刊第一次用书评形式在大众媒介上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并且引起了社会上对文学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当时对曹禺的作品《日出》的集体评论,萧乾在“编者补白”中说明:这是一次“超攻讦”、“超捧场”的批评。④不论是文坛前辈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对《日出》在勉励赞扬之余,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客观而中肯。“集评”之后,曹禺以自述《我如何写〈日出〉》的刊发作为对这次集体评论的答辩。面对这场跨空间的读者作者大讨论,曹禺对许多作家的意见做了逐一回答,也在结尾对《文艺》这一平台组织的这次集体评论表达了深挚感激。⑤
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不仅仅是传媒与文学有机合作、密切结合的历史个案,亦是由精英带动大众进行的一场社会大讨论。
二、京派文人俱乐部——“沙龙式”的公共交往
“1935年我接手编《大公报·文艺》时,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这样的文人俱乐部式的茶会常常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家中,朱光潜、卞之琳、靳以、巴金、冯至等京派中坚几乎每次必到。萧乾回忆的正是《文艺》前主编沈从文由上海重新回到北平时期的情景,其与《文艺》的正式诞生有着莫大的联系。1933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9月《大公报》的第一个纯文学副刊《文艺》诞生。
《文艺》副刊此刻已经不仅仅是个刊物,而是密切联系像沈从文之类的大学师生,作家读者,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小团体。每个人的文学主张在这里激烈碰撞,再由《文艺》作为对外的窗口刊发,课堂上的互动变成了实践,少数人的唱和变成多数人的发言。⑥
从私人的聚会,到形成了公共团体的对话,再到报刊“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的接受者”,这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说到的“自发聚集的文学公共领域”是相契合的,京派文人俱乐部这种沙龙式的公共交往,也奠定了《文艺》副刊的历史地位。
三、专栏“读者信箱”——与大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互动平台”
《文艺》副刊刊有读者来信和编者答复的“通信”或“读者信箱”栏目,它为编者与读者之间提供了互动的空间。
萧乾是一位讲究“互动式操作”的编者。他在《文艺》上开辟“编者、作者、读者专栏,力求在三者之间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反映刊物的新打算,作者的新动向,读者的新要求,以及对已发作品的片断意见或对个别谬误的订正⑦。“答辞”小专栏是用来回答投稿读者的各种问题。之后巴金又将这些“答辞”和沈从文类似文字一起合编成《废邮存底》,统一出版。
在萧乾观念中《文艺》是个圆桌,而不是个讲台,他并不希望其成为编者的自白,这是他在任主编初期就强调的。⑧读者来信踊跃,有关于《文艺》内容本身的问题及观点,还有谈升学的,谈恋爱问题的,更多的是谈到青年未来出路的。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大众读者的需求与当时环境下青年人内心的焦虑状况。此刻的《文艺》似乎扮演了青年导师的形象。⑨萧乾致力于做好这项工作,他每天站在排字房按照版面所差的字数给读者写《答辞》。
萧乾认为,对于整个文艺界来说,副刊“不失为一个论坛,一个不容轻易放弃的阵地”⑩,进而还是“中国促进文学昌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⑾。
“通信息”,并不等于迎合读者,萧乾的编辑观使得《文艺》副刊,这种对大众开放的论坛式的报刊,在编者、作者、读者的互动中对文学话题的探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培养了受众,促进他们在精神层次上的交流、对话。
四、“综合版”《文艺》——具有战时政治色彩的“公共领域”
抗战时期,由于时局的变化,主编萧乾赋予了《文艺》新的定位。“《文艺》过去从不登萎靡文章,现在仅仅那样就不够了,我们把文章变成信念和力量。”他在《文艺》复刊词中申明到。⑿他意识到刊物不能像和平时期那样仅仅是文学话题,更充分地宣传抗战并起到鼓舞战士的作用,更应该去表现战争。
随后,《文艺》开辟了专栏和特刊《战地书简》和《作家行踪》,用来刊发一些来自战场的战地记者文章。1939年春,《文艺》推出“综合版”,这使《文艺》打破了纯文艺的框框,拥有了政治色彩,当时也被一些老先生指责,但是萧乾坚持认为在非常时期,就应该用非常的形式来编。
萧乾自己也认为,“自从我接手编《文艺》以来,它经历了一番巨变。原先它穿的仿佛是士大夫的长袍马褂,联系较多的是五四早期的老作家。我经管后,新一代作家群成为中坚力量,可以说穿的是学生服。在香港复刊后不久,学生服也穿不住了。随着大时代形势的演变,刊物换上了戎装。”⒀《文艺》的历史嬗变也是踏着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脚步,这样的变化也使《文艺》本身得到了升华。
战时的《文艺》走下了文学的高阁,走向了战火纷飞的大时代,这样的“与时俱进”,已经完全改变了《文艺》本身的“文艺”色彩。但战争作为其“公共议题”是顺应时代的必须。当时代的主题已经成为“战争”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和公共报刊无可避免地指向带“战争”色彩的文学作品或者纪实性报道。文艺作品也是社会议题的反映,人们更愿意在其中寻找到现实的影子。
五、“公共领域”雏形的存在价值
观照不同时期《文艺》副刊的特征,契合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某些特征:理性批判与表达、公共性议题、平等自由的讨论空间。其从文学的探讨到政治社会议题的历史流变也契合了欧洲“公共领域”的发展变化。
但是,中国和西方的公共领域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公民意识”这些概念实则是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在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中,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如果不具备可以产生独立的“公共性”的社会大环境,就无法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无疑,当时这种似“公共领域”的报刊,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大众的舆论空间,设置了公共议题,尤其是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有着它的积极意义。
恰如社长胡政之多次嘱咐过萧乾说,“我们并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专在名流上着眼,你多留意新的没人理睬的。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推进力,那就够了。”⒁
参考文献
①⑧⑿⒀萧乾,《我与大公报(1935-
1939)》[A].《大公报人忆旧》[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②⑾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J].《新文学史料(第2辑)》,1979
③李辉:《书评面面观》[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
④《编者补白》[N].《大公报·文艺》,1937-01-01,(第276期)
⑤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总第四十四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⑥刘淑玲,《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6)
⑦萧乾:《我这两辈子》,人民日报出版社,l995
⑨萧乾,《我当过文学保姆》,《新文学史料》,1991(3):30
⒁萧乾,《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辞行》[N].《(香港)大公报·文艺》,1939-09-01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