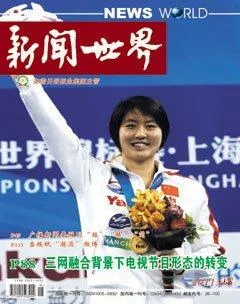浅谈我国家庭伦理剧的责任问题
2011-12-29刘艳白丽媛
新闻世界 2011年8期
【摘要】家庭伦理剧以社会道德为题材,以人伦情感为主线,以婚姻、家事、家族和姻亲的诸家庭伦理关系为内容,在社会转型时期迎来了收视热潮。但以市场为主导,我国家庭伦理剧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片面的“反现实社会”的现象,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笔者通过分析“韩国模式”的特点,试图找出我国家庭伦理剧发展的新出路。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 韩国模式 责任
每一部家庭伦理剧都对应着某种心理原型。家庭伦理剧是一种以反映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通俗剧,具有较强的世俗性和大众性。在我国,家庭伦理剧是最具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叙事方式,或者可以称为是一种婚姻家庭的智慧面具,是存活于现实世界的虚构性的叙述加入了人们的想象、幻想、情感和欲望等组成的一种凝聚物。
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的。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中,传媒被赋予了6项任务:⑴为政治制度服务,提供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观点和讨论;⑵启发民智,使之能够自治;⑶监督政府,保障个人权利;⑷为经济制度服务,利用广告沟通买卖双方的商品和服务;⑸提供娱乐;⑹保持经济自立,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压迫。①
我们所谓的媒体责任是媒介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同时,还应履行维护社会良知、教化民众、弘扬正义、捍卫真理等责任。
一、家庭伦理剧的热播现象
一部优秀的家庭伦理剧总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地域、年龄和文化的差异,产生巨大的影响。继万人空巷看《渴望》的热潮后,新时期的家庭伦理剧收视率继续一路走高,《新结婚时代》收视率达8.78%,《金婚》收视率达13.6%,《蜗居》的收视率达9.6%。剧中人物海藻、海萍、宋思明、佟志、文丽等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人物,剧中人物之间的每一次冲突都会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应。
家庭伦理剧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平淡中见真情,如《渴望》、《金婚》,人物性格鲜活,生活细节生动,观众可以慢慢品味。另一类的特点是矛盾激烈、冲突夸张、情节极致、故事离奇,靠编故事来抓人。如《蜗居》将视角聚焦到都市人最关心的“房子大事”中,展现老百姓买房、供房的种种经历,讲述主人公一波三折的买房奋斗史。
二、家庭伦理剧热播的原因
1、社会原因——人际关系紧张和信任危机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以及体制的改变引发了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利益成为激励社会行为的重要砝码;与此相伴随,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物质刺激强烈地引导着人们的生活。
物质利益的快速膨胀给社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和信任危机,“亲情”、“和善”、“礼让”等传统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竞争”、“自我发展”、“享受”这样的现代价值观念。人们呼唤传统价值的回归,孤立的个体越发依赖家的温暖来抚慰在激烈竞争中受到的创伤和产生的失落感。正是这一意义,使人们对新时期家庭伦理剧给予较多关注。
2、家庭伦理剧的特点——现实和剧情的结合
家庭伦理剧将婚恋内容紧密地与社会现实对接,侧重描写因家庭诸关系的情感纠葛、价值观碰撞而产生的戏剧冲突,聚焦于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注重以家庭成员的情感纠葛和命运变化,以及社会的人伦常理和人文关怀。观众对于这些带有浓厚生活情趣、体现自身生活本质的电视剧最容易产生共鸣。而且在欣赏剧本时会有一种同感的触动,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学习和影响。
以《渴望》为代表,上世纪90年代的家庭伦理剧探讨的是社会转型期间道德的缺失,呼唤心灵的纯净,向往建立一个更富有人情味的传统型社会。而现在的伦理剧更多的是关注代际之间、个体之间观念的冲突,试图展示现代都市青年人的家庭所面临的来自上一代的压力,以及自身个体独立意识和家庭需要相互妥协磨合产生的冲突,尝试着建立家庭和谐的另一种可能和途径。
3、经济利益——市场化炒作泛滥
经济效益也是最大的驱动因素之一。市场化炒作剧情的剧本已经在情感影视剧中泛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表示,“某些电视剧价值导向错误,社会影响低俗”,直批《蜗居》“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
三、家庭伦理剧热播产生的影响
麦克卢汉在《人的延伸》一书中强调,“电视不只是娱乐工具,还是制造现代人心灵、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大众传播具有文化或者社会建构功能,它通过“议程设置”和精心的编码建构一种现实之外的媒介世界,以改变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使得个人逐渐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③
来自为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一个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从数据上看接收TV Globo (主放拉美电视剧)信号地区的出生率比未接收信号的地区少0.6个百分点,普遍离婚率也较高。假如肥皂剧里的女主角离婚,那么当地的离婚率也会瞬间增长0.1个百分点。
近几年反映离婚问题的家庭伦理剧主要呈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痛苦失败婚姻的比例过高,而幸福恩爱家庭的比例偏少,这样传达给受众的就是现在社会婚姻家庭是痛苦。有专家表示,“这类影视剧用大量篇幅刻画第三者如何破坏家庭的过程,过度渲染家庭的脆弱,既不符合社会的现实,又影响了社会和谐与稳定”。中国国产剧中的家庭有很多像战场,夫妻间经常是对立的关系,结局也通常是离婚。
二是灌输婚姻就是“坟墓”的观念,将婚内生活表现得沉闷,缺乏生气,而将婚外恋写得有滋有味。《金婚》中的佟志与李天骄、《蜗居》中的宋思明与海藻,这几对婚外恋关系都写得缠绵而且富有人情味,这就在感觉上给受众一种误导:婚外恋比起婚内情似乎更符合人的本性,诱导着受众对婚外恋的同情和艳羡。
据统计,中国的电视剧观众的平均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都偏中下,这使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能力也相对偏低。《金婚》的导演郑晓龙认为,“一些情感剧的剧情表象属于社会问题,但现在荧屏上夸大、渲染一些社会不良现象,这样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有婚外恋是合理的,也使一些小众夸张为大众问题对成年观众的情感观念也会产生误导。”
更有人表示:“社会的婚姻观、道德观、价值观被扭曲、被颠覆。我们每个人所曾经坚守的东西,我们的底线,我们的是非和原则,越来越受到社会现实的严峻挑战!”
四、家庭伦理剧的责任
《继父》导演陈家林认为,“婚姻和家庭永远是这个社会的支柱和基本组成部分,家庭婚姻问题也是最贴近电视
观众,最朴实深刻的问题。”④
家庭是人性培育的最初场所,是社会转型的敏感之地。每个人都是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人的认知结构有很大部分是由家长的经验继承而来的,家教、家规、家风在人的道德素质形成上具有重要作用。⑤在中国,家庭伦理剧不仅要具有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还应在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当今社会现实、培养共同信仰和核心价值观以及提高审美层次方面的发挥重要作用。
1、满足受众需求,发挥粘合剂的作用,做受众“客厅里每天到访的一位睿智的健康的宽容的朋友”
受到群众好评的家庭伦理剧往往是建立在世俗和平基础上精神的同构与共生。”既能成功完成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形象塑造,又能挖掘出日常生活中的人情美、人性美。
相对于我国家庭伦理剧极力追求激烈的冲击,在理论观念上强调创作要表现正邪对立、正反相斗的斗争模式,韩国编导再现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人伦情感。它通过描写日常家庭琐事揭示人的内心,展示情感历程,宽慰人心,这类电视剧的内容“符合人们日常的心理节奏”。注重用和谐的家庭行式应对和化解社会的道德危机,注意从民俗和传统礼仪的强化来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抚慰处于现代社会压力下变得脆弱的人心,调节紧张的人与人之间关系。
2、用主流舆论引导非主流舆论,用正向舆论引导负向舆论
2004年10月中日韩三国电视剧导演聚首的一次研讨会上,韩国家庭伦理剧《看了又看》导演张斗翼表示,“老龄化、离婚问题等在三国都存在。离婚不能儿戏,我就是想用电视剧去影响社会风气”,“靠情化解矛盾,溶化冲突,维系家庭的和睦”。
用主流舆论引导非主流舆论。主流舆论是那些反映社会本质和时代前进方向,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舆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公平、民主、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舆论,是时代的主旋律。用这一主旋律的舆论引导非主流的舆论,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用正向的舆论引导负向的舆论。负向舆论歪曲客观事物的真相为了追求刺激、看点,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家庭伦理剧要反映客观、全面、本质的现实生活,以消融、统一负向的舆论。
3、强化中国特色民俗文化
家庭伦理剧的热播为传播民俗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但我国的家庭伦理剧生活细节缺乏,民俗的缺位,很少感受到中国特色文化。韩国将民俗点缀到电视剧内容的每一个角落,这项举措很值得我们借鉴。
在2006年3月14日的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网络新闻自由问题,温总理提出了爱尔兰作家肖伯纳那句格言:自由意味着责任。家庭伦理剧作为最现代的信息载体和最直接的触摸婚姻家庭的信息传播方式,便成了影响社会文化发展和个体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可以将对新型道德的思考融入叙事之中,以情感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立场,以大量鲜活的伦理生活信息引起人们的反思,积极建设新型伦理道德。
参考文献
①[美]威尔伯·施拉姆 著,戴鑫 译:《传媒的四种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士·坦卡德 著,郭振之等 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和应用》[M].华夏出版社,2000:310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14
④⑤吕乐平:《中国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的叙事艺术》[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81、65
(作者:均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