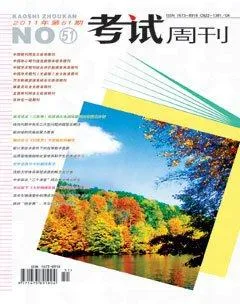语文课是可以“表演”的
2011-12-29王镇宝
考试周刊 2011年51期
摘 要: 语文课堂教学与说书有着许多共通性,将说书艺术引入语文课堂教学是可行的。语文课也是可以进行“表演”的,能够把学生带入语言的艺术殿堂,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习兴趣,熏陶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让学生在学习中娱乐,在娱乐中学习。
关键词: 语文课堂教学 艺术性 读书艺术
一
同样是对着书本“说书”,缘何说书人能够吸引那么多听客,而语文教师就不一定能够吸引那么多学生的注意力呢?说书艺术与语文教学有那么多相似点,在保证知识传授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条件下,是否可以将说书艺术引入语文课堂教学?语文课是否可以像成功的说书艺人那样进行“表演”吸引学生呢?本文主要探讨这些问题。
二
高中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了,语文教师的作用已经远远不是传授知识那么简单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领悟语言的艺术魅力。这一点,单靠知识点的讲解,侧重语言的工具性、思想性和人文性,很难让学生对语文产生兴趣,更难让学生发现语言的艺术魅力。这就需要语文教师首先把语文当作是一门艺术,一门可以令人回味无穷的“表演”艺术。语文教师完全可以将说书艺术引入语文课堂教学。
中国的说书艺术滥觞于唐,兴盛于宋,古时称之为“说话”。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说书人周围通常围着一群听书人,或站的、或蹲的、或坐的,聚精会神地听着段子。一段书说下来,每到精彩之处,人们便发出一阵喝彩和哄笑。姑且不论说书内容的准确性,仅凭它能够将一大群三教九流的人汇聚在一起认真听书的组织能力而言,就有着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书过程具有知识性(姑且不论知识的准确与否)和娱乐性,听客们不仅在听书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而且身心获得了极大的愉悦。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对着教材授课,与说书艺人对着话本说书有着许多相似性。语文课堂上,教师授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书,学生就是听客和看客。假如把语文课上得跟说书一样精彩,那么学生就会在学习中感到快乐,在快乐中学习知识,其教学效益将得到显著提高,学生对语文课就会有兴趣,语文学科的魅力也将大放异彩。当然,知识传授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是第一要务,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将语文课上得跟说书一样精彩动人。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目前《百家讲坛》中备受人们欢迎的各位专家学者身上获得启发。由于自身水平及职业道德素质等各类因素的影响,并非各位专家或学者们所讲的内容都是真理,有些人误解或者故意曲解了文化经典,难免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我们暂且撇开易中天“品《三国》”、于丹 “《论语》心得”等节目内容的科学性不论,他们能够将大江南北的老少妇孺鼓动起来,去观看的他们的节目,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或者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无论是易中天的“品《三国》”,还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它们都与古代的说书艺术有极大的相似性,道具也很简单:一个话本,一张桌子,一个主讲,若干听众或者看众(从某种意义上讲,准确地说是看众,因为听者们不仅听书,还观看说书人的表演)。教师授课的道具也大致如此,若干教材,一个讲台,若干学生。易中天、于丹等可以说是现代版的说书艺人,从激发看客观看节目的兴趣角度来看,他们无疑是成功的。语文教师完全可以向他们学习,取其所长为己所用。
当然,即使是说书艺术,也是有水平高低之分的。我们大致可把说书艺术分为三种状态:一是案头状态;二是导演状态;三是表演状态。语文教师的授课,也可以用这三种状态来形容。
案头状态主要指的是说书人根据话本如实照搬地进行说书,相对应的就是语文教师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没有自己的主见,只会根据教材教参教辅授课,缺乏活力与激情,这类教师很难受学生的喜欢,教学效果也比较差。
导演状态就是说书人能因地制宜,对话本进行创作,根据听客的反应不断调整方案,相对应的就是教师能够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反应,适时地改变教学设计。这类教师能够比较受学生的欢迎,教学效果也相对比较好,但仍然很难把学生带入语言艺术的殿堂,让学生热爱语文。因为这不是在引导学生欣赏语文,而是让学生按照教师的教学计划不停地去完成教师事先所布置的任务。教学目标是完成了,但语言的艺术魅力却淡化了;这是在解析语言,而不是在欣赏语言。久而久之,学生会误以为语文教学无非就是教师讲解教材、提问、学生回答问题、教师布置作业、学生按时完成作业等这一简单的流程,对语文产生厌烦。
第三种状态是最高境界,表演状态指的是说书人不仅讲述了话本内容,而且有所发挥,同时在说书过程中还掺和了艺术表演,相对应的就是教师在授课中,不仅讲解教材,而且对教材有自己的见解,授课时还能运用肢体语言,授课犹如表演艺术一般。如此,教师在授课中既能展现个人魅力,同时又能够对学生产生艺术感染,将学生带入艺术殿堂。
从易中天、于丹等人的成功经验来看,也是由于他们善于“表演”。下面列举易中天“品《三国》”的部分片段,我们可以从中见出端倪。
易中天的“品《三国》”,继承并发扬了说书艺人语言幽默的风格。在易中天的“品《三国》”中,引起人们哄笑和喝彩的妙语比比皆是。比如,“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关羽和张飞,对刘备则名为事之如兄,实际事之如君。可见维系三人友谊的,就是英雄之义。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三个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这个时候的曹操因为刚刚出道,二十岁还不太懂得官场,是个生瓜蛋子。以为他当了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就怎么了不起了,他放出话来:谁敢违令,格杀勿论,结果蹇图这个大尾巴狼撞上来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只好硬着头皮把他打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选自《易中天品〈三国〉之〈 乱舞春秋〉》)。
在上述所引用的片段里面,易中天声情并茂地用现代的语言(甚至使用口语)去解读古代的语言,同时还比手画脚地配合着肢体语言。撇开其对历史解读方法的科学性不论,他语言风格所体现的出来的幽默及他肢体语言的合理运用,足以令人捧腹,恰恰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这并非没有先例,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早已成功地为我们做了示范。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中提到了梁启超先生演讲时的情况。梁实秋在文中说,梁启超在讲《桃花扇》时“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在讲杜诗时“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他背诵忽然记不起下文时,“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演讲到紧张时“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这里所说的演讲,就其所讲的内容而言,本质上就是一次成功的授课,是一出臻至完美的艺术表演,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梁实秋回忆说:“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语文教师最大成功之处就是让学生喜欢上语文学科。
三
其实,语文教师的作用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而且在于艺术涵养的熏陶与引导,只有做到了“表演”语文课,才能让学生感受到语言艺术的魅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知识的传承毕竟是有限的,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最多二十几年,每个阶段都接触不同的语文教师,而在有限的时间里教师也很难把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再说,如果仅仅是知识点的掌握而已,学生现在不懂,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都不懂,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学习,他们将来也可以通过自学的方式弄清楚,毕竟高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学能力。但语言的艺术魅力,却往往不是学生自身独自一人可以领悟到的,这就需要语文教师通过语文课的“表演”来熏陶他们。现代社会注重的是终身学习,假如学生在校期间都不喜欢语文,他们进入社会后就更不可能去学习语文了。
学生一生当中会遇到许多语文老师,每个语文老师都曾经传授他不少的知识,但他却不一定会都记住。那个能令他牢牢记住的语文老师,对他的影响往往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而已,而更多的是人格魅力的影响,个人语言艺术涵养的影响,等等,以至于在他今后人生的生活、工作语言表达中,那位语文老师的语言风格若隐若现。
许多高中生不喜欢语文,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觉得语文教学模式过于简单,基本上是教师讲解教材、提问、学生回答问题、教师布置作业、学生按时完成作业等单一模式。许多刚升入高中的学生刚开始挺喜欢语文学科,但到后来渐渐地兴趣减弱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因为他们原本期待着高中语文教学模式有了新的改变和突破,至少不应当是他们所熟悉的初中的教学模式。假如这一状态得不到改变,学生的期待值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就会对语文学科丧失兴趣,甚至是产生厌烦情绪。从小学教育甚至是从幼儿教育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许多学生接触的基本上是几无二致的授课模式,他们会认为语文教学不过如此,语文学科亦不过如此。
四
语文作为一门语言学科,除具有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外,还具有艺术性。忽视了这一点,语文学科就丧失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语文教学与说书艺术有着许多的共通性,将说书艺术适当地引入语文教学,可以让学生感觉到语言的魅力,发现原来语言也可以像其他艺术品一样拿来不断地鉴赏,在教学中感到身心娱乐,在娱乐中学到知识,进而极大地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语言素养。
同样是面对几本书籍,同样是对照书本的内容进行讲解,假如语文教师能够做到韩愈所说的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为伍,积极向说书艺人学习,在保证知识传授的科学性与准确性的前提下,将说书艺术引入语文课堂教学,“表演”语文课,那么语文课堂上出现“哄笑”和“喝彩”的活跃氛围将不再是梦想,学生也会像听书人那样聚精会神地听课,学生不喜欢语文的局面将得到彻底的改观。
只要语文教师适时地“表演”一下语文课,相信学生们就会像梁实秋记住梁启超那样牢记语文老师,学生们也会“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