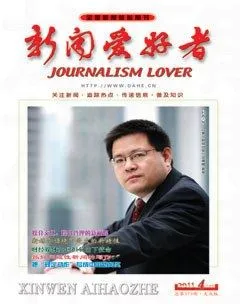晚唐古文家孙樵对文体的创新
2011-12-29丁恩全
新闻爱好者 2011年7期
文体的革新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成果,对此研究者有充分的论述。刘国盈说:“所谓古文运动,简单地说,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的一种变骈为散的文体改革运动。”①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首先辨析“古文”一词的含义,也明确指出古文是与骈文相对的新文体。②孙樵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殿军,对古代散文体裁的革新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前人对此有零星论述,如陶喻之就认为《兴元新路记》是一篇议政杂文。所以,孙樵对散文体裁的开拓实有深谈之必要。
孙樵,字可之,一字隐之,唐宣宗大中九年进士,曾任职方郎中,和李潼、司空图一起,号称“行在三绝”,晚唐著名古文家。孙樵对散文体裁的创新,体现在记文、祭文、赋等体裁方面。
孙樵古文体裁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对“记”体文的创新上,《书褒城驿壁》和《兴元新路记》是代表。
《文章辨体序说》:“《金石例》云:‘记者,叙事之文也。’西山曰:‘记以善叙事为主。《禹贡》、《顾命》,乃记之祖。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议论。’后山亦曰:‘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窃尝考之:记之名,《戴记》、《学记》等篇;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议论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做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范文正公之记《严祠》、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③这段话论述了“记”体文的发端、特点,以及“记”体文在唐宋之间的发展演变。虽然“记”体文的发端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但对于“记”体文的特点及其演变则论述极其精当。“记”体文以叙事为主,到宋代以议论为主。《兴元新路记》虽然叙述了主持修路的官员、修路的过程、路途的详细情况,尤其是路途状况,占了全文四分之三以上。但孙樵叙述路途状况主要是为了说明兴元新路和褒斜旧道的优劣,写主持修路的官员和修路的过程,是为了突出荥阳公郑涯的“济民于艰难”,批判以贾昭为首的官吏不能尽心于公事。这样,孙樵的主要目的——为荥阳公郑涯鸣不平,破除“道路”的“唧唧之叹”和“朝廷”的“窃窃之议”就达到了。所以,不仅文末有大段议论,而且在路况叙述过程中亦杂出议论,文章详细地记录了兴元新路每一段的情况,不时发表自己的看法,点明新路的优缺点,而且明白地说明新路不足的原因在于“都将贾昭争功”,“苟使贾昭尽心于荥阳公”,则新路胜于褒斜旧道。也就是说,文章形式上是叙事为主,但精神上却是议论为主。这种写法,既不是“记”体文的正体,也不是宋代纯以议论为主的变体,而是处于正体向变体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而《书褒城驿壁》则一反常规,不叙述褒城驿的兴建过程,而是叙述褒城驿由繁盛到破败的过程。孙樵借驿吏之口说出褒城驿的破败原因,宾客没有“顾惜心”,“棹舟则必折篙破舷碎鹢而后止,渔钓则必枯泉汩泥尽鱼而后止,至有饲马于轩,宿隼于堂”,工作人员即使有心修理,也赶不上破败的速度,所以渐趋芜残。接着用老甿的话深化主题:“今朝廷既已轻任刺史、县令,而又促数于更易,……故州县之政,苟有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县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乎?”褒城驿的遭遇反映了管理的弊端,州县官对州县管理的弊端也是如此。刺史、县令因为“促数于更易”,就像宾客一样,对待州县的治理也是毫无“顾惜心”。因此国家也日趋破败,对话之间,寓以深忧。和《兴元新路记》相比,写法不同,《兴元新路记》虽然精神上是议论的,但仍以叙事的手法为主,这篇文章却是以驿吏和老甿的议论作为主体的。从这方面来说却完全是宋调了。
杨庆存认为宋代记体散文和唐代相比有“立意高远”的特点,亭台堂阁记变唐人“以物为主”为“以人为主,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其中”,④山水游记变唐人“单纯的自然审美型”为“兼重议论说理的复合型”,提高了游记散文的“信息容纳量和社会教化功能”。⑤孙樵的《书褒城驿壁》和《兴元新路记》就是将强烈的主观意识纳入记体文的写作之中,突出了社会批判意义。孙昌武盛赞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是一篇含义深刻的讽刺文,在写法上和内容上都很独特”,⑥这篇文章突破了记体文“备不忘”的写作要求,但其对县丞地位的尴尬和崔斯立怀才不遇的同情,还是采取了记叙的手法。
孙樵对文体的创新,还体现在《祭梓潼神君文》对祭文的变革上。按《文章辨体序说》的看法,祭文的演变如下:“古者祀享,史有册祝,载其所祀之意,考之经可见。若《文选》所载,谢惠莲之《祭古冢》、王僧达之《祭颜延年》,则亦不过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后韩、柳、欧、苏,与夫宋世道学诸君子,或因水旱而祷于神,或因丧葬而祭亲旧,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诚学者所当取法者也。大抵祷神以悔过迁善为主,祭故旧以道达情意为尚。若夫谀辞巧语,虚文蔓说,固弗足以动神,而亦君子所厌恶也。”⑦则六朝祭文之正规写法,是“叙其所祭”和“悼惜之情”,到唐宋而改变为“或因水旱而祷于神,或因丧葬而祭亲旧”,对象改变为神或亲旧,“祷神以悔过迁善为主,祭故旧以道达情意为尚”,所表之情也由“悼惜”而变为“悔过迁善”、“道达情意”。梓潼神君即张恶子。汪师韩注:“宋孙光宪著《北梦琐言》,梓潼县张恶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嶲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立祠,时人谓为张恶子,其神甚灵。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张恶子庙即梓潼庙,梓潼县北八里七曲山。按《图志》,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嶲人也,因报母仇,遂陷县邑,徙居是山。……又按英显王庙在剑州,即梓潼,神张亚子仕晋战没,人为立庙,唐元宗西狩,追命佐丞。僖宗入蜀,封济顺王。”此文因是祭神,按常规写法,应是“悔过迁善”。此文虽然是“悔过迁善”:“樵实顽民,不知鬼神,凡过祠宇,不笑即唾,今于张君信有灵云。”但孙樵却写了两件十分怪诞的事情,会昌五年和大中四年,梓潼神君两次显灵,帮助孙樵渡过难关,读之如志怪小说,所以汪师韩评之为:“此记事为祭文,然近小说家语。”⑧实为祭文中之趣闻。
另对赋体的创新,体现在《大明宫赋》和《露台遗基赋》中。曹明纲《赋学概论》说:“文赋是赋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于唐宋时期才形成的一种新类型。它在吸取以往辞赋、骈赋和律赋创作经验和形体特点的基础上,更融入了当时古文创作讲求实效、灵活多变的特色,从而在形体方面形成了韵散配合、骈散兼施、用韵宽泛和结构灵活的新格局。它的篇幅长短皆宜,句式骈散多变,创作不拘一格,题材无往不适,用途宽广无碍,是以前任何一种形式的赋体所不能同时具备的。”⑨《大明宫赋》和《露台遗基赋》的讽喻作用、结构灵活、多用议论都体现了文赋的特点。《大明宫赋》借大明宫神大发议论:“籍民其雕(应作‘凋’),有野而蒿;籍甲其虚,有垒而墟;西垣何缩,疋马不牧;北垣何蹙,孤垒不粒。”自己却正话反说:“今者日白风清,忠简盈庭,阖南俟霈,阖北俟霁,矧帝城阗阗,何赖穷边!帑廪如封,何赖疲农!禁甲饱狞,尚何用天下兵!”最后又用神的话推翻自己的正话反说,肯定神自己说的话:“孙樵,谁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形式之灵活、议论之深刻、讽刺之突出都与文赋一致。《露台遗基赋》也是如此。文章主题就是中间大段议论:“惟昔汉文,为天下君,守以恭默,民无怨慝,天下大同,……朕以凉德,君子万国,唯日兢兢,如蹈春冰,高祖惠宗,肇启我邦,作此宫室,庶几无逸。逮夫朕躬,孰敢加隆?矧麋府财以经此台。周为灵台,成乎子来,文王以升,以考休征,兹台以平,周德惟馨。章华虽高,楚民亦劳,灵王宣骄,诸侯不朝,民既携二,王遂以死。岂朕不惩,斯役实兴,鸠材啸工,以害三农,斯岂文王灵台之旨哉?”虽然都采用了问答体,都主要使用了四字句,但两篇赋的感情表达却又不同。《大明宫赋》是愤慨,《露台遗基赋》是无奈。
孙樵要求写文章必须“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推崇“玉川子《月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鞚骑生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的艺术境界,他对文体的创新也恰恰体现了他“储思必深”、“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的艺术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就。[本文为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晚唐古文家孙樵研究》(2010FWX02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释:
①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②⑥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第146页。
③⑦吴纳:《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第54页。
④⑤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第196页。
⑧汪师韩:《丛睦汪氏遗书·孙文志疑》,《光绪丙戌秋八月钱塘汪氏刊刻于湖南长沙》,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⑨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