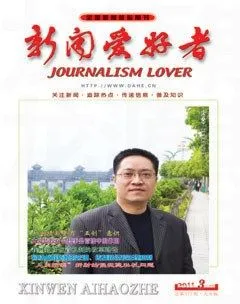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反思
2011-12-29刘加昆孙燕
新闻爱好者 2011年5期
2010年上半年,有媒体报道,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黄山正在发起西门庆的故里之争。阳谷县将建设“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项目,临清县提出打造“西门庆旅游项目”,黄山将西门庆定义为“徽商代表”,并声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西门庆居然被抢,然而无论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西门庆都是恶霸、奸商、色魔的代名词,作为文学形象,西门庆是世态炎凉的讽喻符号。开发以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项目,首先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作为儒家礼乐文化的深刻文化价值观念,不能饥不择食、寒不择衣。其次,在挖掘旅游文化资源方面,不能生拉硬拽,有人就用,管他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教材,只要是“名人”就“大胆”取用,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总比没有好。最后,面对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竞争是必要的,通过挖掘名人,打造品牌,达到在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是有其可取的地方,然而类似这样的“攀龙附凤”,想打名人这张牌,最终打到“西门庆”这里,则正好反映出当代中国在文化创造力方面的严重不足。
一方面,现有的文化创造力无法让一个地方名闻遐迩,则只能靠着过去仅有的这点历史符号,“只能转身向历史要,向传统要”,这种等、靠、要思想极不利于当代文化创新。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已经无法像孙冉翁那样能够创造天下第一长联使得昆明大观楼声名鹊起,也无法像柳宗元书就《永州八记》让湖南永州在人们的心目中留有一席之地,更无法像王勃一言九鼎,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让江西滕王阁几乎一夜成名,至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着岳阳楼的格调更是高情千古。
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参与挖掘古代名人及其事迹,以及发起名人故里之争等,反映了全国各地文化创造力的普遍缺失。仅以江苏省苏北地区而言,连云港打“西游记孙悟空牌”、宿迁打“项羽牌”、沭阳打“虞姬牌”、沛县打“刘邦牌”,徐州联合宿迁等地共同打造楚汉“西楚雄风”文化,而且这些地区多数是以列举的这些“牌”作为文化发展的主心骨。至于湖南双峰和湘潭展开的徐静蕾原籍之争,则为当代中国文化创造力提升敲响了警钟。现如今,仅在影视娱乐文化产业方面,就表现为名著、名剧改编翻拍,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上海滩》等;电视节目如法炮制,如选秀比赛、电视征婚、体育竞技节目等各地雷同。很多地方在文化产业建设方面的思路其实也是“跟风”,看着别的地方这么干,我们也这么干。为此,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做到大胆创新、科学创造就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大繁荣的战略问题和技术攻坚问题。
那么,当代中国在文化创造力方面的不足根源何在?
笔者认为,归根结底在于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动力,过分追求文化功利性的文化发展趋向及“量”文化的发展模式。而这直接导致了个性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及文化产品缺失,精英文化创造力不足,文化产品生产的“传送带”模式非常突出等问题。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完全进驻文化生产领域,成为阻碍文化创新乃至创造的重要因素。
首先,以市场为导向,决定着文化资源产品化、文化产品研发的方向,决定着艺术家、作家等文化生产者应该制作什么样的文化成果,该走什么样的商业路线等,而这些所依照的就是大众的口味和市场的需求。由此,检验一部文化作品、文化产品是不是好的产品,就仰仗于是否会带来好的市场收益、是否符合大众的需求,而这样会导致很多文化产品倾向于走平民大众化路线,而不愿意生产只为少数人才能理解、消费受众少的具有创新性、不可重复性的精英文化产品,否则,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其市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不明显,回报率少,那谁还会再生产呢?因此,精英文化产品的创造力不足在所难免。如果说大众文化产品反映着文化创造力的横向广度,那么精英文化产品则昭示着文化创造力的纵向深度。“纯文学”的命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纯文学”走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步履蹒跚”、“苟延残喘”的局面,很多纯文学刊物办不下去,举步维艰,如履薄冰,而“纯文学”的文学文艺作品,往往直接被个体生产者所创造生产,是创作者思想情感的自我流露,崇尚个性,追求创新,具有原汁原味的原创性,对于市场需求和接受者的口味不太注重,因此,它们“不识时务”,不被主流形态所“收编”,只能落得流离失所,无“价”可归,作为“纯文学”刊物的主办者,面对无“价”可归、无利可回,因此只好永远地“合上了书本”。为此,以市场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个性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及文化产品的缺失。然而事实上,文化产业范畴里的文化产品,必须面向市场,否则文化不可能成为产业。但反过来,文化产业到底是关于“文化”的产业,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其所作的许多“曲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按文化的内在“音符”和“市场的旋律”谱写的。总之,文化的这种“穿透力”,不仅仅是入“市”三分,也还得要“力透纸背”才行。
其次,近几年来,由于文化本身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地区发展差距依旧是各地政府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动力导致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功利性和盲目性倾向。为此,有专家提出,要谨防文化患上GDP崇拜症。从另一个侧面看,名人故里之争,本质上是资源之争,是文化资源争夺战。现在,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庞大资源支配能力的经济综合体,利益驱动下的资源经济博弈迫使其不断行使对资源的寻觅和支配管理,因此追求文化的功利性,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瞄着灶台,对西门庆的“宠爱有加”也没有什么不可能,表现在经济学中,这种有利可图,必然会迫使生产者加大生产从而提高产量,表现在现实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就是文化发展的功利性和盲目性。这也许就是“改革家的急躁”。所谓文化发展的“盲目性”,是由文化发展的现实条件的不足和文化发展的过度功利性倾向矛盾引起的。就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当前在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西南边疆地区,文化发展仅处于一个文化培育和起步发展阶段,形成产业,尚不具备。很多文化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科技文化成果转化率低,并不具备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和独立的产品研发能力,很多都以提供初级产品为主,生产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然而,为了眼下的实际需要和挤占市场份额,他们以GDP的数字为目标,以利润为动力,“开足了马力”,结果过分追求文化的功利性而导致了生产的盲目性,正所谓欲速则不达,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原创动力不足,创新性不强,质量不高,因此很难出文化精品,而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文化的原创动力不足的原因。
再次,在“传送带”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直接发展了文化产品生产的“传送带”模式:文化产品生产的程式化、规范化和批量化。也即文化产品通过工厂式生产组织用标准化手段大批量地生产出来,目标直指市场,其“经济上的策略,比其他考虑更为重要”。事实上,文化产品的程式是结构意义上的“类推”机制,而所谓“类推”即保守与革新的原则,是巩固成果,保持稳定,延缓和抑制创新的原则。工厂里面的“传送带”,在传输成品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其所传送的产品在高度、宽度、体积、重量方面基本一致,因此,老调重弹的层出不穷不足为怪,这也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另外,采取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主体是生产组织,如电影业的好莱坞,唱片业的华纳、索尼、宝丽金等巨头。在工厂式生产组织里面,生产方面的创造性人才不再是组织的核心,对市场反应敏锐的经营者才是真正的掌控者和幕后操纵者,如影视制作领域的导演核心地位的丧失和制片人的总揽大权,音乐制作领域的经纪人地位的上升等。文化产品研发中心研发的产品,其创意再好,也不如销售得好、市场反应好,所以销售部门才是工厂的核心。如此一来,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创造性人才严重不足。而文化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在大力培育一批本土化人才的同时积极吸纳和引进一批外来文化专家和学者,做到思想大碰撞,形成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局面,这对于提高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十分有利。当前,一些文化机构和文化部门管理主体缺失,长期以来是以政治家或官员来负责,他们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干脆就好比一个学术机构官员,一般不做什么学术研究,即使要做研究也是考虑到又有什么项目了,又可以申请并拨付多少资金了。对此,如何对下辖文化企业和文化单位给予实质性政策引导?如何给予其创新性指导?如何保证文化发展的质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几年,江苏省提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人才共同发展的三强战略,这可以成为我们的良好借鉴。
最后,由于对文化功利性的刚性需求,因而在发掘文化资源,并用现代创意整合文化资源的时候,没有坚持科学的尺度。也即在发掘文化资源时生拉硬拽,没有做到准确判断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没有很好地用现代创意整合文化资源,没有很好地将现代理念和情感内容注入到文化资源中去,因此要么创“过”了,要么就是创不足。争夺西门庆,我们认为是创过了,它已经超出了社会普遍道德意识形态的底线,尽管它具备了市场的眼光。因此有专家指出,西门庆“受宠”是在拷问社会道德。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文化产品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的,但这种创新并没有照顾到文化本身所蕴涵的内容本质,而只是考虑到它能带来的商业价值,因而这种创新是不合时宜的。从根本而言,用现代商业机制支撑的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是存在很多问题的,需要不断规范和完善。
总之,针对目前的现状,我们必须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不足的原因何在、应该如何突破提升。一方面要反思:在文化产业建设中,文化的地位应当如何摆正?没有文化,哪来的文化产业?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如何按照文化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来发展文化?如何做好对文化资源内涵的挖掘?如何实施对零散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对现有公认文化资源的打造,以及区域性大文化圈内的协调?如何处理好文化发展与社会普遍道德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做到发展文化产业和发展文化事业齐头并进?如何处理好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还要反思: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所处的背景和阶段,在此背景和阶段下如何提高文化的原创动力?如何发展创意文化?立足文化如何理解“创新”的含义?难道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1990)中所说的“创新”,就是指任何一种做事情的不同方式,只要它能够提高一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就是一种创新,还是不仅如此?还有,如何为文化创新铸就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外部环境?如何建设培养具备创新性和创造力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文化产业建设和繁荣需要达到或配备什么样的文化创新机制等。
在我国,长期以来文化处于经济的附庸地位,但不管怎样,经济发展的最后必须要上升到文化,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的地区,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地区,一个地区如果不注重挖掘和培育地方民族文化及其创新因子,则无异于自甘堕落。而发展培育文化的创新因子,必须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身规律,必须依照文化产业生命运动的内在逻辑,做到文化资源的合理延伸,科学整合科学发展,否则就是没有坚持科学的尺度。
最后,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耐以生存的源泉,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乃至最后繁荣的不竭动力,文化创造力是落实在文化上的一组发生的意义或将要发生的意义,与其说文化创造力的大小或足与不足,不如说是文化发生意义的深远与否,其实更多的是与子孙后代有关。
(刘加昆为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语言学教研室教师兼学院教学秘书,讲师;孙燕为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党委书记兼玉溪市委宣传部特约新闻阅评员)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