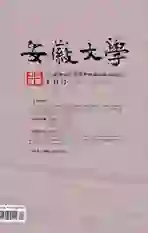宋姐酸菜鱼
2011-12-29谢燎原
安徽文学 2011年1期
女人从楼梯上下来了。
这个时候,为为的眼睛已经适应了这个小饭店里面的光线。她看到了一双穿着黑色的纤细高跟鞋的脚。女人下楼的步子很慢,那是一种笃定。那脚分明是很熟悉这楼梯的,一探一探的脚尖并不是在探路,而是如同一对自信的黑鸽子般,徐缓地,一层一层地栖息在自家的狭小的木楼梯上。跟着下来的是腿。女人的腿是修长的,旗袍裙的衩恰巧开到了膝盖上面,丝袜里的小腿线条优美,大腿在黑的旗袍裙的庄重的裹挟里,也是仪态万方。为为想,这样的腿该是承载着什么样的身材面容、怎样的肤色的女人呢?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在如此狭小逼仄的楼梯上,走出豪宅别墅宽大的楼梯上才能走出的步态呢?
店铺太小了。狭长的一条,一个过道似的。上面是阁楼,窄窄的木楼梯已经脱了色,女人大约就住阁楼上。后面是厨房,为为侧着头看了一下,使用面积最多一两个平米,只能容纳一个人在里面操作。
此刻店铺还没有开张。小吃一条街上的排档,一般都是下午才开张的。
店铺的墙上也没有什么装饰,两面墙上各有一个镜框,挂着两幅画,只有黑白两色,白纸黑墨画,两幅画画的都是一个椭圆的盘子里卧着一条鱼。为为看有点像儿童简笔画,又像考古展览上的古代壁画,稀疏的几笔,质朴拙笨,只有鱼的眼睛,倒是有神的,躺在千年万年的盘子里,死死盯着外面的世界,一副什么也不想告诉你的神态。为为原以为是画在宣纸上的画,要么是买的装饰画,走近一看,才看出来是十字绣。不用说,是女人的手工了。为为嗅了嗅鼻子,店铺里也没有那种烟熏缭绕的酸菜鱼散发出的既酸且麻又辣的味道。
女人终于下来了,站在为为面前。她定睛看了看为为,嘴角轻轻地扬了起来,算是微笑着招呼了为为。为为也看清女人了,猜测了几分钟的神秘女人,此刻就站在自己面前,不年轻,不惊艳,不咄咄逼人,只是很有分寸地对自己微笑着。不温不火,不远不近。
为为看见,女人穿着一条已经落伍,却又永不过时的黑色旗袍裙,浅圆领的米色针织上衣。头发梳成一个光滑的圆髻,流年已逝地盘在后脑勺,像是一位从荧屏上走下来的昔日闺秀。这个发型让女人的神秘在为为面前又添加几分。女人指着一旁的一个木椅子,让为为坐下。
看女人安静的微笑,为为想到自己宿舍里的同学,每天晚上大家回宿舍洗漱好了以后,就是宿舍同学的聊天时间,聊着聊着,大家就放声大笑起来,就笑得死去活来,笑得抱着被子在床上打滚,笑出了眼泪,笑得肚子疼。那个笑,如果算十分的话,这个女人的笑,应当定格在三分到四分之间。
店铺里只有四张桌子,和别的排档的简易的桌子还不一样,女人店铺里的四张桌子都是髹着枣红色漆的课桌,或许比一般学校里的课桌大一点,每个桌子有两个空抽。椅子也是髹着枣红色的木制的靠背椅子。为为想,这样的桌子若是再多几个,这家排档就像教室了。
女人坐在为为的侧面,两只胳臂搭在桌子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扣着,侧过脸来,问为为的名字是哪一个为。为为说是因为的为。女人说,你父母给你起了这个为?不俗,想必是让你有所作为吧,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般人家女孩子可能就叫葳蕤的葳,或者叫蔷薇的薇了。
为为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无法给她的年龄定位。有着苹果般的脸才二十出头的为为,不太会分辨三十岁以上女人的年龄。眼前这个女人或许比自己的母亲小,也或许比自己的母亲大。女人算不得漂亮,却也看不出哪里难看,皮肤不太白,但没有什么皱纹。为为不能确定这个排档的老板娘有一种什么样的气质,总之,为为觉得女人和这一条小吃街的其他老板不一样。于是,她心里有了一肚子的好奇,和一肚子想说的话,想晚上回到宿舍一定要和同宿舍的同学说说,或者,应当让同学来看看这个女人再说。为为宿舍的几个同学,每天晚上熄灯以后都要海侃一个小时的。
想到女人的小餐馆来打工的为为,这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眼前这个女人了。她看这店铺的样子就像只有女人一个人,连端盘子的服务员也没有看到。门口的招牌上写的是“宋姐酸菜鱼”。为为想,也许应该称呼她宋老板吧。
宋老板……为为说。女人立刻打断了为为,用手指了指门口的招牌,就喊我宋姐吧。为为看着眼前的女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为为不知道为什么是自己不好意思。
宋姐……为为说。女人又打断了为为,我这店里只有我一个人,生意嘛,你也看到了。
为为不明白,这条小吃一条街上,怎么会有女人的这家店。
为为所在的大学离这里不远,小吃一条街的大部分顾客都是附近几所学校的学生,或者说,这些排档,就是冲着学生来的。为为想在课余时间在这里找一家店铺打工,便到这条街来转了几次。夜晚来临的时候,这小吃一条街上几乎所有的店家都是油烟和人气一样旺。夏天里许多店家都把桌子搬到了门外,简易的餐桌边,围坐满了吃油炸串、吃米线、吃炒饭、吃捞面、吃龙虾的年轻人。所有的店家门口都有一两个女人,穿着彩色的劣质的塑料拖鞋,坐在一个大塑料盆子面前,洗着流水般送过来的脏碗。盆子里的洗洁精泡沫先还如同一座堆起的小山,洗着洗着,小山就没有了,水也黑得像沟里的水,洗碗的女人便就地一倒,水就漫到她们自己的脚上。
洗碗的女人都是坐在塑料小板凳上,多半是穿着花绵绸衣裤,身体大幅度前倾,那姿势有点奋不顾身的味道。她们就那样程序化地洗着排档里源源不断地送来的碗,直到倒掉的洗碗水漫到脚上,这才感觉到自己的脚有点麻,看一下自己的一双脚,早游离到塑料拖鞋外面来了,只是踩在塑料拖鞋的鞋帮上,自己一点也不知道。
为为走完了这一条街,没有看到一家中意的铺面,却不甘心地踅了回来。
她趿着凉拖鞋,终于走到了一块干地方,她前后看看,很少有铺面门口不是湿的。而这家店在这条街上真算是有点冷清了,铺面的招牌和任何一家都不一样,敦敦的魏体书法,宋姐酸菜鱼,五个字白底黑字,不卑不亢,不暖不凉。为为原以为是宣纸上写的字装裱了一下,后来才知道是女人自己绣的十字绣。
为为抬头看着这一条街,每一家铺面的招牌都是五颜六色的彩灯,从下午开始,就在那里一闪一闪的,挤眉弄眼,卖力地喧哗着,胖子怪味龙虾,回头米线,私房小吃,正宗李氏手擀面,韩式烧烤,等等。
那天,宋姐酸菜鱼这家排档只有一个客人,正在边喝酒边吃火锅。为为走到门口,问道,老板在吗?后堂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吃饭吗?几位?为为对着声音传出的方向说,对不起,老板,我想问问你这里需要人手吗?略略停了一下,女人在后堂说道,我在忙,过两天你再来吧。
女人告诉为为,自己这个小酸菜鱼馆的生意不像其他排档那么忙,客人少,做酸菜鱼的草鱼和一些时令蔬菜,每天都有人送来。烧酸菜鱼的红尖辣椒是自己泡的,酸菜也是自己泡的,都在厨房的坛子里。做酸菜鱼的时候,捞一点出来就行了。
为为不知对女人说什么好,低头抠着指甲,想了想说,宋姐,我回去让我的同学到你这里来,吃你做的酸菜鱼,到时候你少放辣椒,也让你的生意好一点。女人对为为笑笑说,好啊,你的同学来了,我烧一锅另一种口味的酸菜鱼,给你们尝尝。
为为到女人这里来打工后才知道,女人这个酸菜鱼小饭店从来没有请过第二个人,为为是第一个。每天晚上只有零星的几个顾客,女人完全能应付过来。下班回到宿舍,洗漱好了以后,躺在自己床上,为为把这个小饭店女人的情况,告诉给了宿舍的同学。宿舍同学的八卦话题,就立刻从远在天边的影视明星,转到为为的老板身上了。有一个同学想了一会儿,说,这个女人一定是不缺钱。另一个同学说,不缺钱为何不在家做全职太太?还到小吃一条街来开排档呢?经营一个饭店到底是不容易的,我知道的,我舅舅家就是开饭店的。
以后,为为每天晚上来到店铺里,也就是端端菜,擦擦桌子,打烊前,才把水槽里不多的碗洗掉,然后整理收拾一下厨房。有客人要啤酒饮料什么的,宋姐就打发为为到不远处的小店去买。为为看见女人下厨的时候,都是那一身衣服,没有见她把衣服换掉再下厨。
这一天为为下班后回到宿舍,也不等洗漱完毕,就睡到床上,迫不及待地告诉同学:哎,跟你们说,我的这个老板真是和别人不一样哎,你看她在厨房里忙的时候,仍然是穿着那一身衣服,脚上也是那双高跟鞋,像是出门做客的打扮,只是头上包着一个帕子,身上围了一条围裙。是吗?宿舍同学听为为这么说,也觉得有点奇怪。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为为好,过了一会儿,一个同学笑笑说,呵,你这位老板还是一位老小资啊,唯美主义,在那么个油烟的环境里还穿着这么一身衣服。
于是,大家又好奇地嘻嘻哈哈议论半天,宿舍熄灯前的一场哄笑之后,宿舍同学对为为说,为为,现在我们给你布置今后的任务,那就是,打听到这个宋姐的丈夫和孩子,或者说,打听到宋姐的婚姻情况。
为为每天晚上带着同学布置的这个任务,去“宋姐酸菜鱼”打工,却多少天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她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女人的丈夫或孩子到小饭店里来,也没有听到女人说起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女人在为为的眼里虽然有点神秘,但为为觉得,女人还不是那种矜持到高深莫测的女人,通常,她还是愿意和为为聊聊的。在没有顾客来的时候,女人就洗了手,从一个塑料袋里取出十字绣来绣,然后一边和为为说着话。
为为想,这个宋姐要是有孩子,那孩子该有多大呢?宿舍的同学说,那你得先搞清楚宋姐多大。为为摇了摇头,说我真是看不出来她有多大。想了一想又说,要不哪一天你们假装找我,到小饭店去一次,你们看看她到底有多大。我曾和她说过,让你们来她的酸菜鱼小饭店,就算是照顾她的生意。
两个星期了,宿舍同学布置给为为的任务,她还是没有完成,宿舍的几个同学有点着急了,于是就商量着去小饭店吃饭。在这一天傍晚,结伴来到女人的小饭店里。
女人在厨房里正指导为为切酸菜,为为看见同学来了,对女人说自己的同学来了,女人就转过身来。呵,来啦!是为为的同学?为为早说了,让大家来吃饭照顾我的生意。女人说着,就让为为招呼同学,自己系上围裙,为为为的这几个同学做起了酸菜鱼。
为为的几个叽叽嘎嘎喜欢八卦的宿舍同学,带着一肚子好奇,聒噪着,来到女人的小饭店,见到女人,竟然都噤了声,没有一点声音了。她们观察着女人的举动,看见女人今天穿的是一件乳白色棉麻衬衣,下面配的是一条蓝花布直筒裙,裙子显然是熨烫过的,不然,棉布的料子怎么会那么挺括,脚上果然是穿着一双黑色浅口高跟鞋。为为的同学看见,女人下厨的时候,果然是只在头上系了一个帕子,腰间围了一条围裙。
半个小时后,女人让为为端上来一个精致的沙锅。沙锅是淡黄色的,锅盖上面静静地卧着一条鱼,一片荷叶。掀开盖子,里面正扑腾着诱人的酸菜鱼,女人还送上四碟清淡的小菜,自己榨了一点果汁给她们做饮料。
那天晚上,为为宿舍的几个同学揉着肚子,打着饱嗝,回到了宿舍。一个同学说,哎,这宋姐家的香米饭可真好吃,我吃了两碗,肚子都撑坏了。另一个同学说,这下子咱真是吃了人家的嘴软,都不好意思去议论人家了。另一个说,她做的酸菜鱼味道也不错,像她的人,有点与众不同。不过,她的年纪真是看不出来,总有四十多了吧,也可能五十岁了。为为这天晚上倒是没有说什么,她听到同学赞美女人,有些莫名地自豪,好像同学在赞美她似的,暗暗地受用着。
几天以后,为为下班回到宿舍,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几个同学都向为为围拢过来,问为为女人说什么了?为为说,今天,小饭店里只来了四个客人,而且是一道来的,可能也是哪个学校的四个男生,宋姐一锅酸菜鱼搞定。我听到那几个男孩好像是说,其中是哪一个得了奖学金,不然不会花如此多钱来吃酸菜鱼的。后来没有顾客了,宋姐就和我闲聊,她可能是听到那几个男孩在说女友的事情,就问我恋爱过吗?可有男朋友?
为为的同学哄笑起来,说,为为,你一定要说你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样,或许就可以抛砖引玉了。
为为说,我告诉她现在还不算有男朋友。同学就问,她怎么说?为为说,她没说什么,只是用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了一句:年轻真好。有同学说,有门了,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有故事的。
为为在女人的小饭店打工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闲下来的时候,她鼓足勇气问女人,宋姐,这个酸菜鱼馆你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得过去,为什么要让我来你这儿呢?女人正低着头绣着手中的活计,听为为这么说,就放下了手中的十字绣,看着为为,对她说,你不是嫌工资少吧。为为忙说不是不是。女人说,你都说得对,你看到了,这里的顾客主要是附近几个学校的学生,我的酸菜鱼馆对他们来说,算是高消费了。所以,我开的这家酸菜鱼小饭店的生意始终不怎么好,我让你来我这里,也的确不是因为人手不够。你来问我这里是不是要人那天,我在厨房,回头看见了你,看见你清纯的朝气的脸,就想到,让你来吧,来和我做做伴,有时候,有电话来叫外卖,也可以让你帮我送送,当然,你看到了,这样的时候不多。
情况就是这样的,为为。这样于你也不是坏事呀,在我这里打工,不太累,也不会过分影响你的学习。女人说。为为没有说话,又在那里低着头抠着指甲,突然抬起头来,鼓足勇气,提高了声调说,宋姐……又突然不说了,欲言又止。那语气和神情,像是在悬崖勒马。
女人笑了。为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包括你的同学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我都知道。为为听女人这么说,脸突然红了,啊了一声,张着嘴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才好。
女人看看门外,对为为说,这会儿可能不会有什么客人了,咱们打烊吧,你在这里等着,我上去拿一样东西给你看。为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会突突地跳,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晚上回去要和同学说什么。她站了起来,关上店铺的门,却急着要打开心中一扇早已欲开的窗户,窗户外面是什么样的风景,她和她的同学都不知道。
女人从阁楼上搬下来一个方方的盒子,将盖子打开,问为为,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为为看了半天,还是摇了摇头,她睁大眼睛,看着女人。女人不说话了,只是弯着腰在那里摆弄着这个方匣子。不一会儿,方匣子里面的东西转了起来,竟然有音乐传出,为为听出来了,那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女人对为为说,这是一台老式的电唱机,上面的圆盘,就是唱片。女人又拿出了几个纸口袋套着的唱片,给为为看。为为发觉这些纸口袋,已经变黄变脆了。
为为听着这熟悉的旋律,看着匀速转动着的唱片,感觉到,旋律真是从这个电唱机里面流淌出来的,徐徐地,缓缓地,汩汩地。
女人说,你们现在听的都是立体声的音响,一定没有几个人听过这种老式电唱机了,可能见过的都少了。
女人说她比为为还小一点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她的父亲是资本家,解放前,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棉纱厂,不用说是首当其冲遭到了批判。在此之前的其他运动中,都因为她父亲虽为资本家,但抗战时期曾经资助过抗日,而幸免于难。“文革”的爆发,天罗地网般,使得他们家这回没有成为漏网之鱼。
她说,她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骄阳似火,万里无云。外面的行人不多,柏油马路蒸腾着太阳的热辣。一伙红卫兵闯进她家里,拿来一个纸壳做的牌子,揪出父亲,说要批斗这个剥削阶级的资本家。
女人说她父亲是很讲究的一个人,当时已经很少有人穿西装了,一般情况下,男人在比较正式的场合,都是穿中山装,可她父亲进进出出,还是一身的西装领带,皮鞋也是擦得一尘不染。那个时候,父亲走在大街上,算是很显眼的。
那天,父亲衣柜里的西服领带被红卫兵强行拿出来,扔在地上,几个红卫兵愤愤不平地在上面踏来踏去。
女人说,父亲过去总是告诉他们,人是要注意仪表的,这也是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一个人,如果连自己这一身都收拾不好,还能说什么呢?那时候,总是很难理解父亲的这几句话,那是因为在学校里,老师教育学生要艰苦朴素。穿着补丁摞补丁衣服的同学,常常给老师表扬。
女人告诉为为,红卫兵到她家以后,又把她父亲的十条领带全部系到他的脖子上,去游街批斗。红卫兵在游街的时候,不时地扯着他脖子上的任何一条领带。罪行当然是资本家崇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穿着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服饰。女人说,自己的妹妹,就是那天看见父亲给人家这样批斗以后,吓坏了,在家哭了三天,以后就神经错乱了,到现在还住在精神病院。
女人说,为为你想像不出来那个场景的,就是你父母,也未必能知道。可是为为,那一次红卫兵那样撕扯推搡我的父亲,在游街批斗他的时候,他的神态没有一点猥琐和失态,虽然没有那么优雅裕如,但远远看上去,还有一种不屈服的从容在里面。后来,我才体会到,为什么父亲说仪表要讲究,这时看来,简直就是一种多年的修炼了。当然父亲让我们读书,让我们听电唱机播放的经典乐曲,后来知道,这些也是可以衬托和诠释仪表的,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仪表。
“文革”前,父亲让我们在剧院里听过一些当时不多见的歌剧,我和妹妹还看过歌舞剧《东方红》的演出。父亲甚至托人在上海给妹妹买了一架钢琴,让妹妹学习。
再后来,女人说,红卫兵就抄了我们家。我和妹妹作为资本家的后代,也不能去上学了。接着学校的同学老师都去搞“文化大革命”了,学校也就停了课。那几天,我们家也不像家了,像是任人宰割的一块肉。只是,我自己心里发誓,就是拼了命,也要把自己万分喜爱的这个电唱机和这套唱片留下来。在家里,我把电唱机和唱片东藏西藏的,有时候晚上就守着它们睡觉。可那时候,何曾睡过安稳觉呢?眼睛一闭,就是噩梦。
我的电唱机和唱片还是没有保住,在后来的一次抄家中,给一帮红卫兵找到了,这拨红卫兵里有许多是我的同学,他们戴着红袖章站在我家里的时候,我看着他们。不久前,我们还是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同学,现在是两个阶级阵营中的人了。我们艰难地对视着。他们凛然的眼神,划出了我们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同学都是一拨觉悟很高的左派,他们中间不少人不乏到我家听过唱片的,那时他们也是很喜欢听,甚至羡慕我们家有电唱机。这会儿,他们因为这台电唱机和唱片,要变本加厉地给父亲添加罪名。我哀求他们,说你们是知道的,这电唱机是我的,不是我父亲的。他们不予理睬,执意要搬走,我哭喊着,歇斯底里地和他们吵,这是家里我最爱的东西了,我对我的这些革命同学嚷道,唱片里面有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是革命剧目!
《白毛女》知道吗,为为?女人问。为为点点头说,听说过。女人说,可能当时颇能显现艺术特征的就是这部歌剧了,我家里当时还挂了一张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喜儿的一个造型的画作,是我妹妹临摹的一幅油画。
女人说,我自己都不知道,那几天,失去了我最心爱的电唱机,我是怎么过的,像丢了魂,失魂落魄。
没有想到的是,一天夜里,天下着小雨,一家人惊魂未定刚睡下不久,一阵急促的低沉的敲门声响起来了。一时间,我们全家人都紧张起来,以为是红卫兵半夜又来了。我听着声音不像,就自告奋勇地把门打开,一看,门口站着的是我的一个男同学,他抱着一个大包袱,头上脸上湿漉漉的,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汗水。为为,这个场景可真像当时的电影镜头。那天抄我们家的时候,他也来了。
我惊奇又警惕地睁大眼睛,对他说,成爱民,是你,你半夜来干什么?他说,你先让我进去再说。我只好把他让进了我的房间。成爱民放下了手中的包袱,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雨和汗,喘着气说,我把你们家的电唱机和唱片给送回来了,你打开看看。外面下雨了,雨还不小呢,我怕淋湿了这些东西,就用我父亲的棉大衣给包上了。他告诉我说,当时抄出的许多东西都让红卫兵砸坏了,他看到我那么喜欢这电唱机和唱片,就始终看管着,东西拉到学校室内体育馆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搬了下来。这天晚上,他叫上了他弟弟,砸了体育馆的窗户,爬进去,又从里面把门弄开了,才把东西弄了出来。
为为,你知道吗?我这一生,也许就那一次可以用生命来理解“惊喜”这个词汇的,那是极度的惊和极度的喜相交融,那是在悲哀无望的十八层地狱下,看到天上闪现的彩虹般绚丽的惊和喜。此前,我只知道这个叫成爱民的男同学,喜欢默默地注视着我。他是工人阶级的后代,用当时的话说,根正苗红。此刻,我们各自的家庭背景,变成了各自的阶级背景。
成爱民说,我和他们一道来抄你家的时候,看到你是那么喜欢这个。你一直跟着我们到门口,哭着说里面有《白毛女》,说《白毛女》是革命剧目。我就想,我一定要想办法给你弄回来,不惜一切。
我一头扑进了这个落汤鸡般的男同学成爱民的怀里,感激、信任,命运在刹那间还原一切,又颠覆一切。还有,那突发的岩浆般汹涌的爱情。我只有哭了,那哭是极度惊喜之后情感恣肆的滂沱和喷发,我哭着,还努力要忍住那无法控制的哭声。我一边哭,一边拿一条干毛巾擦着成爱民脸上的汗水和雨水,又把自己的泪水蹭到了他的脸上,然后,又给他擦干,又接着蹭,如此反反复复。
为为,女人说,我无意说你们这代人爱情的平凡。但是我们这代人的爱情,因为时代的原因,就有了那种惊心动魄的淬砺和不同命运的引领。
我和成爱民相爱了。就在那天夜里,我拉下窗帘,熄了电灯,点上蜡烛,把我们家的唱片全部放给成爱民听。一首一首,一圈一圈。那时候,他也不太懂,只是说,这些个资产阶级的乐曲怎么那么好听?我不知道怎么给他解释,就只有说《白毛女》和《东方红》给他听,这两部是他知道的无产阶级的作品,我说这就是艺术。
后来,我们商量了许久,决定电唱机和唱片仍然由他帮我保管。因为那时候,我家随时都有可能有人来抄家。
他冒险给我送电唱机和唱片的事情,还是让别人发现了。当时,几个红卫兵团体联合起来要批斗他,因为他父亲是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红卫兵的头头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没有批斗他,只是把他从红卫兵的组织里清理了出去。在那一段时间内,他成了没有组织的逍遥派。
他父亲对他做的那件事情也很生气,认为他胆子太大了,混淆阶级立场,给工人阶级家庭抹黑。可谁也没能让他交出我家的电唱机和唱片。后来,为这事情,他父亲居然用麻绳抽了他。
成爱民最后还是跟他父亲走了。他父亲因为有点文化,又因为是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被调到一个县里的大三线厂当工宣队队长去了。一家人都搬走了。
走之前,他又在半夜里跑到我家。那次他到我家的时候,浑身是汗。他告诉我,他把我家的电唱机和唱片,送到了他的一个远房的哑巴叔叔家里,这个哑巴叔叔非常喜欢他,和他亲,他让我一定放心,说这个哑巴叔叔是铁杆工人,而且还是一个单身汉。说着,他写下了他哑巴叔叔家的地址。我一看,他这个哑巴叔叔家离我们这里有三十里路,而且经常不通车。我无法想像,成爱民是怎样抱着这么一大堆东西,还要掩人耳目地步行那么多路的。
成爱民手里还拎着他哑巴叔叔送给他的两条草鱼,说是给我们家的。我又激动得流泪了,知道他为了帮我送电唱机到他哑巴叔叔家,一天没有吃饭,就在厨房洗了一条鱼,准备给他做一碗酸菜鱼。
女人含着眼泪笑了笑,为为也低头抹了一下眼泪。女人说,那时我们家的情况已经不好了,家里也没有现在这种酸菜,碗橱里只有一点早上剩下的小菜雪里蕻,更没有现在的红尖椒,只是装辣椒粉的瓶底还有一点点辣椒粉,我找来毛衣针刮了个干净,才刮出最后的一点点粉末,家里当时甚至连烧菜的菜油都没有多少了。就那样,我热了一点冷饭,做了一碗酸菜鱼给他吃。
那天夜里,他在我的房间里吃酸菜鱼的场景,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为为,你能想像出来吗?一对不知道明天的命运是什么的青年人,就在那里享受着短暂的幸福,是我把那个晚上的一切命名为幸福的。你是可以想像出来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吃我做的酸菜鱼,我在一边看着他吃。没有人说话,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天亮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不得而知。当时我们共同的愿望,就是保护好电唱机和唱片。
女人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为为估计他们的故事要告一段落了。
以后呢?为为忍不住问。以后嘛,女人笑着长叹了一口气。以后,几乎就没有见过他。二十年前,有一次在街上见到他,还没有辨认出来,就擦肩而过了。至于他的情况嘛,当然知道了,因为我们都是同学啊。他后来怎样了?为为问,为为其实是想问他结婚了没有,当着女人的面,她没有直说出来。
他后来没有回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在他父亲的那个县里招工,进了一家化工厂,后来他结婚了,和同厂的一个女工,有了一儿一女。
宋姐,他一直没有和你联系过?为为问。女人没有回答为为。
女人说,三年以后,“文革”虽然没有结束,但我父亲因为资助过抗日,所以后来的处境就有所改善了。我按照成爱民留下的地址,找到他的哑巴叔叔家里,拿到了电唱机和唱片。女人指了指为为面前的这台电唱机,就是这个。
女人说,去的时候,看到成爱民的那个哑巴叔叔的家里很简陋,几乎是家徒四壁,可我家的电唱机和唱片,却还是用成爱民父亲的棉大衣包得好好的,放在一个没有上漆的箱子里。我费力地打着手势问他成爱民在哪里?他只是使劲地摇头。我说我要找成爱民,他立刻张开双臂做出阻拦我的姿势,并且拼命地摇着头。
再后来呢?为为问。女人说,后来我才醒悟过来,他那哑巴叔叔的意思,可能是让我以后别去找他,一定是他感觉到我们如果结合是不相宜的,老一辈人就是看得远一点。婚姻和爱情可能不是一回事情吧。后来,我就一个人这么过着,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知道自己不会再有那岩浆般的爱情了。人这一辈子,能有个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为我冒险送过电唱机,我已经很感激了。婚姻嘛,没有也就罢了。有时候,同学聚会我也参加,可他倒是一次也没有去过。再后来,我退休了,没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开了家小饭店,简单,以酸菜鱼为主。不忙的时候,我还是把这个电唱机拿出来听听,尽管后来出来的各种音响我都买过,但这台电唱机和唱片,我始终保留着。
这天晚上,为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