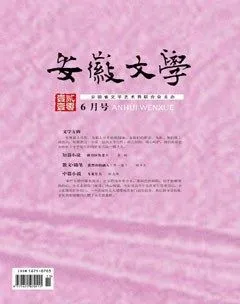明月夜里梦李白
2011-12-29吴晓卿
安徽文学 2011年6期
某个时刻,我纵身一跃,失重的身体在太空飘忽、旋舞,穿越芊绵时光,直抵那个伟大时代。
我看见明月如霜,明晃晃地照亮长安郊畔的一处茅屋,如豆灯火渐明渐灭,诗人杜甫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起身伫立窗口——思念滋生于这样静谧的夜晚。古旧的窗花糊着白纸,月光渗进,小心翼翼地滑落到房间的一角,地面显露出柔软光泽。植物灵动起来,兀自摇曳,它们的气息把夜色搅浑。他的思念浮出来,一点一点。
杜甫的脸庞,在月光下,异常皎洁,他沐在温柔月华中,不能不想起一个人——李白。那年三月,李白离开朝廷,他们在洛阳初见。“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闻一多曾这样激动地描述他们这场惊为天人的遇合。其实,这场被后世传诵的会晤着实简单,当时李白已是公认的大诗人,而杜甫尚在走向大诗人的途中,杜甫只是李白众多粉丝中不起眼的文学男青年。
公元744年。这年洛阳的牡丹开得格外地娇艳,这多少抚慰了诗人那受伤的心。李白和杜甫相见于某处高亭,当然可能不止他们两个,盛唐文豪们同往开封、商丘游历,对酒当歌,吟诗作赋,好不快活!该有多少欢言与美酒啊,长空如碧洗,他们衣袂翩跹,陶然共乐。这其中又有多少不可言说只能意会的万种风情,我们无从揣度,历史的洪流将这一切倾覆,他们头戴高冠,手中的美酒玉杯,湮灭在虚无时空。
那时的诗人杜甫看起来有些寂寥,寂寥的他,三夜频梦李白。他铺展卷纸,挥毫写就《梦李白》,他低徊欲绝地吟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窃以为,这是写实诗人老杜最浪漫幽婉的一句诗。因为李白,他敬慕的文学巨匠被流放夜郎,他只知李白身陷囹圄,并不清楚当时李白已被释放。于是,文人那如水的忧伤情怀如一张网,细细密密将老杜裹缠。他在明月夜里梦李白,如同我等弱冠文学青年某夜偶梦东坡。
那时的李白,该是二十五岁,与我这般年纪,却已有远大志向——“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青年李白是一个超级驴子,他游历了蜀中很多名胜古迹,他行进的路线,是当下资深老驴梦寐的地方。在途中,李白写下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出三峡后,李白依江而下,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时逢开元盛世,才子李白发出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呐喊。他写蜀道,写黄河,写庐山瀑布,写友人离别,写独旅心情,还写闺情怨女。
林语堂认为他了解苏东坡,因为他喜爱他,而杜甫了解李白,是因为他从李白身上看到了自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何尝不是写他自己呢?老杜是苦吟诗人,他是悲情的,李白其实也是。同样施展不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诗人的傲岸使他们无法为五斗米折腰,不能圆融通达于官场——伟大的诗人不适合从政。又经历一个国家由盛至衰的跌宕,最后寂寂死去。
李白是杜甫平生最倾心的诗人,就如苏轼倾慕陶潜,曹雪芹倾慕阮籍,这是后人对前人的敬仰,是相同志向性情的吸引。尽管李白与杜甫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李白浪漫大气、一挥而就的才情是老杜没有的——老杜被李白深深吸引了,折服了,类似于文学小青年对文学巨匠的崇拜。杜甫的后半生不停地怀念李白,他写李白的句子成了千古绝唱:“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而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则属应酬,他可能写过就忘了。
杜甫的诗读得不多,我浅薄的感觉——老杜是沉稳笃定的,常常为了一个字,眉头深锁,捋着山羊胡子苦苦推敲,力求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后世的画像中老杜总以一副纵横沟壑、苦大愁深的长脸出现。世人偏爱李白,因为我们都喜欢“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洒脱豪情,李白是人们理想主义的化身——理想的性情,理想的才情,理想的纯情。
杜甫说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是凡人的诗人,而李白是“天上谪仙人”,是供给凡人去念想去梦见。一千二百多年后,不再写古诗的现代人,某天从故纸堆里翻出杜甫诗集,千年的尘埃随风飘散。那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穿越浩渺时空,轰然直抵心脏。于是有人在临睡前,微闭双眼,喃喃地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