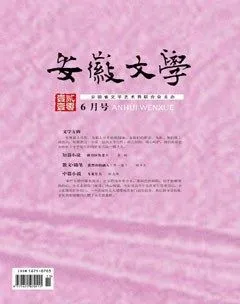母亲的村庄
2011-12-29孙长江
安徽文学 2011年6期
定居小城后,我似乎成了村庄的过客。确切地说,现在的村庄让我感到陌生。这种陌生感来自于地域和时空的差异,十几年的光阴足以让一些人和事渐行渐远,包括我的村庄。
联系村庄的一直是母亲手里那根长长的电话线。二叔病了,癌症,晚期,母亲第一时间就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你能回来看看吗?”母亲小心翼翼地问我。“能,请了假就回去。”我想是必须要回趟村庄了。母亲开始唠叨:你二叔都是抽烟喝酒惹的,一天两包香烟,三餐酒,前年就病了,一直拖,孩子又不争气……
从村庄的商业街里穿过。母亲在等我,电话里就一再强调一定要在12点以前回来看二叔,看病人是不能下午去的。二叔的家还在水塘旁边,还是以前的老瓦房,只是水塘变得越来越小了,曾经那么宽阔的水面,清澈的湖水,现在只剩稻谷场般的大小,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垃圾,水塘四周建起了许多厂房,对面电管站宿舍楼的生活垃圾漂到二叔家门口都是。二叔坐在厅堂桌旁,瘦得吓人,颧骨高高凸起,脸色蜡黄,病恹恹的样子,对我的到来很吃惊,毕竟我多年未回村庄了,拉我在家吃饭。我看见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拒绝了,丢下几百块钱和一些补品,安慰一番,和母亲一同回家。路上母亲说,不要给二叔添麻烦,那个样子了。母亲很伤感,一路叹气。
第二日,恰逢是农历十五,母亲一早起来要去镇上白衣庵去烧香。白衣庵在镇上很有名气,周围几十里的人都经常去烧香、许愿、祈祷。农历初一、十五更兴旺,香客云集,鞭炮声不绝于耳,敬香磕头都要排队。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突然想陪母亲去烧一次香。母亲有些喜出望外,让我洗脸,换件干净的衣裳,嘱咐我不要乱说话。
我机械地跟着母亲后面烧香、磕头、求签。母亲说,当年你考大学、调动工作都是来这求菩萨保佑着的,你要好好敬敬香。我突然有些感动。那些年我在一个小山沟教书,一直想调回小城。后来,小城的一位校长,与我因文字结缘,费尽周折,把我调回去。一次乘车回山沟学校,在长江大桥上,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说:你不要着急,我刚刚去白衣庵帮你求了菩萨,菩萨说今年能调回去的。这个电话让我止不住泪如雨下……我在车上用报纸遮挡着脸,任泪水肆意流淌。
小时候总想离开母亲的视线,但总是逃离不掉,常常在尽情玩耍时,被母亲逮个正着,一顿好打,乖乖地回家写作业。现在每次回村庄,我总跟在母亲后面,陪母亲聊天,听母亲唠叨。在母亲的唠叨里我知道了村庄这些年发生的许多事情:许多人家都不种田了,本来田就少,现在被征收得差不多,许多人便在街上做事情。和我童年的王四喜现在在街上跑出租车,还顺便帮人家收账,要工钱什么的;赵二胖子发了,在商业街开了大酒店,镇上的一些机关、学校,还有村委会都是大酒店的常客;钱三多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些年在街道上混事,现在突然也发了,开了大浴场,整天洗澡的人还不少;王大爷的儿子又进去了,三进宫了,这次是打劫,听说判三年,他爸还在找人……母亲还说到钱蛋子,他是我儿时最好的伙伴,两人曾经一起放牛、偷瓜、踩藕,干尽“坏事”,母亲说他运气很背,媳妇在街道上班跟一个开发商跑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母亲还告诉我一件喜事:奶奶现在一个月能在政府领一百块钱养老金,村里人到六十岁后都能领到养老金了,还是政府好啊!
第三天回小城,母亲送我去公路旁等车。一条县级公路,横穿田野,两边的田地里建起了许多高楼大厦。公路成了小城的商业街,热闹非凡。超市、商场、发廊、浴场,应有尽有。偶尔,可以看见一头母猪从没有关紧的猪圈跑出,大摇大摆,穿街而过;或者看见一头发情的公牛咆哮而来,街上的人显然早已是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横七竖八的广告牌,迂回纠结的电线,一股小城镇气象扑面而来。我的村庄呢,我儿时纵情疯跑、少年时挥汗劳作的田地呢?我的心里起了一丝怅惘和失落。
等车的时候我看见了小丫。她坐在自家服装店门口,打扮入时,丰腴了许多。母亲早在电话里就告诉过我,小丫结婚了,在外打工挣了些钱,回来嫁给了村长儿子,在商业街开了家服装店。小丫算是我的初恋。我们一起玩耍,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初三毕业小丫没有考上高中去沿海打工,我读高中,我们经常写信,都说些天真的话。我考上大学那年暑假,小丫回家参加她姐姐的婚礼。乡村的夜晚,安静极了。我们开始在大树下偷偷约会。两个年轻人说着一些断断续续的废话。相互把对方的手攥得很紧,手心里全是汗。有那么一次,小丫想把自己给我,我没要。我知道我最终不会属于这个村庄,我给不了小丫一个承诺,我不想亏欠村庄和这里的人。
村庄,再见!透过车窗,我看见白发苍苍的母亲一个人站在商业街的公路旁,目送着我,两旁的商业街热烈非凡,抬头看见那幅巨大的某品牌的内衣广告在逆光下很刺眼,刺得我的眼睛模糊了。
再见!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