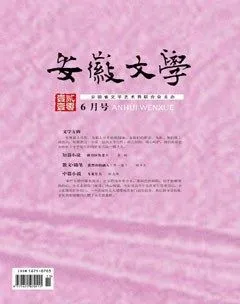徽州脸谱
2011-12-29许若齐
安徽文学 2011年6期
屠户七斤
读小学时,经常被教育着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写过一篇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本子上当然是解放军战士什么的,心里想的却是小镇上那个杀猪卖肉的屠户——七斤。用当时样板戏里的一句台词说,就是“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吃得不好不饱使然。那是一个什么都匮乏的年代:米、布、油、肥皂、香烟、火柴……严冬早晨四五点钟,北风凛冽,滴水成冰。镇上不少人家的门“吱”地开了,闪出一个个缩着脖子,睡眼惺忪,挎着篮子的身影。背后总有人要叮嘱一声:别忘了带肉票。在昏暗的路灯下,一溜人踩着满地白霜,朝副食品门市部方向蠕动、聚集。那里两扇门冷冰冰地紧闭着,门口摆着一块其大无比的剁肉案板。以此为起点,人们跺着脚,搓着手,连接成一条长龙。那年头,吃肉不容易啊,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每天汤汤水水里飘着的几星油花子,一家人十天半月才有的一次小牙祭全靠它了;插队农村的子女溜回家,也少不了要一碗红烧肉润滑一下缺油的胃肠。东方终于泛出了鱼肚白,排队的人也兴奋与躁动起来。那些个砖头、木棍、破篮子顷刻变现为大活人,队伍也拉长了将近一倍。一番争吵和推搡后,最终都无奈地接受既成事实。因为这些玩意的所有者,不是强汉,就是悍妇,你是弄不过他们的。人们希冀的目光,开始投向不远处的小吃店。卖肉的主角七斤,此时正坐在里面的条凳上,就着热乎乎的豆浆,咬着刚出炉的大饼油条。店小二正围着他,点头哈腰地忙前忙后。他四十来岁,原在养猪场杀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二十年,不知背了多少条猪命。据说有一次他用布蒙住眼睛杀猪,一刀了结,然后放血去毛、开膛剖肚、大卸八块。众人看呆了眼,“屠户”由此闻名遐迩。两年前,七斤调到门市部专司卖肉,又成了小镇上的“要人”。这不,在众人目光的追捧下,他腆着肚子,晃悠悠地走出来,不时地用手指把嘴角边残留的芝麻送进口里。七斤打开门,用特制的抓钩把猪肉拎到案板上,刀斧并用,连砍带剁忙乎了一阵,那猪头是头、腿是腿、胛是胛地分成了几大块。买肉者大抵以两为计量单位,绝少超过一斤的。只见七斤手起刀落,一块肉往秤上一甩,误差绝不过半钱。这可是真功夫,也让他赢得了一些名声。众目睽睽,克扣斤两的缺德事七斤是不干的,他对自己在街上的“名头”还是挺看重的。他最瞧不起那个把四盒火柴拆成五盒卖的上海“小赤佬”,更何况他干的是公家的事情。至于你买到什么肉,则要取决于七斤刀下的情分了。最倒楣的是割到肥腻腻的槽头肉或连皮带骨一挂的,让你哭笑不得。若还咕咕哝哝地计较,七斤会凶巴巴地吼着:下一个。当冬日的太阳三竿高时,案板上的肉也卖完了,唯独剩下一个猪头围了一圈人,要买不买地犹豫着。七斤用刀敲着案板,挺有板眼地嚷着:猪头肉好吃,吃了还想吃,下酒味道香,要买赶快买。直到有人拎着猪头无奈地悻悻而去。每次人们发现案板下的箩筐里,总有几刀好肉。都知道这不是给领导、就是给相好留着的,却又无可奈何。领导喜欢前胛,相好喜欢后肘,七斤安排得妥妥贴贴。
七斤在小镇真吃得开:出门乘客车,总是坐在司机边上的位子,那是不用买票的;七斤嗜烟,两只耳朵边总夹着“前门”;走在街上,迎面的是一片谦恭的笑容和热情的招呼。他最喜欢下午在案板前,靠在旧藤椅里懒懒地晒太阳,就像一大袋口子没扎紧的土豆。七斤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吐出的烟圈在空中能完整地漂浮着,还时不时地拿起满是茶垢的大搪瓷缸咕咚几口。常有少妇过来与他搭腔,“七斤七斤”叫得又甜又酸。无非是打听一点明日卖肉的行情。七斤总是卖关子,说些荤兮兮的笑话逗乐子。少妇带着几分嗔恼地捶他:不要脸的死七斤。七斤一点也不躲闪,十分快活地大笑。
时过境迁,当年卖肉的地方,如今建起了一个歌舞厅,红红绿绿、亮亮闪闪的。门口放着一个大音箱,放着一些当红歌星的流行歌曲,男男女女,进进出出。七斤又在何处呢?问了几个上了年纪的人,都摇摇头,居然没一个知道。
乡村木匠
在过去的徽州乡村,一代代的木匠大抵是这样产生的:没考上学的儿子从城里灰溜溜地回家了,耷拉着头,蜷缩在昏暗老屋的一角,全然没了平日的嬉劣。父亲无不忧伤地注视着墙上泛黄了、秀才模样的祖宗画像,搔搔头、摆摆手,长叹了一口气:学一门糊口的手艺,做木匠去吧。
其实,做木匠在当地不失为一种上好的选择。“三匠”之中,石匠太苦,砖匠太累,尤其是对南川老万家的万贵这样细皮嫩肉的后生。他从小被宠着,书读不进去,整天想着被县剧团招去,哪怕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也很风光呀。真要去学木匠了,万贵倒没什么失落,只是坚决不拜师。整天拿着斧啊、刨啊在家里捣弄,嘴上一刻不闲地哼着黄梅戏文,什么“你织布来我耕田、你挑水来我浇园”。乡村的木匠,能把家具打成个模样,凑合着能用就行了,哪有什么精雕细作。手艺好些的,出来的活看上去充其量像个粗眉大眼的村姑。万贵挺聪明的,无师自通,不到两年,就成了方圆几十里地面上颇有名气的师傅了。那时,山外的县城里刚流行海式家具,什么“四十八条腿”。万贵只进了一趟城,回来比比划划,居然也像模像样打出了一套,而且没用一根铁钉。被村里的大户根发花三百块钱买去,摆在当小学老师儿子的新房里,抢眼了好一阵子。万贵就这样火起来了,约他的活至少要提前一个月。他也开始摆谱了,工钱倒在其次,待遇可一点马虎不得:譬如上门做活,早饭要么是肉丝挂面,清汤清水的,还要盖上两个煎得金黄的荷包蛋;要么就是一大碗油亮亮的蛋炒饭。烟瘾倒不大,但要抽“东海”牌的。当地有民谚:生产队长“大铁桥”,大队干部“猫对猫”,公社干部“水上飘”(东海牌香烟),万贵讲的是档次。中饭、晚饭也得要有那么像回事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