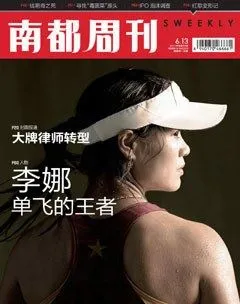周耀辉的心思与风度
2011-12-29邓小桦
南都周刊 2011年22期
周耀辉平和、均速的叙述,大概是港式独有的文艺味,那是比内地和台湾的文艺都要冲和的淡然;但在抒发内心感受时,我却品味到隐隐有一种海派的文风,朦胧间依稀是张爱玲式的透彻苍凉。
周耀辉是香港著名的填词人,经常给“达明一派”、黄耀明、“人山人海”、AT17等较有文化气息、脱俗另类的歌手、乐队写词。他并不时常曝光,也没有工厂式的多产,但每每出手,总能创作出那种有深意到你永远都记得的作品;他始终不驯服于流行工业,每次都像在尝试拓展整个工业的容纳度:经典作品如《排名不分前后左右忠奸》,竟能在流行工业中做出这个如概念艺术般的作品,把玩艺术和政治,又嘲讽流行工业的本质。我还记得初次听到《黑房》里“你舌尖舔着我要害”的句子时的震撼,连我也要羞愧于自己的审查意识。
据说词坛另一圣手林夕对周耀辉词作的形容是“有仙气”,是啊,《爱弥留》里的“请收起你的温柔/浮在水仙中的杀手/请收起你的风流/垂在钟摆间的借口”,意象多么迷离;《随身听》里“当声音随心飘/我耳畔荡着玫瑰花//前面隧道快到达/沿路尽是一片白/多美丽念着千句话/别寂寞让别人害怕”,这分明是诗,而且是非常具有现代都巿感的诗。
我只见过周氏真人一次,而他的确就是像他的作品一样,仿佛围绕着淡淡的光晕,从来没有因为常规的折磨而老去。看周耀辉的随笔小集《突然十年便过去》,便感觉到,那种变化与恒定,是如何在他身上糅合为一。
周氏的散文文笔,也是诗意秀丽,叙述语调冲淡柔和,讲起日常生活琐事,心头不是没有波澜,但总以一种温和的语调驾御。这些散文是素朴而诚实的,周氏在写作时直面他与亲友爱人的关系,绝不煽情,不迁怒,不贰过,也不夸张善恶美丑的对立,用流行话来说,就像是无添加的纯净水。周耀辉平和、均速的叙述,大概是港式独有的文艺味,那是比内地和台湾的文艺都要冲和的淡然;但在抒发内心感受时,我却品味到隐隐有一种海派的文风,朦胧间依稀是张爱玲式的透彻苍凉。我一面读,一面想起我非常喜欢的香港散文家俞风;至于周氏的爱情纠葛,则令我想起另一位香港文人,早逝的李国威,他也常写爱情的龃龉。大概,他们都是成长于同一年代,吸收了1970年代香港本土文学的养分,在他们的文字中可以见到善感而不膨胀的自我,并且感到个体的情感,经历城巿生活的打磨,仍然绵密,不会僵化。
而如果我们静下来,慢慢在周耀辉的字里行间逡巡,其实我们会发现其中也有芥子须弥的惊涛骇浪。在平淡的句子中,我们会发现,周耀辉的心思突然会跳得很远,有一些和外在环境极不呼应的感受,所以在匀速句式的行文里,某些部分,文章的浓缩度和跳跃性会大增,寻常人要么接受不来,要么容易错过。比如《醉过新年》,一般醉后是流露自我,而他明明醉得厉害,回家对镜自照,却感到非常陌生,然后完全以抽离笔法写镜中做鬼脸的“丑陋面孔”(其实周氏何尝丑过),写那脸孔接连做鬼脸来证明自己拥有那张脸的控制权,而后又马上抽离地想,做鬼脸这行为看在别人眼里一定很怪。短短几行已经转了好几个角度。周氏可能是那种仿佛林黛玉式“极欢之际,突然流下泪来”的人,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常常笑的悲观的人”。他会在婴儿诞生时禁不住在脑里担心,比如担心孩子智力是否健全、会否有身体缺陷,这些固然是断断不能在喜庆期间说出口的话,而周耀辉更进一步担心到身体的缺陷联系到前世的忧伤,“那孩子喝过什么婆的什么汤,仍然记起前生的什么,待要出世时,却又后悔了。进退之间就此桎梏在生死关头。”这更是说不得的了。周耀辉也在文章中坦率地说过,如果我没有把自己心里所想的说出来,那就不会添加大家的麻烦。唉,只有文人知道,聪慧敏感,有时反而会带来人世的灾难。
本书里也记载了许多情爱的折磨。我有时觉得这样把事情披露于众人之前,也真算是惊心动魄。但也许那个城巿还不复杂,没有太多狗仔队,也容让个人有放浪和徘徊的余地,公共的版位也还有容纳私人的空间。在工作或家庭日常,周耀辉是在意他人目光的,但在爱情这部分,他却是毫无保留地写。
可是都巿的压抑毕竟是要有个出口的。回看起来,周耀辉原来写过很多很多关于“出走”的词作,像王菲的《流星》。他并没有把自己“偏离常规”那一部分压抑下去。可能是像他母亲说的,“条颈硬过鬼”(极其固执之意)。
关于偏离常规,我喜欢周耀辉是淡淡地说起,一点不高蹈。他和旧友聚旧,嘘寒问暖之际就谈到工作和理想,每个小小人儿,吃饭喝茶时也可以谈到如何营造更民主的生活、更开放的社会。他从不在犬儒的角度去嘲笑理想,也不会听到别人谈起理想就自惭形秽,想想这其实里面是有深厚的自信,对于自己始终能够实践自我、趋近理想的自信。其实有时我想问那些文化大腕在大富大俗之后,听到淳朴的理想时,能否还像周耀辉那样有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