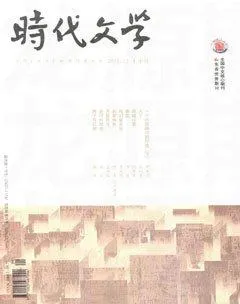阿来:侬本多情
2011-12-29徐坤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11期
话说1997年年底京城的严冬,一个叫阿来的一脸沉静的藏族青年,端坐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作协10楼的会议室,听一群学者诗人宣判《尘埃落定》一本奇书的命运。他面如重枣,色如佛陀,眉间一颗醒目吉祥痣,表情亦僧亦俗,棕深色的衣袍,鞋子上蒙着尘土,仿佛已经走过很远的路,无数等身长头千山万水跋涉到此。
尘埃落定。嘉绒草原初霁的雪地和啁啾啼叫的画眉,一下就把在座汉人们的心擒住。谁也不知道这个格萨尔王的后代、年轻的游吟诗人是从哪里来的,他吟唱的一段近代藏民边贸史也仿佛熟悉又陌生。精致、绵长的汉语纪事,不仅有甲骨和雕版的硬度,更有丝绸和羊皮卷的柔软,还加上了酥油青稞酒的香醇。人们都被这部说唱史诗迷住了。
谁能想到,这却是一次半民间性质的青春聚会,到会的拥趸,几乎都是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人们更无法想像,彼时,在1997年底开这个会时,《尘埃落定》的书还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印刷厂没出来,人们看到的,还仅是《小说选刊·长篇增刊》上选摘的20万字书稿。
当然,就连阿来自己也没想到,不出几年,这部陌生藏族青年的陌生作品,就成为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经典。
那次会,应该是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的一次聚会。今天,在哪里还可以找到不花钱、完全出于热爱而给一个陌生作者和陌生的书开个研讨会的事情吗?没有了。而在那个时代,都说是商品经济大潮铜臭滚滚的时代,竟然还有那样一群年轻人,有信仰,有决心,尊重和崇拜文学,将写作当成神明,每每看到一部好书、读到一篇好文,就由衷喜悦奔走相告。他们将读书当成这一群人心有戚戚站在时代高地的接头暗号。
《尘埃落定》这部从1994年完成之后就在各出版社之间艰难游历的书,直到1997年才由《当代》编辑周昌义、洪清波将“疲惫的书稿”带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高贤均看后称赞是部好小说,决定出版。出版社将订数定在很冒险的一万册。
当此际,中间出现一个人,对阿来这部经典的问世和后来的举世闻名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他就是当时《小说选刊》的编辑关正文。当时他常为他们的《长篇小说增刊》到各出版社抓书稿,高贤均向他力荐《尘埃落定》,他看过后决定先选20万字发。刊物出来后,又是这个关正文张罗要开个《尘埃落定》研讨会,并且决定不要老面孔,不要老生常谈,刊物送到新派评论家手中,还送了一句话:有谈的再来,没谈的不必勉强来。效果是奇异的,研讨会本定在40个人左右,结果来了60多人,很多人是知道了《尘埃落定》这部书来研讨会旁听的。很快报纸上陆续出现关于评价《尘埃落定》的文字…… 这下该出版社坐下来商量对策了。”(见责编脚印的回忆录:《阿来和〈尘埃落定〉》2003年12月29日央视国际网)
脚印女士大概还不知道,刊有《尘埃落定》的杂志还是由关正文自己开着车子挨家挨户送的,那情景相当感人!那次会,除了人文社的几个年轻编辑外,记得李敬泽、戴锦华、崔艾真、徐小斌等都去了,都发了言。我那篇发言文章题目叫《小说,作为一门叙事的艺术——读〈尘埃落定〉》,首先高度表扬阿来作为一个藏族作家,比汉族作家还要纯熟的汉语思维和表达;然后分析他的整个知识结构,就是《史记》以降的汉民族文学文化传统,以及欧美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到米兰·昆德拉的政治性解构主义风格的影响。最后提到,以傻子为主角的故事,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读起来都不陌生,比方说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比方说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比方说历史书记官的舌头两次被割比之于司马迁受阉刑……
“阿来的写作可以说是继承了先锋派的叙述手法,同时又避免把自己对语言的纯熟敏锐把握当成杂耍技巧炫耀,而是采取更为平实贴近的态度,把所有的机锋、所有的才情,都在看似朴拙实则精道的叙事中加以掩藏。他运用他从前写诗的经验,将小说中的对话和描述处理成诗一般的有韵律的形式,但是比诗更自由,在隐喻的处理上更加明朗和豪放,段落结局处一些对历史的叩问和反诘时时呈现有华彩的调式,其对历史颠覆和反讽的面目在抒情式挽歌的豪华盛宴里总是欲盖弥彰。期间并无任何哗众取宠噱头或添加某种媚俗的商业发酵剂,而是将小说真正当成一门语言的叙事艺术来做。从这一点上说,阿来也为今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方向,为那些业已瓦解的宏大叙事的恢复提供了一点信心,也同时辟出了一道可能险胜的蹊径。”
我之所以要大段摘引1997年12月写下的对阿来的评价,目的无非是为了借阿来大师出点小名,也顺便佩服一下那个年代我们村儿里的年轻人!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那么纯净、纯粹,心无旁骛,连喜欢也是由衷而纯洁的。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们,再也无法激情燃烧地阅读某部书、然后抱有虔诚之心第一时间写出有硬度的评论,一如年届知天命之年的阿来,再也不会写出饱含青春气息的、抒情华美的《尘埃落定》,而是写出有如摩挲转经筒、参禅入道般的《空山》、写出大众欢乐文化辞典《格萨尔王》。
那次会议之后跟阿来也没有什么来往。无意中在一篇冉云飞与阿来的谈话录里见阿来说过这样的话:“在不少评价《尘埃落定》的评语中,我个人比较看中女作家徐坤所认为的我所作的努力,是在探讨一种取胜的险道。当然这种取胜并不完全是像竞技体育那种夺冠后的胜利感。”
这是发表在1999年05期《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文章,见了他这样的谈话,让我不禁有了点小得意,也让我跟阿来心有戚戚焉。此时的《尘埃落定》还没获茅盾文学奖呢,所以阿来还可以提及一下晚辈女作家的文章。等到获奖以后,评的人多了,俺就挤不上咧,哪还能入阿来的法眼哦!
有关我的这篇书评,还有个后续的小故事:后来在刘庆邦的文章里又见提及。庆邦2005年发表在《山花》杂志《有关徐坤的几个片段》里说:“她有一篇评介《尘埃落定》的文章,我是偶尔读到的。看徐坤文章里流露出的那股子高兴劲,仿佛《尘埃落定》不是阿来写的,而是她徐坤写的。近年来,我很少看长篇小说,一是长篇小说太多了,看不过来;二是有点时间我还想着炮制自己的小说呢。出于对徐坤的信任,我把《尘埃落定》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