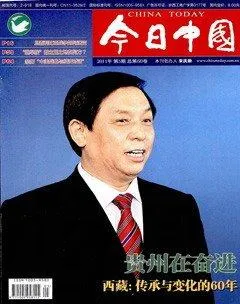挚友
2011-12-29
今日中国·中文版 2011年5期
傅鹰:奋翅归来终不悔
何瑫
1922年,20岁的燕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傅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祖国。他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在中美之间多次往返,被称为“美国两次都留不住的科学家”。
6年之后,傅鹰的博士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美国一家化学公司的注意,对方派专人拜访并许以优厚的待遇,条件只有一个——长期在那里工作。
傅鹰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友张锦商量之后,谢绝了。回国后,傅鹰先后任教于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岛大学、重庆大学,并在1935年与张锦完婚。1941年,他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理工学院院长。其时,厦门大学七个带“长”字的重要人物中,唯傅鹰不是国民党员。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甚至专程来到厦门,亲自劝说他加入国民党。傅鹰却倔强地表示:“我宁可不当院长,也绝不加入国民党!”并借口外出招生,对陈立夫避而不见。
这件事在文化教育界一时传为佳话,但是他也因此难以在国内继续开展科研工作。1944年底,他和张锦第二次远赴美国,回到了曾经就读的密歇根大学,与当年的博士生导师巴特尔一道从事表面化学研究。
此后的五年内,他一心沉醉于学术研究之中,在美国化学界的声望越来越高。巴特尔希望傅鹰继任他的职务,傅鹰十分高兴,这对他“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还击,打伤了“紫石英”号。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发表声明,向英方提出强烈抗议。
这一爆炸性新闻使傅鹰相信,祖国不再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令人无可奈何”,而是有了希望。他与张锦当即决定回国。其时正值张锦怀孕,很多朋友善意地劝他们晚一点回去,因为凡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可成为美国的公民。然而,傅鹰夫妇却恰恰因为此事着急,巴不得早一点离开美国,为的是使未来的孩子不入美国籍。
1950年8月,傅鹰夫妇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号”客轮,驶向祖国的怀抱。从此,他们一直为新中国的科学进步而努力工作。
当时的傅鹰,已是国际公认的表面与胶体科学家。但他却并未满足于所谓的“功成名就”,而是“把帮助祖国发展工业和科学作为严肃的首要任务”。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坦诚直率地发表过许多有胆识、有创建性的意见,将所观察到的问题和盘托出,毫不隐讳。
“他这人‘大不吝’。”傅鹰之子傅本立曾这样形容他的父亲,“‘让我说我就说,什么都不管不顾’。他就这性格,不说假话。”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傅鹰当年的一些言论也颇有些“惊世骇俗”。1957年,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下,他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如下观点:“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傅鹰如此“大鸣大放”,在“反右”中竟然安然无恙。而这得益于毛泽东的“钦点”: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写道:“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不过,“文革”开始后,傅鹰不再有“反右”时的幸运。当时已是北大副校长的他,和北大校长陆平、历史系教授翦伯赞成为重点批斗的对象。
即便是被关入牛棚,他还是不改直言不讳的本色。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上头”派人了解傅鹰的动向。他对来人说:“我担心总理死后天下大乱!”来人问:“‘天下大乱’是什么意思?”傅先生直截了当地回答:“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了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傅本立回忆说,一次父亲被拉去批斗,眼睛都被打紫了。他陪着父亲回到家,感到很气愤,于是问父亲:早知今日落得这个地步,当初选择回到新中国后不后悔?父亲回答得很干脆:不后悔!
2002年,傅鹰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致函北大:“傅鹰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拥护党的领导,以主人翁的态度向党进言献策,是党的真挚诤友。他刚正不阿,在逆境中仍坚持真理,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傅鹰先生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