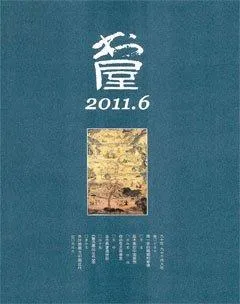当古典遭遇世俗
2011-12-29张中驰
书屋 2011年6期
一
从2002年的《长门赋》到2011年的《子在川上》,前后十年,两篇小说的题目以古色始,以古香终,古典意味浓厚的两个题目遥相呼应,从中不难发现阿袁对古典文学的钟爱。然而细读作品,既没有陈皇后的凄美,也没有孔夫子的庄严,这古色古香的题目要告诉你的竟然是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家长里短。
文学史上,纯粹以知识分子作为讽刺对象的典型小说大概可以追溯到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为古典小说,它向我们讲述了“儒林”狼藉不堪及“士”阶层丑陋、萎靡的精神面貌。时至现代,学者钱钟书的《围城》仿佛预示着这类小说将会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条脉络被传承下来。凭借着辛辣、洒脱的文笔及对新式知识分子灵魂深刻洞察,《围城》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将目光停留在当代,千百年来一直罩在文人头上的光环终于彻底褪去了,“文人”作为一个尴尬的名词,似乎其本身都带有讽刺意味,没有谁再肯以单纯的“文人”自居。在这种情况下,以文人为讽刺、批判对象的小说更是层出不穷,比如表现文人极端的失落与放纵的贾平凹的小说《废都》,这些作品深入到文人的私生活,揭露其腐败与颓废,为文学作品创造了新的书写空间,然而对于钟情于《儒林外史》与《围城》的人来说,其中总是少了些风味,好像没放孜然的羊肉串一样,辛辣有余,口感却得不到满足。我们一直期待着在这条线索上会有新的节点,直到阿袁作品的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读者的“胃口”。
作家阿袁本人在大学教书,于是似乎顺理成章的,她小说里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师大”这个她熟知的环境。近年来随着她小说数量的增多,它们渐渐为读者拼构成了一副当代大学校园里逼真的生活图景。这些作品里所要表现、讽刺的大学教师与前代的知识分子相比已经改头换面,批判的矛头也改变了方向,作品传达出的精神内涵也与前代的完全不同。但阿袁的作品也是以自身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为述说对象,以消解知识分子的崇高为己任,她的叙述雅俗交织、睿智轻快,她犀利的文风、调侃的语调以及黑色幽默的气质都与上述两者暗暗相通,不谋而合。
以当代大学校园里的知识分子(多为教师),这个社会上的较小的精英群体为述说对象,是多数读者所不熟悉的,于是小说不必营造便自然而然的有了陌生化的效果,读者也会因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而被吸引。而现如今世俗的故事到处都有,跌宕的情节也并不稀缺,这类小说能否成功就更多的取决于讲述的方式了。阿袁的小说并没有刻意的追求小说的技巧,往往是轻轻松松地直奔主题,接着就水银泻地般地铺陈开来。在笔者看来,阿袁的小说精彩之处,更大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古典语境下的妙语连珠以及对人物心理极其迅速的白描。她的话语表达及思维方式里包含着同样给人以陌生化效果的雅与俗的强烈冲突;她的故事情节里充盈着对人物内心情感细腻而精准的剖析以及对人情世故文雅而又泼辣的解读。这样的话语遭遇这样的心思,它们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如此独特,给人以非凡的美感。
二
中国的传统诗论爱讲“言有尽而意无穷”,爱讲“言约而旨远”,古代的诗词文章都在不自觉的追求这样的语言特征。然而在白话文一统天下的今天,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学经验虽仍被人们当做经典提起,实质上却因与当代作家的追求异趣而早已被架空。阿袁在这个时候用自己的作品起死人而肉白骨,赋予古典以新的解释和生命力。读阿袁的小说第一感受便是惊艳——惊其语言之艳、古色古香的艳——她用成熟了的古典语言来写现代的世俗故事(学院里的俗事),本身就构成了冲突。在这种冲突之中,古典的精致典雅、婉转曲折不仅被用得极尽反讽之能事,也在与世俗生活的遭遇中创造了喜剧效果。如在《马群众的快乐经济学》中,马群众因背叛了未婚妻而陷入苦恼,作品是这样说的:
按下来的日子,马群众是冰火两重天。快乐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身体有多快乐,精神就有多痛苦。身体和精神一分为二。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两者各为其主,浴血奋战。马群众的精神对陈荞忠心耿耿,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马群众的身体却早已是逆子贰臣,去意已决,无可挽回。精神是黄沙百战穿金甲,身体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精神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身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以往的作品中,人物肉体和精神斗争并不少见,少见的是用这种方式对两者的反复渲染。背叛爱人后心理描写在读者的期待视野内,但这种表述方式则开拓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作者仿佛在以身体和精神为主题写一副对联,其中杂糅了比喻、夸张、对偶、排比及反复、回环、移情等等,词汇与诗句运用的工整、贴切又不着痕迹,整段文字一气呵成,让人欲罢不能。用慷慨激昂、富有哲理的古诗词来表现大学教师在世俗欲望里的挣扎,每一句都是含蓄的,整体来看却又表露无遗。诗词与欲望这两者精神高度的悬殊以及教师的身份与其思想间的反差所营造给读者的,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甚至有些许新鲜、刺激的阅读体验。诗词本是凝练的,繁复的使用是对其本身用法的反叛,于文章,则让情节推进时富有节奏感,读者便能在这一唱三叹中细细回味。
如此段落在阿袁的小说中层出不穷,读这些小说,读者很容易发现它们对古典语言的回归。可以猜测这种回归一方面是刻意为之,更多则是因为有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以后的自然流露。这种古典的素养反过来又使作者对白话文的掌控得心应手,白话于是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话,它身上也有了文言的痕迹,并在同文言的碰撞、交织中营造了珠落玉盘一般朗朗上口的语感。在世俗与古典这个框架内,小说制造了高尚与低俗、散乱与工整、直白与含蓄、繁复与凝练等等参差有致、相互冲突的效果,而古典修辞与其所表达内容之间自然地形成了反讽的意趣。
大学的教师一般来讲对本专业都有着精深的研究,而阿袁笔下老师不仅如此,他们更善于将专业的智慧直接运用到生活中来,与现实交锋时,成败都不重要,关键是精彩。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也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本来对现实的作用是间接、曲折的,如果生搬硬套地去解释世界,则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喜剧效果,这甚至也是形成小说风格的原因之一。比如《子在川上》的苏不渔,因为研究魏晋文学,便有了魏晋的名士风度,为人处世上任性而为,不拘无柬,这为他与系主任矛盾的展开提供了条件,也为全文的喜剧风格打下了基础,既有了新意和高度,又在名士与世俗的斡旋中实现了反讽。再比如《鱼肠剑》中的孟繁,因为研究李商隐,便表现出了李商隐诗歌的婉约气质,于是围绕着孟繁展开的情节便都与这婉约挂了钩,在孟繁因被吕蓓卡称呼孟姐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一节,有这样的分析:“高校里的人逮谁不是叫老师呀?关系生分的叫老师,关系亲密的也叫老师,敬重的叫老师,讨厌的也叫老师。老师的意蕴最丰富多义,几乎和李商隐的诗歌一样丰富多义。言简而意丰,多合适的一个称呼。”
这是人与人之间难以察觉的,即便察觉出来也难以表达的微妙关系,然而在古典文化与之相遇的时候,理解它变得如此简单,它里面蕴藏的种种意味都在瞬间被转化为对李商隐的感觉里,这是我们熟悉的体验,心照不宣,不言而喻。
三
有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作家在古典的语境里浸染的久了,体现出来的不仅是语言逻辑与表达方式上的相似,他的思维方式与他眼中的世界自然都会蒙上一层古典的色彩。用古人的画笔来描绘今人的景象,将古典的触角深入到大学教师的琐碎生活,捕捉人物内心的细微活动,然后用古典的情感模式去揣摩今人微妙的爱恨情仇,是阿袁的一大创新。在阿袁的小说里,古代的文人墨客时而出面,为男女主人公吟诵自己的诗词佳句,这些句子要么切合当时的情境,要么契合男女主人公的心理,用这种古典的视角来打量当今的世俗情感,既有书生气,又有市井气,既有世俗的现实冲击力,又有古典的醇厚韵味,难能可贵的是两者能自然地合并在一起,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俗语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在《看红杏如何出墙来》,饭店的名字都是古典的,要么叫“西厢记”,要么叫“莱根香”,紧接着说陈叶子受的戏弄是“风戏荷叶水戏萍似的戏弄,是哑巴吃黄莲似的戏弄”,再紧接着这样形容几个人各怀鬼胎,“陈叶子是为撇清之前的误会;余东坡呢,也为喝酒,也为看戏;老盂是为渔色;朱婵娟或许是为被渔,或许只为调戏一下渔翁”。小说的古典氛围便在这隔三差五地运用的诗词典故中营造出来,而阿袁更习惯反过来在这种古典的氛围中去构造一篇篇具有都市情感特点的小说。比如,小说《虞美人》所选取的题材是具有现代观念的大学校园里男女老师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是从始至终,作为夫妻的陈果、老猫与疑似第三者的虞美人都在自觉的维持着一个平静甚至愉快的局面,而只在各自心里翻江倒海,这是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所致,更是作者的古典视角使然,从这个视角展开的故事,注定了世俗的欲望与挣扎将被浑厚的古典所包裹。整体看来小说的精彩已经不在于凌厉的甚至戏谑性的诗词、妙语的铺排,而在于古典唯美的氛围被世俗的诱惑不断地尝试着打破,并因此形成的一种张力。《虞美人》的情节并不复杂,但要讲好这样一个故事却不简单,因为故事得以进行下去,靠的全是人物不经意的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关系以及各自心理上的微妙变化。而古典语汇、诗词意象及古典的表达技巧向来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优势,最善于处理的便是这种“微妙变化”。下面是自己的老公在深更半夜跑去给虞美人修电脑时,陈果的一段内心独白:
陈果知道虞美人是如何挑逗老猫的,是良家妇女中略带有一些风尘味的,是亦正亦邪的,亦人亦鬼的,言语也好,眼风也好,都是多义的,这般想,没有什么意思的,那般想,却全是风月。虞的把戏,陈果看得一清二楚,陈果是开了天眼的道士,即使妖精七十二变也能看回原形的,但也只是看回而已,降不住的,陈果既没有桃木剑,也没有鬼画符,再说,自己老公的道行不深怨别人干嘛?
这样的白话仿佛“熔炼家常语”,落笔精辟雅隽,语工意新,言语率真自然,表达却细腻婉转。正与邪、人与鬼、道士与妖精、桃木剑与画鬼符等等比喻诙谐幽默、不落窠臼且韵味十足,既写实,又写意。心理分析可以淋漓尽致,但心理本身又是虚无缥缈的,不可以量化和程式化;情感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小说可以将其定格,放大给读者欣赏。阿袁这种古典的思维模式与表达方式有着言尽而意不尽的效果,将重重思绪娓娓道来,让人回味无穷。
以古典作为一种视角,阿袁长袖善舞,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古典优美与反讽的张力,但与此同时,其中局限也昭然若揭。古典的语言经过几千年加工与沉淀,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优雅,而“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却还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学语言,于是重新运用古典来书写当下,与粗糙的语言环境中造就的作品相比,无疑占据着很大的优势。但正因如此,它更容易将自身的使用者带走。阿袁笔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的一直生活在世俗的、失落的现实中不能自拔,每个人到最后都还依然过着琐碎、卑微的生活,这些都源自于古典文学其自身过于雍容而批判现实的力度不够。如耿占春所说:“在我们自以为是语言的主人之时,我们已沦为某种既定文化的囚犯。”也正如福柯所说:你以为你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阿袁古典的袖子没有舞出钱钟书一样的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涵,便是因为她过于沉溺在古典的语言里(甚至将语言作为游戏)而反过来被话语诉说了,因此不可避免地会缺乏《儒林外史》那样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缺乏《围城》那样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询问与思考。这是古典的不足,也是阿袁暂时的不足。
中国古代文学向来有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但自从白话文创始,大多数时候我们要么将传统文学当做经典来供奉,要么兴之所至,用纯文言的写作来对其追忆。在阿袁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坚持,她将古典的抒情与叙事融为一种写作姿态与气质,并一直在她的笔下得以体现。中国自古有雅俗之争,众口难调一直是文人写作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阿袁将世俗的故事化腐朽为神奇,做到了雅俗共赏,用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步入文坛以来,阿袁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它们以质取胜,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为其本人赢得了声誉,但在为其喝彩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阿袁创作中存在的缺陷。限于作家的生活及创作环境,她的小说题材过于单一,虽然篇篇都很精彩,但整体看来变化不大,因而有主题先行的嫌疑,读者也很容易因陷入一种雷同感当中而感到厌倦。另外,前文提到阿袁的小说虽凭借其古典的素养而独步,但同时也被古典文学悄悄引入其消极的一面,影响了小说的气象。《子在川上》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苏不渔的《告全校师生书》将魏晋名士风度注入到粘滞、僵硬的大学校园中,让人心胸舒畅,这是古典对比当下时显现的力量,也是阿袁应该抓住的地方。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据此,我们有理由期待阿袁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也可以想象如果阿袁写出长篇,会不会成为当代的“新儒林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