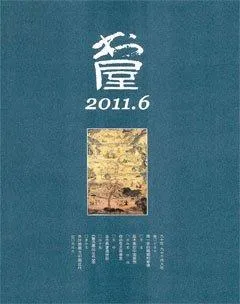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
2011-12-29杨云宝
书屋 2011年6期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将大力推进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这是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对于出版业来说,受其影响最大的是信息化。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在出版业中的主要表现就是数字出版,它的基本特征是: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
数字出版虽然是个新的业态,在发达国家已经初见端倪,在我国方兴未艾,它对传统出版形成了挑战。对此,人们不得不审慎研究出版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发达国家数字出版发展态势
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和高度普及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数字出版的引领者。近年来,适应于互联网发展形势,方便学生查阅图书和资料,美国在新建一些大学或改造个别老校时,不再建盖图书馆,大规模建立数据库及各种数字终端,以数据库来取代传统的大学图书馆。同时,为了保护环境,减少纸张、印刷和发行费用,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施瓦辛格宣布,从2009年开始将免费发放给中小学生的教科书改为免费提供电子书包。此举既方便学生,又使每个学生一年可为州政府减少一百美元的政府公共财政开支。随后美国又有几所大中学校推行电子书包。
另外,受互联网发展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报刊发行量大幅下滑,大约每年下降百分之十,发行量下降严重的像《西雅图时报》等报纸甚至停止出版纸质报纸,只出网络电子版报纸。创刊于1851年、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2010年表示,未来将停止印刷《纽约时报》,改而主攻网络订阅等经营模式,并认为,网络可能是报纸的最终归宿。
与此同时,数字出版成就给人印象深刻。美国亚马逊书店推出的电子阅读器的发行量大幅攀升,已超过同期精装书的销售,直逼平装书的销售。同时,苹果公司推出的苹果平板电脑和苹果智能手机的销售,不仅在美国节节攀升,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一年内就分别销售几百万台。由于受到互联网、平板电脑、手机和手持阅读器等数字媒介的多方夹击,美国的纸质图书、纸质报刊销售的下滑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图书零售巨头博德斯公司2010年全年关闭六百多个连锁店,整个图书销售业务全面萎缩。
为适应读者的需求,日本索尼公司也推出电子阅读器。近年来,由于受到数字出版的冲击,日本的传统出版市场一直处于萎缩状态。2009年日本出版业的销售额比2008年减少百分之十六。为了应对数字出版的挑战,日本的三十八家出版社于2010年3月成立了“日本电子书籍出版协会”,此组织几乎涵盖了日本主要的出版社。
据2010年德国出版业的调查,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出版公司德国的斯普林格集团2009年从数字化方面获取的收益已超过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但是,人们也看到,传统纸质图书和报纸依然是出版商的主要利润来源。在德国2009年出版业九十六亿欧元的收入中,电子图书的营业额仅占百分之一点八,而且德国四分之三的互联网用户不愿为数字内容付费。
面对数字出版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在发达国家对出版业的发展前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预测:一是掌握数字出版技术的厂商预言,数字出版将较快取代传统出版。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曾放言,大约在十五年内完成这一转变。随后微软公司正式发表的文告中指出,数字出版取代传统出版大约需要二三十年。二是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士预言,数字出版和传统传统将在未来的发展中长期共存,并驾齐驱。2010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双方争辩电子书的地位。一方认为,电子书迅猛发展的势头表明,出版业已经站在数字出版的门槛上,未来图书领域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数字出版,纸质图书将逐渐消失。有业内人士估计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十五年,美国可能会提前三四年。另一方则认为,虽然数字出版在逐渐增长,但它与纸质图书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2010年德意志银行的报告认为,数字出版使出版业面临重新洗牌和整合,传统书店可能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最大牺牲者,预计到2015年,传统书店营销份额将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
二、我国数字出版发展情形
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信息技术的提高和应用普及,尤其是年轻一代读者的成长,我国国民阅读习惯和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从2010年4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来看,人们的阅读习惯正从“纸质阅读”向“电子阅读”转变,电子阅读以“普及性、经济性、移动性、便捷性、互动性、音画性”的特征,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阅读时代。据2010年统计,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四点二亿人,每天上网时间总和超过十亿个小时,巨大的网民人数和巨大的上网时间孕育着巨大的市场前景。因此,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在短短几年内突飞猛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出产值屡创新高、手机出版异军突起、电子阅读器风生水起、数字出版盈利模式不断创新等发展态势。
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表明,2009年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达到七百九十九点四亿元,比2008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点六,数字出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总体经济规模首次超过传统出版物。在数字出版内部,手机出版的营业收入已超过传统的网络游戏,占数字出版全部营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二,位居首位。新闻出版产业的总体格局在技术进步的带动下已发生改变,初步形成了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区。
2010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建立全国第一个数字出版基地——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2008年,上海市数字出版产业实现销售收入一百二十三亿元,远远超过传统出版,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2009年增长百分之五十达到一百八十五亿元,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这其中张江基地贡献了九十亿元的产值。张江模式迄今已结出了累累硕果,在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出版结构转型上凸显成效,更为全国各地数字出版基地的未来摸索出一条道路,成为全国数字出版的领跑者。2010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又批准虹口园区为上海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延伸园区。
鉴于人们普遍认为,数字时代“内容为王”,谁掌握了数字资源,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2009年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数字出版网”工程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信息化试点。人民出版社争取到三点四亿元的国家财政拨款打造公益性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传播平台。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与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双方将通过组建合资公司的形式,携手打造一个面向全球用户的专业数字出版与运营平台。同时,该公司还与中广传播集团公司就三网融合创新教学平台及电子书包应用系统业务合作之项目——睛彩中南空中教学项目开展战略合作,将会建立一个融CMMB无线数字广播网和互联网、通信网为一体的教学平台。安徽出版集团将开通“时代”网上教育平台,推出全国第一份教育类手机彩信报。陕西出版集团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建立国内最权威、最完整的音视频资源数据库。中国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等出版商推出旗下自主品牌的电子书,重庆出版集团与汉王科技合作推出“读点经典”阅读器,《读者》杂志推出电纸书。著名的民营出版企业万榕书业则宣布全面进入电子书领域,将它所拥有的全部图书同时在纸质、手机、互联网和电子阅读器上出版,成为国内第一家全媒体出版商,并宣称已在数字出版领域开始盈利,估计在二三年内,数字出版利润占它整个出版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汉王科技的“汉王”、盛大文学的“锦书”等电子阅读器和北大方正的阿帕比公司及“番薯网”、中文在线网等技术提供商,特别是百度、新浪、搜狐等网站利用强大的数字平台纷纷涉足数字出版,与传统的新闻出版业合作,已分别拥有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电子书出版资源和数以百计的报刊数字出版资源。2010年底,方正电子推出的天津日报电子新闻阅读器已成功登陆。正式面向公众提供移动新闻阅读服务,这是移动阅读器在报业市场的第一个成功案例。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花巨资打造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通过互联网发布新闻。
为适应出版业发展趋势,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升级,推动我国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力争达到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形成八至十家各具特色、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产业园区,传统出版单位到2020年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把数字出版产业打造成新闻出版支柱产业。
然而,在数字出版繁荣的形势下,人们也注意到一些明显的问题。在2009年我国数字出版七百九十九点四亿元总产值中,手机出版和网络游戏的营业收入在数字出版营业收入中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一点三,数字期刊、电子书和数字报纸(网络版)三者营业收入所占比重不足百分之三;数字出版收益内部结构不平衡,数字出版在我国传统出版业中的收益微不足道;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呈现萎缩态势,未来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此外,许多有识之士特别关注到数字出版面临的五大困局:一是数字出版产学研尚未有机融合,致使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奇缺。二是数字出版资金投入巨大,但其盈利模式尚在探索中。三是数字出版产业链各环节联系不紧密,内容提供商和技术提供商各自为阵,尚未找到合理的耦合方式。四是数字出版的版权之争将愈演愈烈,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难以协调作者、出版社和技术提供商三者的利益关系。2011年3月,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度网站与作家们的版权之争就是例证。五是数字出版面临严重的盗版和非法下载问题,对作者和出版社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数字出版终将取代传统出版
数字出版取代纸质出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主要jQ4C+f9yuwyZ2m3bge/ZGNuEEqZi+bKlEL3WiSsf8ho=基于环境保护、经济成本、便捷互动和技术进步四大因素的考量。由于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对使用树和草等资源进行加工的造纸业成本必然会节节攀升,加上印刷和发行成本上升使传统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相比有明显的先天不足,
尤其是数字出版拥有的高效、开放、交互、共享、音画等显著优势,决定了数字出版的发展势不可挡,从而导致人类文化积累与传播方式和传播载体的革命性变革。
从中国历史的纵向考察可知,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国文化积累传播载体曾有三次革命性变化。第一次是夏商周时期,文化积累和传播的主要载体是青铜铭文和甲骨文,取代了史前时期的陶文等,延续了两千多年。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竹简、木简和布帛取而代之成为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主要载体,延续了约一千年的时间。第三次是东汉蔡伦发明或改进造纸术后,尤其是唐宋以降,纸成为了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主要载体,延续至今大约有一千五百年的时间。总结这三次变革的经验,我认为,促使文化积累与传播载体变革的决定因素是,“经济性、普遍性、便捷性”等三个优势,而现在的数字出版除了这些优势因素外,还多了“互动性”和“音画性”两个优势因素。因此,数字出版取代纸质图书是迟早的事,目前我们正处于数字出版的门槛上。有识之士估计至多需要二三代人即可完成这一转变,时间快的话也就是一二代人、三四十年。决定取代时间早晚的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的快慢。曾有科学家预测,手持阅读器可以造的像纸一样薄,并可折叠。真是这样的话,那纸质图书就可进历史博物馆,或成为富人享受的奢侈品。
有的业内人士进一步预测,随着数字出版的崛起,传统出版业将面临重新洗牌,图书印制、销售企业甚至出版社将面临生存危机,有可能百分之百的书店关闭,百分之七十的印刷厂关闭,百分之五十的出版社关闭。虽然这个预测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们不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发展趋势。欢呼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更要未雨绸缪,对出版业的革命性变化预作准备,为数字出版的发展尽绵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