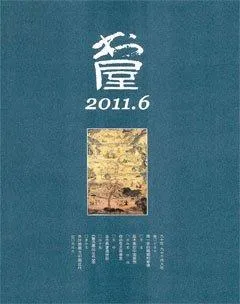清末民初热心扶植“新人”的说坛前辈
2011-12-29孙超
书屋 2011年6期
包天笑从清末编辑《时报》副刊《余兴》开始,就十分注重文学青年的提携和培养。周瘦鹃是一位在民初上海无论编刊、撰译都仅次于包天笑的著名报人小说家,特别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其文艺界地位更是如日中天。然而,起初,他是一位典型的被贫苦生活逼迫进小说界的“投稿家”,十六岁,当他还是中学生时就已经试探着走进上海文坛以谋取生。他在清末登上文坛的第一篇作品《落花怨》就发表在包天笑主编的《妇女时报》(1911年第一期)上。《妇女时报》不仅在周瘦鹃的成名路上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而且成为他早期发表小说的重要园地。据笔者统计,周瘦鹃共在《妇女时报》上发表作品三十六篇,居众作家之首,而小说作品则占了该刊小说发表总量的几乎一半(总数为三十七篇,周瘦鹃作品十六篇)。特别是该刊前十期,除第二期没有他的小说作品、第三期只登其一篇小说作品外,其余几期都是刊登两篇小说,几乎占据了整个“小说栏”,这充分说明了包天笑对起步期的周瘦鹃的高度重视和热心提携。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包天笑从书信中知道周瘦鹃在1912年大病一场,又知他家庭清寒,便预支一笔稿费给他,并在信中说,以后只要他的稿件一到,不论发表与否,即优先付酬”,这种在生活上的切实帮助不仅让周瘦鹃渡过了难关,而且增强了他继续创作的信心。仅从周瘦鹃在《礼拜六》创刊前发表小说的情况来看,他在《时报》系统发表作品总计三十一篇;在《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申报》、《民权素》上仅分别发表三篇、一篇、二篇、一篇,共计七篇。据此可见,包天笑所在的《时报》系统对他成名给予了巨大的助力。更为可贵的是,包笑热心扶植周瘦鹃完全出于对其文学翻译、创作才华的赏识,据载周瘦鹃第一次到《时报》馆拜访包天笑在1913年9月,这时距他在《妇女时报》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已有两年多了,他已经是上海小说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了。
张毅汉也是一位几乎全赖包天笑提携而成名的小说家。在《小说时报》的撰稿人中,包天笑很早便认识了张毅汉的母亲“黄翠凝女史”,她是清末民初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因为张毅汉经常为母亲送稿,他便与天笑认识了。后来,由于家境贫苦,张毅汉便将其译作投递天笑请他介绍发表,但当时毅汉是无名之辈,其文笔也不够好,其译作便每遭编辑部退稿。在这样的情况下,包天笑出于爱才之心,就帮其润色,并与之联合署名,才最终得以发表。张毅汉就这样才得以真正走上文坛,在民初时段发表了大量的小说作品。由于民初包天笑主编了多种小说刊物,正需要写作上的帮手,张毅汉其时恰好“中英文精进”,便成了他翻译合作者的不二人选。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至1923年问,以二人联名发表的小说作品有五十余篇,其中有不少收入当时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集《小说名画大观》、《天笑短篇小说》之中,另外二人还一起出版了小说单行本《断雁哀弦记》、《红泪》、《血印枪声记》等。正是通过这种联合署名的合作方式,包天笑将一位初出茅庐、作品无人采用的青年作者推举成了在民初颇有影响的小说名家,正所谓“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而且,据郑逸梅介绍,当时“所有稿酬悉数归给毅汉,毅汉对于天笑非常感戴”。当张毅汉在小说界慢慢成名后,包天笑更以一个文艺界名编辑的身份继续予以奖掖,在主编《小说大观》时,就将他称为说坛“大将”了。可见,包天笑对新进作家的提携真是不遗余力的。
再如,民初以《人间地狱》红透小说界的毕倚虹也是经由包天笑一手培植起来的。据包天笑说,毕倚虹之所以进入上海报界、成为小说家全因他的引导。他们的相识说来很有些趣味,天笑在编辑《妇女时报》时,经常接到署名“杨芬若女士”的诗词文稿,“颇见风华”。他明知道是“捉刀人”所为,但当时真正的闺阁之文难求,自然予以发表了。据包天笑回忆:“不久,倚虹到报馆里来见访了,我们谈得甚好,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二人从此订交,时在1914年到1915年间。当时包天笑正做《时报》主笔,又忙于各种小说杂志的编务,实在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包天笑曾说:“及至毕倚虹进了时报馆。那觉得志同道合,才是我一个好帮手”,“后来我们商量组织《小时报》,由他主任,而我也便帮助了他”。二人由于性情投契,很快便成了忘年之交。据有关资料来看,包、毕二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以致倚虹初入花丛,也是因了天笑的导引,遂后倚虹竟根据他们那段真实的北里生活撰出了一部堪可传世的《人间地狱》来。这部小说里涉及民初文艺界名人不少,对于他们叫局佑觞、游戏花丛的描写实在是当时上海文人日常交际的实录。而在1915年《小说大观》出版时。毕倚虹已经开始在时报馆工作了,于是自然成了包天笑作家阵营的“先锋队”。在包天笑的帮助下,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名小说家。在接着由天笑主编的《小说画报》上,毕倚虹发表了名震一时的《十年回首》,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包天笑曾给予这部小说极高评价,他说:“可惜(《十年回首》)这书未写下去,那要比李伯元所写的《官场现形记》高明得多咧。因为李所写的,只不过是道听途说,而他却是身历其境呀。”上世纪二十年代,当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时,毕倚虹也不忘反哺,为其主持“星期谈话会”栏目,并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每期都有,共计十五篇,无怪包天笑到了晚年还深深感慨:“这个时候,在写作上帮我忙的,以毕倚虹为独多。”可惜毕倚虹三十五岁即因写作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包天笑直至晚年还在追悔将他引入报界、文学界,他说:“如果不遇着我,或者他的环境不同,另走了一个康庄大道,也不至于如此身世凄凉。我对于他很觉一直抱歉似的……”可见,他们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
在清末民初,经包天笑提携后来成为名小说家的还有徐卓呆、范烟桥、江红蕉等人。徐卓呆后来被称为“小说界的卓别林”,在他文坛起步时期,包天笑经常与之合作翻译外国小说刊登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合作的形式“大概是天笑的文笔,用他的构思”;“范烟桥经常投稿《余兴》,天笑很赏识他的文笔诙谐有趣,为之赓续登载”,后又主动约请他写作了十回三万余字的弹词小说《家室飘摇记》,在《小说画报》上予以刊发,促其成名。江红蕉是包天笑内弟,自然得到天笑的精心栽培,后来撰写了《海上明月》、《嫁后光阴》、《交易所现形记》等小说,并出版了《江红蕉小说集》,很快成为民初小说界的红人。实际上,包天笑始终重视小说人才的培养,他曾在《<小说大观>宣言短引》中明确指出:“欲治病,先培医。”他认为,要想创作出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具有文学“兴味”的小说佳作,必须培养出懂得小说文体特点、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优秀小说作者。缘乎此,他爱才成性,经他培养出来的小说家真是不胜枚举。因此,他在民初文学界拥有了一支“可以算得无懈可击”的稳定而人数众多的作者队伍。正由乎此,包天笑被新文学家视为“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首席作家,被新时期研究者誉为“通俗文学之王”也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他在编刊过程中,由于始终坚持“一以兴味为主”的较为宽泛的采录标准,因此,就是后来成为“新文学家”的刘半农、陈独秀、冰心、叶圣陶等也都曾在其主编的刊物上牛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