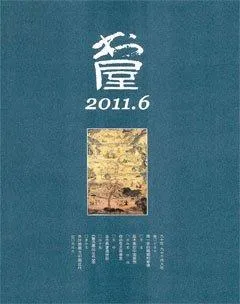芝加哥的中国风
2011-12-29姜异新
书屋 2011年6期
第三次赴美
胡适四十岁便开始撰写回忆录了,在太平洋的船上,他写下《四十自述》的序言,说自己是在赤裸裸地叙述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确认自我曾对社会做过了一番事业。这事业是什么呢?按照他对自己前半生的划分,除了留学,就是归国任北大教授,推行他在美国所习得的思维方法、科学精神和文化主张。
这是他第三次赴美,距上次来美已过去六年。1933年6月18日由上海启程,正在那一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枪杀。尽管胡、杨之间存在着温和与激进的分歧,对这个自己在上海教英文时的首批学生、康奈尔大学的老同学,惊悚之中的胡适仍难抑沉郁的悲伤。他是带着血的刺激踏上远途的,此前一个星期,还在紧张地编写《独立评论》,此时何日回国却不得而知。
第三次漂洋过海历时四个月,直至1933年10月与陈衡哲同船回国。期间与韦莲司通信及电报十五封,几乎未与其他人通信,日记暂缺。
如果说,四十岁之前,深受留美经历影响的胡适主要在中国传播美国文化,力图依照他在美国所看到的东西来限定自己在中国动乱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那么,四十岁之后,胡适则主要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贺司克尔讲座(Haskell Lectures)上的六次《中国文化之趋向》(Cultural Trends in China)的演讲,便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
1933年春,中国北方弥漫的敌对气氛已十分浓烈,早在两年前,刚刚再度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就收到了赴美讲学的邀请,然而,混乱的时局使其一度难以成行。1933年是世界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一年,全球各种新生力量早已引发了令人瞠目的革命性变化。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此年成为美国总统,忙于应付大萧条;莫罕达斯·甘地开始二十一天禁食,抗议英国占据印度,日本已经侵犯中国热河,华北危急中签订了《塘沽协定》。革命已成为中国的时代主潮,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鲁迅正在上海租界“无所挂碍”、“酣畅淋漓”地战斗,带着甘为人梯的心境,成为他人与后人眼中“赤膊上阵”的“左翼战士"。胡适却作为唯一公开支持不得人心的《塘沽协定》的人,幻想着整个华北的军事占领是换取日本人统治下的和平的唯一选择。在他看来,“上上下下整个的没有现代化”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直接原因,对战争的抵抗会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物质和思想成就完全毁灭。
“在成打的日本飞机飞临(北平)城上空的时候,用外文来做任何严肃的写作,是不可能的。”(1933年7月15日致韦莲司信)漂泊在船上的胡适才开始着手开列这后来被认为是其在美国最重要的演讲之一的提纲,并重订多次。近二十天的路途中,如何阐释并讲好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成为胡适主要的思索对象。同行的人经常看到他接连几日坐在打字机旁,时而凝神思索,时而飞快地敲打键盘。胡适却对自己极慢的撰写速度懊丧不已。在后补的日记中,他一再感叹下笔不能文思泉涌,尤其是写英文。不过,林语堂却非常佩服胡适那几百万字的英文著述,在他眼里,胡适的英文写作比他的中文还要漂亮。
6月20日,他列了一个《当今中国文化之趋向》的简单提纲:一、与西方接触之前的中国文化:1、宗教的衰败;2、新儒家的理学;3、理学的反叛。二、中西冲突带来的变化:1、慢慢接受;2、热情欢迎;3、疑虑重重与知识界的混乱。
6月29日,船行至火奴鲁鲁(Honolulu)。夏威夷大学的辛克莱博士上船来接,还有张彭春。胡适下船在夏威夷大学讲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国文艺复兴》,还不成熟,只是芝加哥大学演讲的一次匆忙预演。
接下来的很多天都是在拼命写讲演稿。期间,有位同行的迪林翰女士问胡适有没有读过Mrs,Pearl Buck(帕尔·布克女士)的小说Good Earth(《良田》),见其真诚的摇头,这位热心的女士夸张地说:“你到美国,处处必有人问你对此书的意见,还是让我先送你一本,在船上读了它。”说完,随即取出一本,递给胡适。
自此,胡适每每写稿倦极,便取出这本小说来阅读消遣。可是,越往后看,心里越不自在,深感作者实在不了解真正的中国,很多描写太脱离中国农村和当时革命的现实。就说主人公王龙的大儿子,原是辛亥革命后受城市学校教育的,却仍然要他的妻子裹小脚!这让胡适联想到许多自大的美国朋友总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待中国,好像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永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拯救似的。这更加促使胡适要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透彻地把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状况讲清楚。
芝大演讲
1933年7月7日,胡适终于抵达美国第三大城市“风城”芝加哥,随即下榻国际宾馆。Chicago出自印第安语,有“强壮”和“野生的洋葱”之意。冬季多风,夏季酷热。
7月12日至24日,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胡适在芝大前后讲了六场,经受着体能上的折磨,演讲间歇也不得休息,还要挥汗写余下的讲稿。为此,胡适差不多每天工作到天明,和在中国的潇洒自如相比,这次是真正的“写一篇,说一篇”。
芝加哥大学的哈斯克基金是由卡罗琳·E·哈斯克夫人设立的,为的是促进世界上由于不同的文化、宗教遗产而长期分隔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那时的胡适在美国知识阶层人眼里是这方面最理想的阐释者和文化大使,扎实的国学训练和系统的西方教育使他在文化上既属于东方,又属于西方,因而他是开放的、包容的、内敛的,同时又是激情的。他亲身经历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变迁,并成为开路先锋和深孚众望的领袖。正如A·伊斯坦斯·海登(A,Eustace Haydon)教授所说,他在国际文化交流、理解领域工作,具备评估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过程的文化背景和超然的洞察力。这组演讲是胡适第一次在西方文化世界系统阐述他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未来中国文化趋势的看法。
演讲中,胡适深入浅出地总结了中国在西方文明冲撞的过程中,从精神、政治、文学、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引发的震荡和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次总结和宣传。他希望美国听众能够明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变革已经而且正在中国发生,正在变成一种现实的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结晶。她看起来似乎带着西方色彩,但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却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通过准备这组演讲,胡适不再把中国当时的文化趋势当做孤立的变化来思考,而是当做一个在世界总的历史性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联结在一起的个体来重新看待。
“中国的文艺复兴”是胡适所描绘的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征,可以恰当地阐释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外来文明碰撞的过程中获得新的活力的再生过程。1917年6月,二十六岁的胡适从门关穿加拿大落基山到文苦瓦,在火车上消磨时间,偶然读到了伊迪斯·西奇尔的《文艺复兴》。西奇尔有如下描述:“似乎,这个时代再造出的人类比以前更光荣了,用赤裸的毫不害羞的身子,和那未曾受到束缚损坏的强健臂膀,指向了生命和光明。”这种言说方式对胡适仿佛是醍醐灌顶,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文艺复兴”应译为“再生时代”,字面的意义是“再出生一次的时代”。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坚持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前途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再生。
胡适信奉的信念是,只有把新的东西移植到一种活的历史经验上,才能繁盛起来,只有把传统拿到新思维方式的观照下,才会激发无穷的活力,未来决不会以一种与过去决裂的结果来出现,而会以对过去的诺言的实现而出现。为此,他竭力要从丰厚的历史遗产中精选出他认为将会与他希望在中国形成的现代观念完全一致的成分,竭力要在中国的现代经验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之间找到众多相似之处。直到晚年,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脑海中最深刻的还是读大学时最喜欢的那首卜朗吟的诗一《一个文法学者的埋葬》。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生的追求是什么,正是欧洲早期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人文学者“不顾生命,只要求知”的精神,难怪胡适会被西方人尊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胡适的演讲有着明智的外交策略,充分尊重了中西文化对这个世界看似不同,实则一致的理解。如何在西方国家展示独特的中国,如何促使中国人走出封闭,走向世界,是胡适终生的主题。他充满信心地谈到了中国通过西方影响的“缓慢渗透”而向现代社会的进步。他风趣地讲到皮鞋和烫发在中国的流行,成为中国人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的标志,他滔滔不绝地保证说,最终中国人是能够创造出“一种与新世界的精神并无二致的新文明的”。然而,在他于11月回到北京的时候,他最关心的却是不时提醒他的中国听众,中国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芝大演讲结束后,又举行了为期四天的研讨会。7月22日,作为委员会主席,胡适飞往班福(Banff)赴太平洋关系协会年会。在离开芝加哥之前,胡适将讲稿寄给了韦莲司。九月份,还在暑假期间,万分忙碌的胡适挤出时间去绮色佳与韦莲司相会了两次。胡适欣然接受了韦莲司的建议,将此次演讲稿分成四节,不另冠标题。(1)经济变化与政治革命;(2)社会阶级的重划;(3)家庭的分化;(4)妇女的地位,再加一个结论。
9月30日,胡适从华盛顿给艾格顿(Edgerton)和海顿教授发了电报请他们到芝加哥火车站来会面。艾格顿立刻热诚地践约,还有海顿夫妇,四人共进午餐。艾和胡适谈了两个半小时,最后将书稿留给了海顿教授。胡适建议使用《中国的文艺BkmhBCNTmAP5BLpqjUyy9pbfLYcvw7EQxXEwbCbqHuk=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作为小册子的书名。
10月5日,胡适为这组演讲写下前言,1934--年5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初版。全书分为六章:一、文化反应的类型;二:抗拒、激赏与新的疑问——中国人之西方文明观念的变迁;三:中国的文艺复兴;四:知识分子的过去与现在;五:中国人生活中的宗教;六:社会的分裂与调整。
十年后,胡适在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同学会又讲演过《中国的文艺复兴》。
三十年后,也就是胡适死后的1963年,Chinese Renaissance由纽约Paragon再次发行。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史学教授HymanKublin在再版新序中回忆了二十五年前,当自己还是波士顿大学的一名学生初读胡适这本仅一百来页的演讲集时,所受到的启发和震动。而今,重读三十年后的第二版,他发现自己当初对胡适学识和历史洞察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
巧合的是,胡适和芝加哥大学同时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校训“益智厚生”的芝加哥大学成为商业黑暗海洋里的一座文明灯塔,她一直耐心地等待着一个在远离父亲的家庭毫无征兆地呱呱落地的东方土地的儿子,按照中国传统育婴方式茁壮成长;等着他倚着植物油灯读完心爱的小说,亲眼看到洋油侵人自己的村庄,目睹商店里的煤气灯因电灯的出现而消失;等着他以安徽绩溪上庄村为起点,乘轿子、坐手推车,手划内河小船,到坐马车、有轨电车和汽笛长鸣的轮船,终于在1910年的某一天来到此邦求学,坐上汽车、火车和飞机,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传播中国文明的学者和文化大使。通过这个优秀中国人追赶的脚步,展现的是两种多彩文明的对接与融合、沟通与理解。
自1891年成立以来,芝加哥大学所授名誉学位甚少。1939年6月13日的毕业典礼上,荣获法学博士名誉学位的仅有一人,这就是胡适。对此荣誉,胡适非常看重,甚至超过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位在心目中的地位。
芝加哥世博会
胡适由交通工具的演变概括出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会标对此有更充分的创意体现。旋转的地球划出充满速度与力量的弧形轨迹,向宇宙发散开去,象征了人类告别“蒸汽时代”,进入‘太空时代”。
正值芝加哥建市一百周年。1886年5月1日,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争取妇女权益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已经是芝加哥第二次举办世博会了,不过,却是第一次有明确主题的世博会——“一个世纪的进步”。它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基调,展示芝加哥的独特魅力和一百年来在工业、科技、文化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包含着欧洲中心结构的“现代”时间意识,历史发展的线性观念,开始被欧洲以外的地区包括中国接受,这就是“进步”。在这个新的时间意识中,“今”和“古”成了对立的价值,“现代”因此意味着一种新的维度,一种新的价值标准。
而城市化是这种进步的集中体现。城市把乡村最优秀的人都吸引过去了,正值花季的男男女女,都去了城里,留下社会地位更低的人耕种土地。来自穷乡僻壤的大规模移民,被迫放弃安慰,切断乡村的根,抛弃有组织的信仰,离开家庭的庇护,被扔进现代都市的大漩涡里。
《嘉莉妹妹》即表现了这样的追求。1889年8月,十八岁的嘉莉妹妹独自一人踏上赴芝加哥的下午班车。“母亲和她吻别,使她涌出一阵热泪,火车轧轧地驶过它父亲白天在那里工作的面粉厂,使她喉头有些哽咽,村里看惯了的绿野在她眼前消逝,使她发出伤心的叹息。而那些把她和少女时代以及故乡轻轻牵住的柔丝,就此无可挽回地给扯断了”。
嘉莉妹妹所乘坐的那辆朝前直冲,向五光十色、熙熙攘攘的大城市芝加哥快速飞奔的火车,恰似懵懂无知中被牵引着追赶世界前进脚步的中国。在演讲《社会的分裂与调整》一章里,胡适谈到了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中国古老生活方式的变迁:
城市始终是变革和进步力量的辐射中心。贸易、工业和教育设施吸引了来自远方的人们。这些人也许永久地住在城市,也许再返回其农村家乡。他们或许自己在商店、工厂里工作而把家人留在乡村,或许带着妻儿一起迁居城市。无论哪种情况,城市文明的影响都是难估量的大。它意味着旧式家庭的解体,意味着脱离家庭和家族的血缘纽带;意味着改变生活和工作习惯,接触新型的社会机构;意味着妇女儿童进入工厂;意味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的苦乐、新的诱惑和新的欲望。
参加世博会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显现。尽管时值日本侵犯热河,华北危机,中国国民政府仍勉力参加了此次世博会。在米歇根河畔的公园世博园区,独立的中国展区坐落在铁塔旁,被命名为“上海街”,占地近四千平方米。有一幢三层的上海老房子,每层有单坡顶,四面飞檐翘角。仿上海龙华塔的翡翠大宝塔,和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街”的南京路商业街,都很受参观者欢迎,参观人数达二百五十万人.占全会参观人数的十分之一。
有一位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复制了热河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的古典建筑,名叫捷荷尔金庙,起先在中国构建,后来拆成二万八千个部件,用船运到芝加哥,然后再重新装配。斯文·赫定将其作为营业性观赏建筑,收门票十美分。大约有六万人参观了这一展现东方风情的喇嘛庙。不过,它与代表进步中国的“上海街”毫无关系。
本届世博会还注重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体现男女平等,谋求种族平等公正,延续高雅艺术,展示异域风光,并进而弘扬美国价值观,这些都体现着组织者对“进步”理念多向度的认识。在芝大演讲的胡适在讲到科学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进步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强势地位,却避而不谈歧视,这在有意无意地配合了同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妇女大会突出女性地位的主题。当国内知识界正大力提倡反对封建束缚,争取妇女解放的新文化潮流时,胡适在美国却用很大篇幅,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中国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强势地位。“女人常常是家庭中的暴君”,胡适认为妻子强有力的地位的获得,有时是靠爱情,有时是靠美貌和人格,但最主要的是凭着这一事实:她不能被赶走,她不能离弃。联想到胡适与江冬秀的包办婚姻中曾出现过以刀相逼的较量,他也是倍感强悍的中国妻性文化吧。胡适曾锐意穷搜若干全球怕老婆的故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跟中国相比”。
胡适的演讲主题与用漆器、瓷器、古玩、土特产精心布置起来的中国馆相得益彰。尽管冠以“复兴”的题目,其实,谈的也是进步——个古老文明七十年来与西方文化汇合碰撞、抗拒再生的过程,他以一贯的冷静态度,从容客观地向西方人展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政治经济制度,乃至古老的生活方式,及其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极尽文化之广博、历史之纵深。一个是纯粹学院派的学理阐释,一个是不乏迎合猎奇心理的商业文化展示模式,二者均在各自的受众群体中激荡起层层涟漪。
此次世博会由5月27日延续至11月27日。7月31日,胡适前去观摩,看来是韦莲司建议他去看的。在8月1日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说:“我一直到昨天才看到那个展览会,从39街走到第12街,我走了八里路,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半。”简单的一句话,看不出半点个人观感。被命名为“上海街”的中国展区位于18街科学馆对面,应该在胡适的观览范围之内。
1933年夏天,“风城”芝加哥吹来阵阵中国风。胡适演说中的中国,西方人想象的中国,中国国民政府为展示自己迎合世界潮流而制造出来的中国,却是各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