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
2011-12-29
休闲读品·天下 2011年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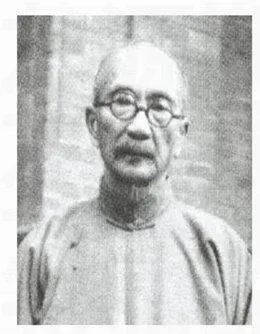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共的政治理念已由“革命”转化为“执政”。与此相伴,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发生了一场悄然而重大的转变:由过去的“革命史叙述”转变为现今蔚为主流的“现代化叙述”,即从过去以是否有利于革命作为评价一切事件与人物是否进步的标准,转变为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价一切事件和人物是否进步的标准。所谓“现代化”不过是“执政”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随着这种“叙述模式”的重大转变,史学界对许多近代人物的的评价也自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在近几年的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人们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冥顽不化的反动保守势力,反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比如兴办近代工业、废除科举、扩大留学、兴办新式教育、实施议会政治等诸多方面,这方面的言论出现得多了,让人们觉得这些人不仅不是反动力量,反而是推进现代化的力量了。这种倾向进一步滋生下去,让一部分人甚至得出了革命不如立宪的“反革命”的结论。
和一切受政治理念影响的史学研究一样,“现代化叙述”也和当年的“革命史叙述”一样,出现了形式化的偏颇,当年不分清红皂白地攻击一切革命的敌人的一切方面,如今,又在不分清红皂白地吹捧一切现代推动人物的一切方面。历史学历来为政治之工具,这已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既然要为政治服务,出现这种与时俱进的叙述转换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革命史叙述”虽然退潮但尚未完全消失、“现代化叙述”虽然炙手可热但尚未到独霸天下的时候,正好给力图以客观的态度探究当时历史真实本相的学者提供了自由研究的空间。本文即是在两种非此即彼的主流史学叙述之外,对袁世凯在近代中国的实质意义所做的一种客观探讨。
1、袁世凯的才干,魅力与政治成就
如果不是后来恢复帝制,袁世凯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完美的人物。他出身于官宦之家,20岁前参加过两次科举乡试,均落榜,于是他将有关科举考试的书付之一炬,放言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耳”,遂弃笔从戎,到其嗣父袁保庆的老战友,淮军宿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手下当兵。
说起来,袁世凯这位“官二代”从其家庭中汲取的全是正面的营养,由于嗣父是军人,他从小便学会了舞枪弄棒、骑马打拳;而且还由于跟着在京城做过刑部侍郎的叔父袁保恒在京城读过书,其见识远比窝在项城乡下的一般青年宽阔。其生父、嗣父均在其还未成年时去世,所以,他也没怎么过锦衣玉食的少爷生活,反而从小就有养家糊口的责任感,他考不上科举,那倒不是因为他没有文才,恰恰相反,他的诗文写得不错,诗中有过这样的句子:“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①气象宏阔,沉郁顿挫。他的奏表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②他的书法也不错,小楷端正平和,行书简牍则写得沉雄劲健。从他的天赋看,考中进士在智力上没问题,之所以考不上,的确是那种考试制度在当时已经完全堕落到束缚人、残害人的状态,他受不了那份逼人弱智的精神折磨。其实,比他更早些,就已经有优秀人物受不了科举折磨而出局的事例了,比如洪秀全、左宗棠。科举制由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变成了残害抑制人才的机制,也是近代历史中应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这里,我们只能说,没有任由科举制的折磨,是袁世凯心智健康的表现。
在吴长庆的军营里,袁世凯不是靠着嗣父的面子吃闲饭的,而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干起来的。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内乱,吴长庆率所部六营兵马奉命入朝平乱,当时23岁的袁世凯只是前敌营务处的一名帮办(相当于作战参谋),负责军需和勘定行军路线。吴长庆命令某营为先锋率先登岸,该营管带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长庆大怒,将该管带当场撤职,命令袁接替;袁世凯接替后,立即部署登陆,很快完成了任务。此后,袁世凯以代理管带的身份,率部向朝鲜京城进发。此时淮军已有暮气,军纪松驰,行军途中竟有士兵对朝鲜民众奸淫烧杀,袁世凯知晓后,一口气杀了七个违纪的士兵,提着违纪士兵的脑袋去见吴长庆。士兵被震慑住了,吴长庆也看到了袁世凯的胆略和手段,由此开始重用他。在朝鲜,袁世凯配合吴长庆将引起动乱的重要人物、朝鲜国王的生父大院君(相当于摄政王)李昰活捉,押解回中国。
此后,袁世凯驻扎在朝鲜,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从他的所作所为看,是个智勇双全、对国家忠肝义胆的人物。他后来能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在李鸿章去世后,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一职,为全国督抚之首,实在是由于其本身过人的才干所致。至于袁世凯后来治军理政的表现,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细节可说,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多赘言。总之,如果从执政借鉴的角度品味袁世凯的治军理政之术,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物,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应该承认,不论按当时的标准,还是现在的标准,袁世凯都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
首先,他是一个敢负责、肯担当的人,他从来不回避责任,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从不诿过于人,凡是和他共过事的人都有这种看法。最明显的例子是恢复帝制失败,让机要局长张一麐为他起草撤销帝制的文件,张一麐一直反对帝制,曾当面向袁世凯提出过自己的意见,所以袁世凯首先向他道歉,说:“我昏聩,不能听你的意见,以致于到了这个地步,现在取消帝制的文件还得由您来起草。”张一麐为了给袁世凯找个台阶下就说:“这件事您是受了小人蒙蔽。”袁世凯反倒说:“不,是我自己不好,做错了事,不能怪罪别人。”③
其次,他是个慧眼识英雄、爱惜人才,使人才能发挥作用的人。不可否认,在晚清官场上贪官庸吏众多的大环境下,袁世凯也和不少无能之辈结为好友,也有搂钱行贿之事,如他与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交往就是如此。但是,他所诚心结交的更多的是那些有才干、有激情、有热血的豪杰人物,这些人很多,政界中有李鸿章、荣禄、张之洞、徐世昌、唐绍仪;军界中有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学界中有严修;商界中有张謇、盛宣怀;科学界中有詹天佑,等等。这些人本身都是有能力、有原则的人,他们与袁世凯的友谊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并不是趋炎附势。当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共同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就真心拥戴袁世凯;而一旦袁背离了大家共同的理想,他们也就会以各种方式反对袁世凯。比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在袁世凯被载沣开缺回家的时候,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一如袁世凯在台上时尊重他,在政治上听取他的意见。可一旦袁世凯倒行逆施时,这些人无不当面表达反对意见,并以或者辞职或者中立等实际行动加以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固然有蔡锷等进步党人反对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嫡系的北洋将领的抵制所致。再比如,唐绍仪这个人物,曾经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处理朝鲜危机时,他亲自佩刀持枪,护送袁世凯脱离险境,可谓是肝胆相照的生死弟兄,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又充当袁世凯方的谈判总代表,全力促成和谈,革命后,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但当袁世凯不遵重《约法》程序,沿袭前清官场人治之陋习、随意行事时,唐绍仪立即宣布辞职,挂冠而去。这些人有原则,也有情谊,当袁世凯死于忧愧之中,原来为反对他称帝而退隐的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反而出山,为他料理后事,修建陵园,尤其是段祺瑞,因为反对帝制而与鼓动帝制最力的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结下了很深的矛盾,以致当他来为袁世凯料理后事时,袁克定还以为是来报仇的。
过去的历史书中均把北洋军队听令于袁世凯解释他用私恩收买下属将士所致,并且无中生有地杜撰出袁世凯在军队中培植对他个人忠诚的故事,比如影响较大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竟然演出了北洋士兵们集体喊操时异口同声地说“吃的是袁大人的饭”的画面,这当然是瞎编乱造,莫说袁世凯没有这种想法,就是有这种想法,在当时也不敢这么做呀!事实上,袁世凯之所以能得到北洋将士的拥护,完全是基于他的政治理念反映了当时进步军人共同的价值观,他的行为风格,赢得了全军将士的敬佩与爱戴。比如在他训练新军时,从不克扣兵饷,发饷时,亲自在操场监督将军饷公平地发放到每位士兵手中。他身先士卒,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和士兵一起出操,风里来,泥里滚。他任人唯贤,几乎没有因某人是家庭亲属和同乡故旧就加重用的。这种人物,放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的军队里,都会得到将士们的真心拥戴。
袁世凯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胸襟宽阔,有海纳百川的雅量,就是对曾经打击过他的政敌,也能公平对待。比如他在小站练兵时,有位御史胡景桂受人唆使,根据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上表参奏袁世凯“克扣军饷,诛戮无辜”,此事经荣禄调查后纯为子虚乌有。后来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这位胡景桂正好在山东按察使任上,是袁世凯的下级,但袁世凯没有挟私报复,在了解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胡景桂此人办事认真,颇有能力,所以,非常重用胡景桂,屡次向朝廷上奏,推荐胡景桂,并派胡景桂到日本考察学务,胡景桂也不负重望,在北洋早期推进新式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比如,摄政王载沣这个曾经想要了袁世凯命的老对头,革命之后,袁世凯对他一直尊重有加,从来没有寻机迫害。
正是因为有上述这么多的优点,袁世凯才得到了当时体制内上上下下的信任和拥戴,他的威信来自自己的信念、努力和人格魅力,人们拥戴他,是因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而他也确实做出了不俗的政绩。
按“现代化”的标准,袁世凯的主要政绩如下:
1、建立现代陆军:将袁世凯称为“中国现代陆军之父”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他将德国陆军的训练和管理体制引入中国,训练建立起了第一支中国现代陆军。他创办了保定军校等一系列专业军事院校,为后来数十年的中国军界培养了军事专业人才,保定军校的学员后来有不少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中都有不少将领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如叶挺和顾祝同就是保定军校的同学。
2、推进近现代实业的发展:最突出的例子是支持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如果没有袁世凯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条铁路早就夭折了。
3、推动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前后,袁世凯联络张之洞等重臣反复上奏,说服慈禧太后同意废除已经存在上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同时提出了可执行的方法,使得这项本来可能激起巨大波澜的改革事业进行得风平浪静。
4、建立新式教育:在袁世凯推动下建立起的新式学校至少有数十所,其中还包括直隶地区最早的女子公学。现在一些有名的大学溯及以往,其创办者就是袁世凯,如天津大学,其前身为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大学;山东大学,其前身为袁世凯创办的山东大学堂。
5、推动君主立宪运动:在清未君主立宪运动中,其实际的最高领袖当是袁世凯,他对上可以和慈禧说得上话,反复劝说君主立宪的好处,对下,以首席督抚的身份,对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和上流士绅有号召和导向作用。
6、劝说清帝逊位:和平解决武昌起义后全国的分裂局面,推动清帝逊位和南方的革命党人互为表里,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无疑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功绩,倘若他的立场发生动摇,那么国家很可能当时就陷入持久的内战之中。
2、袁世凯为什么要恢复帝制
袁世凯生平最大的政治错误是恢复帝制,这个错误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几乎抵销了他所有的功绩和美德。
他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呢?笔者觉得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现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缺少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理念;二是他自身传统的文化基因(即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谋利的念头)顽强地发生了作用。
现在有些研究者称袁世凯是位君主立宪主义者,对君主立宪制度的信念是他恢复帝制的重要原因。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夸大了袁世凯对某种政治制度的执着,与事实不符。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不仅不是一位君主立宪主义者,而且也不是其它什么任何主义者,他只是一位实用主义者。
没错儿,他确实接受了很新的思想,推动了很多新的现代化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些新鲜事物怀有深刻的信念。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事情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而恰巧又有其它国家成功的做法可以借鉴时所采取的适应性选择。也就是说,他能创办很多具有现代色彩的新生事物,并不是因为他内心中产生了与这些新生事物相匹配的理念,而是因为这些新生事物可以化解眼前所遇到的危机。和慈禧太后一样,他有着对时代潮流的敏感,具有与时俱进的应变能力。但他毕竟是体制内的成功者,他没有跳出体制、深刻理解并创造一种新潮流的能力,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管他做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但始终只是现代化的追随者,而不是引领者;当现代化的实践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后,他就变成了保守者、反动者。
从袁世凯的个性及人生经验来看,他对任何形式化的政治制度都没有执着的信念,他本来就是旧制度的叛逆者:反叛科举,靠军功进身。在他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充分领略了“制度”是什么东西。在他看来,一切制度都是表面的形式,都是幌子,关键在于当政的人想怎么干。所以,在旧的制度中,他不太尊重制度,甚至可以说,他的一切成就,都是不尊重制度才创造出来的。什么废除科举制、推行君主立宪制等等“制度创新”,他觉得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换汤不换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之所以能接受革命党人的要求,接受共和制,也是出于这种心理,在他看来,什么共和制与君主制都不重要,关键是在于谁掌权,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如果不搞共和制,他也没有由头掌握最高权力;只有搞共和制,才能给清帝退位找到公众认可的理由,才能改变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者。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化的制度符号,居然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他是权力体系内部的成功者,熟稔权力的实际运行规则,在他看来,一切权力体系的核心实质是最后总要有一个人拍板说了算、别人服从这个人,只要有这种决策与服从的权力关系存在,是叫君主制,还是叫共和制原本没什么差别。
在他做大臣的时候,还有个“国家”的概念,因为那时的最高执政者不是他,是满清皇帝,他还有一种为“公家”打工的概念,知道“国家”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公家”的,所以,他能以一种“公天下”的心态与人共事。但是,当他登上权力的最高峰时,他的观念变了,他认为这时国家已经是他自己的了,既然是他的,那就和他一切的私有财产一样,可以任由他决定了。这时,一位中国地主根深蒂固的自私观念发生了作用,他要把国家像自己家的土地一样,传给自己的儿子,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恢复帝制才能做到,于是,他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有些人将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原因归结为他那位想当皇帝的儿子袁克定的撺掇,也有人将其恢复帝制的原因归结为列强的怂恿。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袁克定确实很热衷于帝制,这样,他就有机会登上权力的最高峰;而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一切能使这个国家发生动荡的举措,只有那样,他们才有火中取栗的机会。
但是,归根到底,这些事情只是外因,最根本的内因还是袁世凯自己想做皇帝,想把最高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常从事外交工作,洞悉列强各国的真实动机,对那些外交代表说的话,从来都不当真,只是在想利用时,援引一些洋人有利于自己恢复帝制的言论而已。对于自己儿子的动机,他其实也不太考虑,他的二儿子袁克文就明确反对他称帝,他为什么不听?与其说是袁克定想当皇帝,还不如说是袁世凯教唆袁克定努力去争当皇帝,这样才不负他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感。现在有个词儿叫“坑爹”,说的是有些“官二代”或“富二代”胡作非为,最终连累了他那成功的老子之事。其实,根本不存在“坑爹”的事儿,只有“坑儿子”的事儿。因为在爹与儿子之间,占据主动地位的是爹,儿子最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更多地取决于爹从其出生直到长大成人这一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如果一位爹从孩子一生下来就宠他、惯他,任由其胡作非为,甚至给其创造胡作非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袁克定所犯的错误,也是袁世凯给设计出来的。袁世凯所犯的错误和今天那些骄纵自己子女的“成功人士”一样,没有差别。
袁世凯是位思想开放的人,他接受了很多新生事物,有很多现代的理念;他是外交官出身,了解世界大势,对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制度等外来文明,没有知识上的缺陷。但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与自己多年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知交旧部决裂,强行恢复帝制,那实在是因为他生命中最本真的天性发生了作用。在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中,是对外界压力适应的动机强大些,还是出自内心本能的动机强大些?毫无疑问,其内心本能的动机要更强大、更持久、更无所不在,只要外界压力稍微减缓,他就很容易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做出跟自己此前适应外界的行为完全相反的行为了。
袁世凯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地主,在他的生命本能中,最强烈的欲望以及最强烈的责任感就是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大片令人骄傲的家业。④在他的价值体系中,最高境界就是皇帝,他向皇帝叩了一辈子的头、下了一辈子的跪,从内心深处对这个位子顶礼膜拜。在辛亥事变之前,他是没有觊觎这个位子,但当他当上大总统后,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坐到这个位子时,其内心深处的冲动便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这才是他的“本我”、“真我”,过去他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只是一个“他我”,即不是按他本人心愿,而是按外界强加的标准而表现出的“自我”:在世界潮流压力下力图维新自求的“我”、在皇帝宝座压力下俯首称臣的“我”。如今,这一切外在的压力骤然减轻,他该实现真正的、按自己内心意愿定义的自我了,于是,他便不顾一切地恢复帝制,因为他认为他能克服这一切阻力。
3、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
袁世凯的错误不只是他个人的错误,也不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而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错误,是延续到今天一直存在的错误。而且,更严重的是,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在内心深处不以为这是一个错误。比如,袁世凯的错误说到底不过是把自己挣下的家产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了嘛!这有什么错?如今那些开公司的,不是也想把家业传给子孙后代吗?那些在政府里做工的,不也想把自己的子女弄成公务员吗?这些人之常情,人之天性,难道是错的吗?是错的!在中国古代,在农业社会,这些观念不是错的,因为它们适合那种生产方式,不会面临外来文明毁灭性的压力;但在工业化的现代,就是错的,因为它们无法建立起适应工业化(包括后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组织形式,无法将这一切现代化的形式按照现代化的内在精神运转。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开始逐步学习、接受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有学者将这个学习过程描述为从器物、制度、义理三个层面逐渐深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这三个层确实呈现出某种逐渐深化的递进关系。所谓“器物”,就是现代企业、现代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现代的武器和军队等物质性的东西;所谓“制度”,就是从经济管理到政治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如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等;所谓“义理”,就是指各种“主义”思想。近百年来,几乎没有哪一个流派的西方思想家被中国人遗漏了,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萨特、韦伯这些人的名字和著作充斥了中国的大学课堂、图书馆,乃至娱乐版的街头小报、网络社区。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对现代化的接受与认识是越来越深刻的。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还有做人的基本天良,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均是表面文章,所谓“器物、制度、义理”在中国只是同一水平的横向漫延,根本没有纵深性的递进深入关系,所谓“现代化”的深化过程只是某些学者在主观幻想中描述出的不存在的“模型”。真实的情况是,随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对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学说的引进,中国出自其先天心理本能的那些观念也逐渐找到了在新形式下获得实现的方式,用现代作家王朔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什么主义到了中国都成了聚敛财富的借口还堂而皇之。”⑤
由于大多数人怀有一颗和袁世凯一样的心灵(而且不幸地是还都没有袁世凯的本事和人格魅力),导致中国的现代化状态呈现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在日益完整的现代化物质、制度和观念的外壳之下,活跃着大多数怀有传统中国地主理想的中国人,正按着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把这个现代化的外壳弄得腐朽瘫痪!
这种现象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假晶现象”。“文化假晶”概念借用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斯宾格勒在比较世界诸文化形态时,借用了矿物学上的一个术语“假晶”来描述在文化交流冲突中,某一族群在其它外来文化的压力下,被迫采取适应性行为,逐渐扭曲自己原来的心理本能,接受外来文明的外壳,而其真实的心灵又与这种外壳相抵触的情况。在矿物学上,岩层中常常掩埋着矿石的结晶体,由于水流的冲刷,这些结晶内部出现了空洞,后来由于火山爆发造成的熔岩注入到这些结晶体的空洞中,然后再依次凝聚、结晶,从而形成一种新结晶体:其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互抵触的结晶体,明明是一种岩石,却表现出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这种岩石已不同于其最初的结晶体了,但还呈现出其最初成为晶体时的外貌,因而被称为“假晶”。⑥斯宾格勒认为这个概念可以贴切地反映一个族群在适应外来文明压力下产生的文明变形状态,在他看来,阿拉伯文化、俄罗斯文化都是“文化假晶”现象之一种。他认为,从1703年圣彼得堡建造时起,俄罗斯文化中的“假晶现象”就开始出现了,外来文明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先是巴洛克的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躯壳。
笔者以为,文化的“假晶”现象,不只存在于阿拉伯文化和俄罗斯文化,而是存在于一切面临新的强大文化压力下的国家和民族中。中国的现代化也出了这种假晶现象,就是原始的中国地主式的心灵,被迫一次次地装入和自己心灵本质不相同的躯壳中:先是装入君主立宪的躯壳之中,然后依次装入民主共和、国民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躯壳之中。而在这些躯壳下面,是无数真实的传统中国心灵顽强地实现自己的意志冲动,这种冲动构成了绝大多数人行为的实际动机,使得这个国家的实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与其制度化的外壳截然不同。
现代化对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上个世纪优秀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有过一个清晰准确的表达:“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⑦比他更早一些的陈独秀用更为简练的两个词概括出来,就是:民主与科学。所谓“民主”就是能否建立起一整套不同于过去基于家庭血缘宗法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并稳定有效地运行,实现一个现代国家一切应有的职能;所谓“科学”就是要有一大批人出于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去从事科学事业,并有独立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
对照上述标准,我们离表里如一的现代化状态尚很遥远。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中国的行政系统还只有依靠高度集中的强制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正常运转,而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要求不是其在公民自治基础上的有限性和基于法律基础上的规范性,而是其迅速铲除社会不公、打击一切危害人民生活安全的邪恶行为的高效性。更为直白地说,人民需要一个正确的、廉洁的、有道德的、无所不能的、强有力的高效政府,而不是一个在人民自我约束和高度自治下,职能与权力严重被限制、缩小的政府。人民缺少依法自我管理的意识与能力是西方式政治制度无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最本质的原因。很多学者顺应没有权力的大众口味,将中国没有彻底实现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某些高官和执政集团,认为是这些人的自私自利才阻碍了民主化的真正发展,这是严重背离事实真相的观点。事实上,几乎每个中国平常百姓家庭中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公务员,到政府当官,有了权力后好给自己和家里人办事。如果一个普遍百姓人家的孩子做了官,不为自己的亲属办事(这些事儿绝大多数是违法违纪的),这个人就没法面对自己的父母亲戚,在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下,无论是什么君主立宪、人民代表大会、议会选举制等等,在实际运行上,均如同古代官场一样。
在科学方面,尽管已经建立起大学和科学院,但涌入这些机构的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和兴趣,而是为了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体面的生活待遇。所以,在这些最需要有主动探索精神的地方,几乎见不到任何科研的主动性,国家只能以项目资金等经济和行政手段硬拉着这些人去做那些他们也未必有什么兴趣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中国所谓科学进步只是技术进步,即只是对别人发现的科学原理的学习和应用,而几乎没有从本质上创新的能力。衡量科学家们的工作标准由于科学界本身的无能,只好由行政干部来制定,而且是那种管农民工的可视化标准:干出一个确定的活儿给多少钱,犹如挖一立米土方给多少钱一样。
最为糟糕的是,所谓知识界们还按其先天的思维本性提出一系列“现代观念”,用这种实质上完全是中国式经验思维传统的所谓“现代理念”来诱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更为严重的“文化假晶”现象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制度决定论”,把一切罪恶全推到体制上去,动辄就鼓吹极端的更换制度的主张,好像只要外在的制度一换,人们的精神实质也就会随之而变一样。造成了这样一种恶劣的精神生态:凡事全归结到制度上,凡事都归结到当官的头上,反正老百姓天生没错,什么责任也不用负,什么心理也不用改,只要国家再按照他们这些知识界的精英的想法再换一次制度,比如换成美国那样的民主制度就一了百了、变得一切美好起来。这种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肤浅观念实际上是来自中国传统的经验理性的思维方式: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究其内在原因。实际情况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已经革了数次命,换了数次制度,可是问题还是老问题,从来没有根本解决它。
4、结论:如何走出“袁世凯”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袁世凯现象”是中国现代化中“文化假晶”现象中的突出例证,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彻底“走出袁世凯”
袁世凯恢复帝制不是简单的文化复辟、“开历史的倒车”的问题,而是真实原始的中国灵魂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压力做出的自我防卫、自我坚持的反应。这种灵魂不仅袁世凯有,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也有,正是因为这种灵魂的存在,导致了中国现代化之外壳与内在灵魂相矛盾的“文化假晶”现象。
2、现代化中的“文化假晶”是很多继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革命不断的重要原因
除了西欧、美国等少数原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被动的适应性行为,即继发外生型国家。但由于其原始本土文明(即本地人真正内在的思维方式)的抵抗,出现了在形式上接受现代化的躯壳,而在实质上仍按传统规则行事的“文化假晶”现象,所以显得现代化总是不彻底,总是落后,赶不上发达国家。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不断发生革命,试图通过换人、换制度的方法来实现真正彻底的现代化。可是,由于任何政治革命不可能把全体人民的心灵更换一遍,每次革命都不能根本解决这种“文化假晶”,所以,又会引发新的革命。
3、不能把外在的东西当作内在的东西
从“文化假晶”现象入手,我们应该明白,不能把生产技术、政治制度,乃至观念符号这些外在的东西当作现代化的实质内核,要明白,仅有这些外壳是不够的,对于建立起这些现代化外壳的人我们应给予清醒的认识,比如袁世凯,他接受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外壳,而没有建起一个有内在灵魂的现代化世界来。
4、放弃对“制度决定论”的盲目崇拜
制度也是外在性的东西,任何一种制度,能解决的问题十分有限,但它所能提供的解决问题的空间是无限的。比如,君主制可以通过立宪改造变为一种民主政治制度,而民选制度也可以通过某种技术手段运用,变成独裁者随心所欲的专制制度。因此,不能对任何制度模式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现代化所需要的一切是可以在任何现存制度框架内实现的。而且,前面我们说过,革命解决不了全体人民更换灵魂的问题,革命只能解决是由哪些少数人当政的问题,现代化中的“文化假晶”问题只能在和平稳定的时期,用其它手段稳步而坚实地逐一解决。
5、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解决“文化假晶”问题,是成本最低、最现实的现代化途径
中华民族正面临一百多年以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政治大局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完全有可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解决现代化中的“文化假晶”问题。
现在一谈改革,特别是深层次的改革,人们就会联想到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联想到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问题,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是,只有中国完全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观念,它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某种现代制度的推崇和学习,而究其精神实质,乃是中国传统的经验思维和权力崇拜心理的产物。说它是“权力崇拜”,是因为这种观念认为解决了权力分配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和传统中国人认为换一个好皇帝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一样,只不过持这种论点的人认为现在的官员不好,按新规则换上去一批好的官员就可以搞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新规则中,自己的那一票投票权还能起点作用。这些人不明白,很多事情是权力解决不了的,而且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对权力范围的极大缩小与限制,如果中国真出现这样一个缩小了的权力,那就会出现无人管理的社会真空,就会产生更多的混乱与无序,更没有条件去解决真正的现代化的深层次的问题——人民灵魂的改造。说这种观念是经验思维的产物,是因为它只看到了制度这种外在的东西,回避支撑制度,使制度正常运行的内在的灵魂。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解决“文化假晶”问题,彻底走出袁世凯呢?
具体路径很多:教育改革、制度创新等等,不一尽述。对于这些技术性的路径,日后我们还可以做专门的讨论,这里只是提出“走出袁世凯”的标准:
1、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父母,再不要求自己的子孙当官发财给自己家里办事,中国人不再蜂拥而至考公务员,政府公务员招聘如同一个小饭馆招聘店面经理一样普通寻常,再也没有爷爷奶奶为了让孙子、孙女上个好幼儿园、“不输在起跑线上”抱着铺盖卷,在某名牌幼儿园前通宵排队的现象,中国就现代化了。而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学者们不再去讨论那种饮鸩止渴的“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愚蠢问题,而努力去砸烂形成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体制,创造出“同质化”的教育。
2、社会有那么一种能力:能识别出什么人是为了挣钱过好日子去读书做研究的,什么人是出于兴趣和爱好才去搞科学研究,并对后一种人提供实质性的工作条件的话,中国的科学才有希望。Ω
◎淮军宿将——吴长庆
吴长庆(1829-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县南乡沙湖山人。1880年,吴长庆升浙江提督。10月,调任广东水师提督,未赴任。清廷命吴长庆帮办山东军务,吴长庆率所部屯驻登州。因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结拜兄弟,故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奔吴长庆,后因袁世凯表现突出,任“庆军”营务处会办,袁世凯的军事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唐绍仪
唐绍仪(1862-1938),汉族,又名绍怡,字少川,1862年生于广东珠海唐家镇唐家村,自幼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881年归国。曾任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为中国主权、外交权益及推进民主共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当时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建立友谊,在政治上给予了袁世凯很多帮助。
↑◎袁世凯的书法
这是袁世凯的一封小楷信札,用笔熟练准确,无一丝懈怠,结构平整端正,自然华丽。袁世凯在朝中为官多年,常年写奏折的功底在这里表露无疑,人们常说字如其人,如此规范、隽秀的小楷,张弛有度,能看出一个人的控制能力;有纵有横,自成一格,毫不拘泥,能看出一个人的灵活多变。
↑◎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
照片中的袁世凯身着军人礼服,佩戴多枚勋章,目视远方。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1878-1958),字云台,别号慧能居士,袁世凯原配于氏所生。辛亥革命爆发后,拉拢汪精卫,后鼓吹帝制,帮助父亲袁世凯复辟。袁世凯死后,袁克定迁居天津隐居。曾任开滦矿务总局督办。1958年,袁克定在张伯驹家中去世,时年81岁。
◎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原籍浙江慈溪,严范孙先生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他倡导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在这一点上,袁世凯与严修的意志是相同的,于是1904年正奋力推进“新政”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恳请严修出任直省学校司(后改称学务处)督办,创办新学。袁氏尝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严修此次也是当仁不让,毫无推脱之意,慨然应允。不论政局如何,严修先生一直为中国的现代化教育,奉献着毕生的心力。1919年,与张伯苓一道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增办南开女中,1928年增办南开小学,被尊称为“南开校父”。
◎张謇
张謇(1853-1926),1926年8月24日生于江苏海门市长乐镇(即今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1876年夏,张謇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庆军幕任文书,后与袁世凯两人成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此举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断绝了一切来往。
深度阅读推荐
1、赵焰著《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这是由安徽作家赵焰撰写的一本袁世凯传记,文字生动,传神地反映出了袁世凯跌宕起伏的一生,没有过去的脸谱化作法,态度严谨且客观,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2、候宜杰著《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本书为历史学家候宜杰先生约在十年前的作品,史料较为详尽,立论尽量公允,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袁世凯的生平事迹。但某些语言还流露出当年对袁世凯批判时留下的痕迹,与赵焰先生的著作对照阅读,不仅可以在史料上互为补充,亦能看出近十年关于袁世凯研究的思想变化脉络。
3、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此书为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所著,唐先生为著名口述史学家,整理过《李宗仁回忆录》等,与民国故旧有亲身的交往,兼之留学美国受西方史学理论影响较深,所以,其著作既有口语般的易读性,又不失理论上之深刻。他对袁世凯之当政及称帝的历史原因有较深入的分析。
4、王忠和著《项城袁氏家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此书是袁世凯的家族传记,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袁世凯的远祖、曾祖、祖父、父亲(包括生父、嗣父)、叔父,袁世凯本人及其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的传记,对于了解这个家族很有帮助。
5、张华腾著《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中华书局,2009年4月第一版。
本书全面介绍袁世凯赖以起家的北洋政治集团的发展过程及形成原因。作为政治领袖,袁世凯不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才获得其历史影响的,故理解这个政治集团成员的思想与活动,对理解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行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