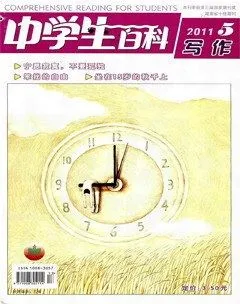色盲之死
2011-12-29马正心
中学生百科·小文艺 2011年5期
中学生也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吗?它是一种凌厉的青春,与人相遇,却无法与人相处,暴露残酷的诗意,与伪装的温柔决绝。
把枪支小心地摆放在窗台上,用一块略脏的抹布包着,他写道:“让我恐惧的不是永恒的光明,也不是阳光,而是藏青色的黑暗。”其实这不是他想写下的,他想写的是:“恐惧永存留在我心间。”
这种充满希望又流于绝望的经历的开始,源于他的出生:产房里摆着一株绿色的盆栽。如果说这是他见过的唯一的绿色,那么他出生时妈妈流出的大量血液,就是他见过的唯一的红色。
但是他是否真的看见了这两样东西,甚至说看见这两种东西时有没有看见它们的颜色,都难以确定。这么多年之后,出生成了一个符号,对于他来说是光秃秃的,像他在生命中最后五年拥有的发亮的头顶。这头顶上有道疤痕,在右上方。他出生后不久,护士试着把他抱出产房。他剧烈地反抗,坚决地用四肢把护士推开。这种行为没有效果,但让刚工作没多久的护士双手一阵又一阵地震动。终于,他从颤抖的怀抱中掉了出来,头重重地磕在了桌角:这让他成为一个红绿色盲。
这样的特质适宜上战场,他也确实去当了兵。失去了对红色血液这最直观的、战争恐怖的象征的感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屠夫。(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他杀死的不是一个个血肉分明的生命,而是一分分变为快乐和理性的可能性。)在他经历的第一场冲锋中,子弹从他的枪里飞出。他有着这样的幻觉:这是和平年代,他站在家的角落,耳朵里是《夜后咏叹调》,但眼睛却怎么也离不开厨房里的外婆。她在高于他视平线的地方,从纸袋里拿出了三四个柠檬,把它们洗净、擦干,用一个特制的钳子用力一夹,深黄色的柠檬汁伴随着难以忍受的尖锐的噪音,温顺地流进了低处的一个大碗里。残留的柠檬渣滓被扔进垃圾桶。他看着她这么做着,浑身发抖。这时《夜后咏叹调》唱道:“要抛弃,要分离,断绝关系。”这种幻觉让他浑身难受。他端起的枪喷出炽热的火焰,血液在战场上飞溅:他的战争是柠檬汁与榨汁机的战争。
在所有的尸体被埋起之后,战争结束了。大街空得能容得下一只恐龙,而每天日落时分,所有的狗依然要不停地叫上两个钟头。在这座城市和所有的城市里,公平、和平又被建立起来。因为他幸存了,也因为他让许多人不能幸存,他成了一名英雄。但在没有了炮火声的头几个晚上,他难以入眠。战争并未给他带来视觉上永恒的记忆,他记得的只是巨响中穿插着难以忍受的、尖锐的噪音。现在这份宁静让他感到羞愧,他亲手建成的世界,却是他不配拥有的。
立场与下场的矛盾,让他自发而自愿地成了一名艺术家。他偏爱视觉艺术,憎恨文学。这十年当中,他画了十三幅画,有大有小。起初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但那栋洁白的、巨大的别墅只有一个中年男人居住,多少让街坊邻居有些诧异。渐渐地,他的访客多了起来,大多是不请自来。他们手里捧着暖壶,仔细地看着散落在画室四周的画作:那些线条绝无停滞,往往一笔从画布的顶端开始,把整块画布劈成两半。他使用的颜色不属于战争,也不属于和平,像一个工作得并不和谐的收音机,游离于两种不同的不真实之间。不同的访客在画里找到不同的痕迹:访客一号在画一号的右下方找到了火焰炙烤的痕迹;访客二号在画四号的中央发现了淡淡的水渍。终于,这些或主观或客观的艺术家访客,把在白色别墅里作画的中年男人的消息传了出去,他的画作不再陈列在画室里,跟着其他的作品流浪在整个战火平息的世界。有这么一群人相信,这些颜料的拼贴、斧凿的痕迹能够给人带来内心的平和。他对这种看法保持中立态度的同时,在每个仍然难以入眠的夜晚,想念着流浪在外的他的画:他的十三个儿子。
没有人热爱那些“线条简单,颜色古怪”的画作。他的儿子们在半年之后回了家,这次他把他们堆放在花园里,与鸟儿、花朵为伍。那花园总是充满了声音,是这栋大房子里拥有生机的地方。他停止了画画。
日子飞过去,他没有一种有效的方式记录——没有钟表也没有日历,只从偶尔手脚拍打出的节拍里体会时间的流逝。时间像一个赤裸的新娘摊在他的床铺上,但这么多年他从不在意。
不知道是哪一天的哪一点钟,反正是太阳正在花园顶端的时刻,他打算出去走走。早已与他的家熟识的邻居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了,他是社区里的陌生人。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双手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摆放,既为了能被人见到、能见到人们而感到欣喜,又无法控制地觉得难过。他想起小时候出门赶集的日子,他的手被一只大手牵着,或者整个人被放在宽阔的肩膀之上。想到这一点,他失去了平衡,栽倒在泥地上。
后来,接近日落的时刻,他被狗的叫声唤醒,支撑着爬起来,掸净身上的泥土,从来时的路往回走。这种散步的习惯渐渐养成了,间或有暴风雨雪的日子,他就坐在写字桌前,回想着那条一成不变的路。
终于有一天走回来时,有人拦住了他。这是在桥上,那个长头发的女子没有把头发盘起,任由它们松垮地披在脸上。她看着他一语不发,他为受到了阻拦而感到意外,做了个手势请她让开。她战栗着让开了路,一只手却紧紧地拽在他的白衫上。回到家之后,花园成了她热爱的地方。她从树上找到鸟儿爱吃的东西,放在手心里,等着它们从天上飞下来啄食。他又被禁锢在了家里,仿佛一离开,这房子就不再属于他了,而属于这个难过的用头发挡住了眼睛的女人。他孩子气地待在大卧室里,不去看她也不离开。直到有一年的春天,竟没有一声鸟叫。他奇怪地来到花园,看到长头发的女人安静地躺在地面,大约四百只鸟儿聚集在她的身边,用爪子温柔地抓着她的衣服,用力地拍打翅膀。当她离开了地面,更多的鸟儿飞来了,从下面托着她。他看着她越升越高,越升越高,离开了这个花园和他的家,心里觉得十分安全。
再后来,他的画突然在全世界受到追捧。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人来到他的家里,礼貌地要求买下他的画,越快越好。无数的艺术组织争着给他颁各式各样的奖——有些是金色的杯子,有些是盘子,还有些是一张写满字盖满章的厚纸——以表彰他对艺术本身的杰出贡献。他不再是一个战争英雄,而是无数个荣誉会员,无数个荣誉教授。他不以为然。
长发女人飞走之后十年,他的头发凋谢了,那个使他成为色盲的伤疤又露了出来。他常常做噩梦,梦到一条黄色的溪流在流淌,而他身陷其中,醒来之后却忘得一干二净。某一日,他往花园里扔了一根火柴——那里已经好久没有鸟儿光顾。画燃烧了起来,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四周的花木也遭殃了。空气里布满了松节油的气味。他相信这样做能驱赶掉这个梦魔,结果也确实有效。
最后的最后,一个年轻的色盲来拜访他。他单膝跪在他面前,毫不停顿地说着对他的仰慕。从他的话里,似乎他真的能理解他。年轻色盲的脸上泛着光,眼睛因为紧张和激动而不停地眨着,身体前后摇晃不断。可他并没有认真听。他躺在他的大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一个黑色的洞。后来,他听得厌烦了,就从床头柜的下层掏出一把手枪,把他射杀了。他胸口的伤口冒着烟,黄色的小溪从里面流淌出来,在地毯上无力地流着,停留在某处。
枪声惊起了在屋顶筑巢已久的鸟儿和警察,远处树林里的鸟儿也在稍后飞起。
他厌烦地叹了一口气,把枪支用一块抹布擦净,小心地放在窗台上。他在写字台前坐下,拿出了一卷羊皮纸和小时候曾使用过的一支好笔。他轻轻把羊皮纸铺平,把笔吸满墨水,认真地写字。他写道:“让我恐惧的不是永恒的光明,也不是阳光,而是藏青色的黑暗。”
编辑/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