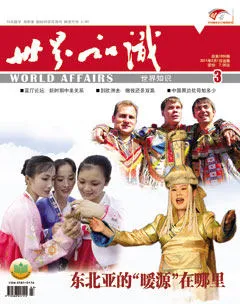边界谈判与国际法则
2011-12-29李清元
世界知识 2011年3期
“老一辈革命家对国际法事务非常重视”
以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国际法事务非常重视。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任命著名国际法专家周鲠生、刘泽荣、涂允檀和梅汝墩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法律顾问,凌其翰、倪征噢、李浩培为委员。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改制为外交部条法司后,继续在位于北京外交部街的清朝总理衙门旧址北楼二楼办公。当时,周总理每年在外交部举办由各司司长参加的宴会时,都特别邀请条法司专家共同赴宴,并与他一起坐在主桌。此外,周恩来和陈毅同志担任外长期间,多次专程到条法司视察,并就有关事务咨询顾问专家的意见,体现了中央领导对国际法事务的重视。
“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条法司曾先后并入礼宾司、领事司和国际司,但因其承担工作的重要性与专业性而最终得以恢复独立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加入了众多国际组织,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参与国际事务越来越频繁,这个大背景使国际法事务在我国外交工作中也越来越重要。
边界问题是国际法的重要内容
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就是国际法。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本身就是制定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的过程;国际法的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也贯穿在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
国界就是国家的界限。领土即是国家范围线以内的领陆、领水、领空等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是构成国家的最基本要素。国家边界的确定与国际法密不可分,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土的性质、划分原则及取得方式等问题都与国际法密切相关。国际法是国家处理对外事务,尤其是与邻国处理边界纠纷的主要依据。
我国建国初期根据国际法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
我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历史上有条约的以条约为依据,历史上没有条约的根据传统习惯加以解决;在解决边界问题之前,保持边界现状;解决边界问题的目的并非谋求获取邻国的土地,而是为了实现中国与邻国边界地区的长治久安。
1 历史上与邻国签订有条约的,以条约为依据
清朝政府在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或类似性质的法律文件中曾规定了与当今俄罗斯、越南、老挝、蒙古等国的边界,这成为新中国与这些邻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历史依据。
受到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局限,历史上签订的边界条约所规定的边界与实际边界状况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中俄边界条约中有如下表述:“山高路遥、人迹罕至,遂遥指天山中梁为界。”这种模糊性的规定既是由于中苏西段边界属高原地貌,交通不便且空气稀薄,两国谈判官员无法亲临实地造成的,也是由于当时地理知识并未成熟,尚未出现“主航道中心线、山脊或分水岭”等专业性概念造成的。这种由技术条件造成的勘界困难的情况在建国后也曾出现,如在中尼边界勘界过程中,双方外交代表都难以登上喜马拉雅山顶亲自查看边界实际情况,只能先派出其他工作人员到边界进行拍摄录影,再向外交代表做出汇报。
再如,中俄历史上签订的有关东段边界的条约文本规定:“中俄边界以额尔古纳河一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以现代国际法的眼光来看,这个表述没有说清楚以江的什么位置为界,江心岛屿如何确定归属等问题,存在很多漏洞。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大多只重视航行利益,还没有认识到江湖作为国家的“绿色国土”所具有的渔业、能源等经济价值。这些由历史条件造成的局限性,都是以上条约文本表述不确切的重要原因。
但客观地讲,历史上签订的边界条约,虽不精确但价值重大,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能对边界划分规定到如此程度已无可指责。
值得强调的是,历史上中国参与签订的边界条约很多是不平等条约。例如,中俄历次边界条约中,除《尼布楚条约》外均是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时期的外长王世杰与苏联外RU7gW+cyxq8lfN6sFv6PPg==长奠洛托夫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中,被迫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建国后有人认为,应暂时搁置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谈判,待国力强大后再解决边界问题。这些意见虽源自拳拳爱国之心,但显然是与国际法相关原则相悖的。根据国际法对政府继承的有关规定,新政权有义务接受、承认相关边界条约。而依靠武力解决边界纠纷的方式,在二战后已经不被各国所承认。
因此,在建国前夕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这个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国民政府继承的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有关条约。其中,巾国历史上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属于被“承认”的范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历史上签订的有关边界问题的法律文件。依照这个原则,在中苏边界谈判之初,中国就表示愿意以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为谈判基础;戈尔巴乔夫访华时,邓小平同志再次表明了这个立场。
2 历史上与邻国未签订过条约的,以传统习惯为依据
国际法规定,对于历史上无条约依据的边界划定以传统习惯为依据,遵循“实际管辖”的原则。实际管辖涉及有效的防务、司法、行政管理等内容。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实际管辖范围问题,内地及东南沿海地区相对明确,新疆地区在中俄有关边界条约中也规定得比较清楚,而西南地区则相对复杂。
西藏、云南等地,历史上长期被分割成众多“头人”的领地,由于某区域的头人经常发生更换,使确定该地的历史管辖归属非常困难。这些地区在建国前后大多仍处于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时期,确定其历史归属自然也应遵照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传统习惯。这主要包括四个要素:行政区划设置、防务、劳役及赋税。因此,在新中国与西南部邻国进行边界谈判的过程中,诸如当地居民向头人缴纳赋税的票据、服行劳役的记录等都成为重要的历史管辖确认依据。
又如南海问题。尽管上世纪80年代后才生效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对领海划分、岛屿主权归属等问题作出了详尽规定,但是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权利是历史性的权利,是遵循无主地先占原则取得的。因此,我们将“南海历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作为拥有对南海主权的基本理由。封建社会时期,国家在无主地上“插旗放炮、公开宣示”并实现“较长时间无异议占领”即可被视作对这块无主地获得了主权。我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获得便是源自这种方式。
边界谈判中的地名问题
地名是国家订立边界条约文本的要素之一,如果谈判双方对某地称呼方式不一致,便容易造成对边界描述的混乱。
以中苏边界谈判为例,双方曾就海兰泡(苏方称布拉戈维申斯克)这一地名产生分歧。海兰泡地区历史上曾是中国领土,沙皇俄国在扩张过程中占为己有,并重新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俄语命名。在边界谈判中,中方坚持要求在交换标有主张线的地图上使用“海兰泡”这一名称,而苏方则要求使用“布拉戈维申斯克”这一名称。苏方认为,该地区已经成为苏联领土,自然应遵照苏联的命名方式,这符合联合国地名委员会提出的“名从主人”的原则。中方代表则提出,由于该地区历史上是中国领土,“海兰泡”这一称呼已经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民众的惯用称呼,苏方应该对中国民众的习惯予以尊重;俄国原本就是通过侵略扩张的方式获得了这片土地,中方已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苏联应照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苏方代表原本担心中国翻历史旧账,因此在中国代表的据理力争下,最终同意采取同时保留双方称谓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即双方同意在共同勘界图与双边条约中出现该地名时,在苏方称谓后加注括号写入中方称谓。同样,对海参崴、庙街等地名也采取了同样方式。
类似的事例还有中尼两国边界谈判中对珠穆朗玛峰称谓问题的处理方式。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尼方称其为萨迦玛塔峰。珠峰是中尼两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山”,具有独特的地位,对其称谓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两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最终,两国同意采取各自命名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在珠峰南麓注出萨迦玛塔、北麓注出珠穆朗玛,但指同一个山峰。
其实,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边境地区的称谓问题。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开始前,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国内地图统一国界线画法、建议对地名进行统一”的通知,以体现中国政府对地名问题的重视和对谈判的诚意。另外,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外交家十分重视废除历史上形成的带有侮辱性的边境地区地名或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地名。例如,我国分别将安东改称丹东、将迪化改称乌鲁木齐、将镇南关先后改称睦南关和友谊关。
国际法知识是外交官的重要“拐杖”
条法司的工作专业性很强,从语言、地理、测绘到国际法、国际关系,各种知识都不可缺少。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际法知识是外交官开展工作要借助的重要“拐杖”。国际法是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外交官的工作更应该以国际法作为重要的行为准则。同时,划界谈判的工作更离不开国际法的相关知识,掌握了国际法的相关知识无疑会便于确定争议领土,从而确定纠纷谈判的重点。
以我国民众普遍关注的珍宝岛主权归属问题为例。我国参与谈判的外交代表实际勘察珍宝岛地形时,根据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地理、国际法常识,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无可争议地应是中国的领土。因此,尽管珍宝岛的主权归属备受瞩目,但我们并未将这一问题作为谈判重点,因为相关的事实是清楚的,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也是十分清楚的。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运用国际法这个武器捍卫国家利益时,同样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以自然地貌划界时对国际法规定所做的变通
以山峰、河流作为国家边界是常有的现象。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以山作为边界,应选取两大流域的分水岭或同一流域两大支流的山脊作为边界;以河流作为边界,如果界河是通航河流,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如果界河是非通航河流,则以主流或河流中心线为界。
在谈判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国际法规定中未涉及的情况。如中苏西段边界谈判中,涉及判断霍尔果斯河(现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界河)河源的问题。经过中苏双方的交涉,最终苏方同意了由中方提出的判断河流主源头的方法:距离最长的源头河段为主源;距离相同的情况下,以水量大的河段作为主源;距离与水量都相同的情况下,以与干流流向的一致程度作为判断依据。
又如,中苏西段边界谈判过程中出现的汗腾格里峰段划界问题。汗腾格里峰现为中、哈、吉三国的交界点,在中俄历史上签订的西段界约中曾将汗腾格里峰作为中俄界点。实际上,汗腾格里峰并未处于分水岭上,与其紧紧相邻的托木尔峰比它的海拔更高。本着尊重中俄界约对界点所做规定的态度,同时考虑到实际分水岭线有被冰川切断的状况,中苏双方同意保留汗腾格里峰作为两国界点,并对该段边界进行了文字与地图上更细致的描述。
再如,中法两国在19世纪末签订的《桂越界约》,曾粗略规定了中国广西地区和越南的边界。由于广西多喀斯特地貌,山峰多为拔地而起,难见连绵的山脉,因此确定分水呤或山脊十分困难,这就使得中越两国不得不以“立界桩、画直线”的方式变通地解决了划界问题。
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具体程序
谈判的基础性工作是确定争议领士,这是以双方交换大比例尺地图的形式进行的。双方在地图上标示不一致之处,即为边界争议地区。由制图准确性造成的河流中心线、分水岭或山脊线的不一致,由双方在会谈纪要中进行记录,在勘界过程中加以解决。
勘界过程开始前,双方要签订九个文件,分别是:《联合勘界委员会条例》,规定联合勘界委员会的工作原则与主要任务;《联合工作组细则》,联合工作组是联合勘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负责实地勘界与立桩等工作;《界标工作测量细则》,规定界标测量方法与精度范围;《水文工作测量细则》,规定水文测量的方法、水文图及等深线的绘制方法等;《测图组工作测量细则》,规定大比例尺地图的测绘与修正工作细则;《过境简化规则细则》,准许双方勘界人员可在对方国境五公里内自由活动;《以界标标识国界细则》;《起草议定书细则》及《文件整理出版细则》。此外,双方还要约定界桩的树立位置。属于以下情况的,需要树立界桩:国界急剧变化地段或实际不易确定地段;界线与公路或铁路交汇处;大型居民点或生产活动活跃地段;内河与界河汇合处;界河河床与主航道可能发生变化的地段;水界与陆界相互转换地段以及以直线方式划界时相邻两个界桩位于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段。
勘界议定书及其附图需要双方政府代表签字,在各自履行国内法定程序并相互交换批准书后生效。在我国,使勘界议定书及其附图生效的国内法定程序,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或国务院的核准。按照惯例,要由外交部、公安部和国防部共同通知有关部门执行。
以上工作细则大多是在解决各条边界过程中形成的,这生动地说明了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本身就是丰富与发展国际法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