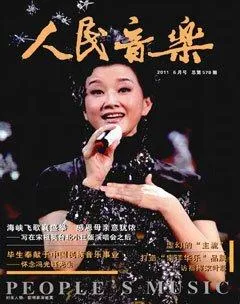音乐的概念\\音乐的功能与血气心知
2011-12-29王虹霞林桂榛
人民音乐 2011年6期
英文musicology(音乐学)一词出自1909年,与法文musicologie、意大利文musicologia有渊源关系①。音乐一词更古老,英文music源自法文musique、德文musik、拉丁文musica、希腊文μουζα和μουοικη τεκνη,希腊文其意为缪斯的艺术或属于缪斯的②。缪斯(Muses)是指希腊神话体系中主管文艺及天文等的九位女神,其中Euterpe擅笛,Polyhymnia擅歌,二者被奉为音乐女神③。今music则专指音乐艺术④。
音乐是声响(sounds)的组织、构造艺术(art),声响感知依赖于听觉官能,声响则产生自器物震动⑤。依声源分类,音乐今被分称为声乐、器乐;而中文常用的“音乐”一词,其音、乐二字恰是分别指今声乐、器乐。考诸文字,“音”本指口声,后指歌唱或歌声,再后又泛指一切声响;“乐”本为建鼓(樂/
楽/ / / / / ,悬铃或不悬铃)⑥,后指乐器奏鸣(含所奏之曲)或综合性歌舞活动,并基此衍生愉悦、快乐、和乐等语义。
一、音乐感血气与宣志
“乐”字有一为人所熟知的义项就是愉悦、快乐意,《礼记·乐记》也有这种用法。“乐”何以由象建鼓形演变为奏鸣、歌舞并有愉悦、快乐意呢?因为“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鼓所以检乐,为群音之长也”、“建鼓,为众乐之节”⑦。鼓有统率群声、号令群民的节奏作用,而这种作用实本于鼓声如雷一样的振奋人血气之功能,此《黄帝内经》所谓“雷气通于心”,《乐记》则谓“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击鼓而舞是先民的生活常态,尤其在大型群体聚会上,故至今仍有“鼓舞”、“鼓舞人心”等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击缶而歌”击的依然是鼓,外形仿曾侯乙墓铜冰鉴而已)。
魏末嵇康《声无哀乐论》⑧与19世纪奥地利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⑨一样,认为声响自身无情感内容(质),它只有舒疾形式(文)与感人躁静的功效。人的知觉或血气、情感是能被刺激而产生或显现的,故嵇康说:“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舒疾—躁静—哀乐”的连接实在声响的舒疾躁静与人血气生命律动之舒疾躁静的交感,而血气生命律动之躁静自然关联人的情感或情绪,故“躁静—哀乐”完全是“刺激—反应”的“物理→生理→心理”过程,孔颖达疏《乐记》“心物交感论”谓“物来感己心,遂应之念虑兴动”。
这个“心物交感”过程决定了特定的音乐构成、音乐形式(声响)能激发特定的“物理→生理→心理”效应,加之人精神意识的“积”与“思”(《乐动声仪》)⑩,故音乐催发的心理效果是丰富的,是具体而纵深的。反之,一个人的心理、生理势能同样可通过参与特定节律的音乐活动来宣泄或释放,故嵇康说“歌以叙志、舞以宣情”。为何年轻人或尤其活跃的年轻人喜欢参与激烈动感的音乐活动,喜欢参与节奏明显和抒情直率的歌唱活动,这其实是因声响效应下“血气—心知”、“生理—心理”的交感机制。
故而,时尚的通俗音乐或动感歌舞自有它存在的价值,自有它依附的人群。这种音乐对于宣泄、释放人旺盛血气下的心理、生理紧张有正面功能,它可以促进人的心理、生理平衡,有利于缓解人尤其是年轻人身心内的高位生理势能、心理势能,“以平其心、以畅其志”(《通典》卷一四一),“和悦性情、畅通血气”(《太和正音谱》)。而年轻人生理、心理实现平和畅达,这对于他(她)自身及社会的安宁与幸福都是有促进效应的。
二、音乐化情性与归和
音乐不仅有直接促进人亢奋型“心理—生理”势能获得宣泄释放或激发产生的功能,而且简单血气心理功能外还有更丰富、更细腻的心理功能,这个功能不是简单的宣泄或激发,而是像皴染、熏陶、濡沫一样渐渐地化人意识,化人情性,完成一种内化型的心理意识塑造。当然,这个塑造过程完全依赖于具体而丰富的音乐刺激(感知),且一个良好品质的心理塑造又完全依赖于一种良好构成或良好形式的音乐。
血气是心知(精神)的基础,孔颖达疏《乐记》“血气心知”范畴时说:“人由血气而有心知,故血气心知连言之。”生命的健康常态是血气运行的平和有规律,而不是持续的、无节制的激烈或亢奋。故与认识到前述感血气、宣情志这一基本功能相比,中国古代哲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音乐于塑造人良好心理品质的涵养功能,而且比前者更加重视这一功能或价值。故《乐记》等儒家经学论音乐总是强调是“乐”塑造心理人格的价值或功能:“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荀子·乐论》)。“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史记·乐书》)孔颖达疏《乐记》曰:“善乐感人则人化之为善,恶乐感人则人随之为恶,是乐出于人而还感人,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火出于木而还燔木。”{11}人创作、演奏的音乐是出自于人心与人为,但音乐反过来又可塑造人心以及人心指令的行为。而古典音乐的功能或魅力,就多不在直接感发、宣泄人亢奋性的血气心理,而在获得血气心理的超越,达到平和、宁静、恬淡、丰富、优美的身心愉悦与健康。
罗马哲人波爱修斯说音乐和谐一在声响和谐,二在身心和谐,三在宇宙和谐{12}。《乐记》则有云:“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此正所谓尚和之“德音”:“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三、音乐养个人之趣味
“和”是追求,但音乐参与的起点未必是“和”而是个性化的具体趣味。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13}(第4013页)又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第3963页)无注意力的趣味化集中,所谓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常常导致人精神游离、恍惚、颓废,导致精神、心理疾病,乃至人体健康受损,此中医所谓“神散”之害。故孔子教导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
当然趣味不见得都是好的、健康的,至于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论作标准”(第3963页)。梁启超称自己是贯彻了趣味的“趣味主义”者,他的趣味是做学问,并把艺术、学问、劳作、游戏并称为人类四大趣味(第4013页)。又说:“专从事诱发以刺激各人器官不使钝的有三种利器:一是文学,二是音乐,三是美术。”(第4018页)还直接提出艺术与情感的关系:“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情感教育的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第3921—3922页)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音乐所关注的恰恰始终为个体化、个性化的人,所落实的也始终是个体化的人。音乐比其他艺术更富有鲜明的个性,更具有鲜活、快捷的感应效果,荀子所谓“入人深、化人速”,前述音乐与血气律动之关系已明之。故音乐对于滋养个人的趣味尤其是培养个人的人生爱好,是便利而深厚的。就譬如孔子,他特别地爱音乐,爱弹琴和唱歌,并且自己作曲,办学重乐教,像他这种人是不可能得精神抑郁症的,他生活得专注、快乐、坦荡,乃至不乏幽默,真是“仁者寿、智者乐”。
梁启超说:“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第3964页)本质上绝大多数人都具音乐律动的天赋,只要血气生命在,都是天生的歌手舞手;音乐尤其是古来优秀的音乐,对于滋养、培养、涵养个人的生活趣味尤其是健康、高雅的趣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
四、音乐承社交之方式
“器乐,就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意义来讲,在中世纪几乎不存在……只是自十六世纪起器乐与声乐才开始明显地区别开来。”{15}“18世纪是欧洲音乐史的一个转折点,音乐从声乐形态向器乐形态转变,音乐创作从声乐思维向器乐思维转变。”{16}近代之前,中西方的音乐形态都是以“音”(人唱)为主而不是以“乐”(器奏)为主,即器奏之乐的纯独立性还不够,所以称“比音而乐之”即乐是为协音(唱)而配的,此即所谓“弦歌”,《毛诗传》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
古往今来,歌唱、歌舞多为群体性活动,《乐记》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就是指在配乐的情境下饰以各种道具载歌载舞。《论语》说:“子(孔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这就是典型的“唱和”,《诗经》里有更多记载,而且单从今本诗句上看去其音乐节奏性依然明显,明显可配唱或跳。载歌载舞是先民常有的生活形态,在祭祀、庆贺等节日性、时令性聚会中歌舞及用乐尤为重要,村邑的各种社集常见歌舞。现今自娱自乐型、表演欣赏型歌舞在城市中亦极普遍,现场参加室内外群体音乐活动并非稀见,乃至群体音乐活动成为了一种社教方式——如听音乐会,听演唱会,休闲娱乐场所唱歌、跳舞等。
音乐对于宗教活动尤其重要,对于宣扬教义、感化信众有重要功能。卡西尔早已明揭“宗教的仪式先于教义”这一心理规律与历史真相{17},而音乐正是教堂礼仪等的核心组成部分。圣严法师说西方基督教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普及,其仪式体系早贯彻到人们的日常风俗习惯中尤其“生—婚—死”等礼,群体性的宗教活动实是他们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现代西方的各种宗教集会,乃是社交的活动”{18}。周谷城也叙述过宗教道场聚会的社交性:“现在许多礼拜堂里的礼拜,确实是变了性质的。礼拜日上午,大家穿上新衣,携着儿女,到礼拜堂,听听音乐;听完之后,同朋友谈谈天,说说笑话;青年男女,还可乘此讲讲爱情。”{19}
即使不论宗教性活动,仅就古人、今人的室内外普通生活而言,音乐依然是重要的。譬如一个爱音乐、玩音乐的人,他(她)除了自己享受艺术乐趣外,也更给他人带来欢跃(欢悦),更受他人欢迎,当然也显著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社交空间。当今各种以音乐为主题的社会活动或非以音乐为主题但以音乐为背景的文化活动,本质上它还是一种聚会型的社会交往方式或过程。音乐既是社交活动的重要“背景”,也是承托、连接社交活动的重要媒介,甚至是社交活动的直接目的。托尔斯泰曾说“艺术是人与人相互之间交际的手段之一”{20},只要人类在,音乐的社交功能或社交性不会消亡。
五、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
王国维说“美育即情育”,王国维、蔡元培尤倡导艺术与美,这与中国古典儒家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他们吸取了古典儒家的思想营养才提出这种现代化表述的教育、文化主张。音乐的向度是美,也是情,总关涉生命的情思,儒家认为生命情思的最高境地是“和”,故《乐记》说礼别乐和、礼序乐和、礼顺乐和、礼敬乐亲、礼庄乐欢、礼辨异乐统同、礼别宜乐敦和、礼合敬乐合爱,而礼乐流弊则是礼离乐流、礼慝乐淫。荀子《乐论》曰:“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1942年朱光潜《谈修养·谈美感教育》说:礼的目的在规范仪表,“养成生活上的秩序(order)”;乐的目的在怡养情性,“养成内心的和谐(harmony)”{21}。
《吕氏春秋·音初》说:“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汉书·礼乐志》云:“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音乐具有宣泄功能,音乐也具有升华功能;音乐具有激发功能,音乐也具有缓和功能;音乐具有外化功能,音乐也具有内化功能;情性会左右音乐,音乐也会左右情性;音乐可以涵养个体趣味,音乐也可以承托社会交往,音乐之功可谓甚大,故《乐记》引古语赞云:“乐观其深矣!”(此“乐”系广义之乐,指歌舞活动,下引经同)
《易经》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总之,音乐实属人类“人文—化成”的文明创造,音乐作为一种依赖听觉来感知的声响组合艺术(文),它有着特定的功能(化):音乐能感人血气与宣泄情志;音乐能化人情性与归于宁和;音乐能涵养个人趣味;音乐能承接社交方式。音乐对于个人的身心和谐、精神愉快以及社会群体生活的和谐、文明、优美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故而乐教与音乐生活应成为教育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由经学专家林桂榛博士审读并提供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谢忱;另,本文受江苏省教育厅学术经费资助,项目号:09SJD760007。)
①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词源词典在线),http?押//www.etymonline.com。
②《大陆音乐辞典》,康讴主编,大陆书店(台湾),1981年版,第771页。
③〔美〕斯洛尼姆斯基、卡塞尔《韦氏新世界音乐词典》中文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7页。
④Music?押 Art of arranging the sounds of voice?穴s?雪 or instrument?穴s?雪 or both in a pleasing sequence or combination.(音乐是人声或器声或人器声以令人愉悦的一定次第或编合而组织成的艺术)--A P Cowie?熏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穴Fouth edition?雪. Oxford?押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熏 1989.
⑤王沛纶《音乐辞典》,文艺书局(香港),1968年版,第447页。
⑥今文字学界、音乐学界皆从清末罗振玉之说,认定甲骨文“ ”即“乐(樂)”字,然此释文实不能成立。“ ”或“ ”状表植物(疑“藥[药]”字实由“ ”加“艸”而得,但“ ”被误定为从“ ”而得“藥”之“樂”部),然“ ”状实表建鼓,两字迥异。而“樂”上“白”符为该字要害,系木虡上之鼓状,不能省且古字从不省,此即建木架鼓状,是为建鼓,金文“ ”尤显其建鼓状(表鼓正鸣)。据字形、字法、字义等并观之,两者绝非同一字,唐写本《说文》释“樂”为“象鼓鼙之形;木,其虡也”及今本《说文》释“樂”为“象鼓鞞;木,虡也”实大体不谬(后者点读成“象鼓鞞木虡也”更宜,“木虡”连读指木性之虡),见林桂榛《“樂”字形、字义综考——〈释“樂”〉系列考论之二》,未正式刊登稿,中国音乐学网〈音乐论文〉音乐学学科理论,2009年12月29日发布。
⑦分别见唐马緫《意林》卷二引先秦《申子》佚文、唐代赵蕤《长短经》卷一;《北堂书钞》卷一百零八引《五经要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二引《五经要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二引《通礼义纂》等。
⑧〔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嵇康集》,刻本影印本,江苏古籍刻印社2002年版。
⑨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文版,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
⑩《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5页。
{12}《大陆音乐辞典》,康讴主编,大陆书店(台湾),1981年版,第771页。
{1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7册(简体竖排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15}〔法〕保罗·郎多尔米《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16}蒋一民《音乐美学》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18}释圣严《基督教之研究》,东初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13页。此书另有佛教文化服务处1967年版,东初出版社1967年版、久大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等。
{19}周谷城《礼乐新解》,1962年2月9日《文汇报》;该文收入:周谷城《史学与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周谷城《周谷城学术精华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0}〔俄〕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
{2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王虹霞 江南大学音乐系副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
林桂榛 徐州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