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与误读
2011-12-29李岩
人民音乐 2011年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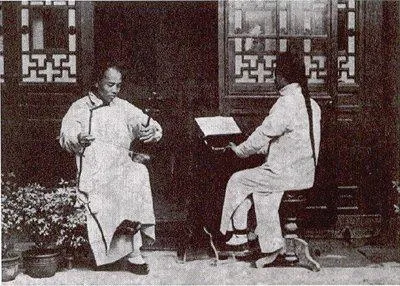
阿炳(华彦钧1893—1950)、刘天华(1895—1932)两位生辰仅差两年的“同乡”,在“生长期”文化地理的“同构”(居地近在咫尺,如“一箭之隔”),使他们有可能产生相同的东西,这使学界纷纷将两者加以比较,文章层出不穷①。但在“青春期”(20岁)后,人文环境的先同后异,及人生际遇的大相径庭,构成必然“不同”的基础。他们以同样的乐器——“胡琴”,发出不同的“声音”,则是他们不同的标志。而他们之间的方方面面,在如此短的篇幅里,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在开论之前,必先设置“问题”,本文初定:“忽略”与“误读”两题,是为序。
被忽略的背景
自20世纪以来,在“传统”被“新文化”质疑并批判时,一个被忽略的背景,即:胡琴作为一种文化,及为戏曲托腔保调的弦索乐,发展势头之强劲,大大出乎今人之意料。在刘天华未入北京(1922年)之前,仅京胡曲谱的出版而论,大量种类繁多的京剧胡琴谱纷纷面世,如:
1.佚名编《阳春雅奏》,清光绪(1875—1908)抄本(出品地不详,工尺胡琴谱)。
2.慨志生著,上海“天宝石印局”编《京调工尺谱》(又名“涤古斋京调工尺谱”)(1914年石印本)内收:《独木关》、《打棍出箱》等34段京剧曲谱。
3.曾志忞、高砚耘编《天水关》(八场京剧)五线谱(白承典、邹振元制谱,1915年6月版,出品地不详)。
4.程焕卿编《京调工尺谱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15年版。
5.乐天生、吴癡魂著《戏曲汇考》(工尺谱,初集、二集)。
6.知音俱乐部编《京调工尺谱》,北京:中华书局1917年版。
7.陈彦衡著《戏选》(第一册),北京:北新书局1917年5月版。
8.陈星垣编《京调胡琴秘诀》(工尺谱),上海:中华图书馆1918年版。
9.周剑云编《菊部丛刊》,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
10.[清]王奕清等编《钦定曲谱》,苏州阊门/上海,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内收北曲谱4卷、南曲谱8卷及曲牌千余首。
在刘天华1922年进入北京前后,除京剧胡琴继续大量面世外,当时胡琴常与风琴结伴,并形成一种独特的乐曲体裁“琴戏谱”,如:
1.[日]近森出来治编《清国俗乐集》(一)、(二),上海:新中国书局1908年版。
2.蒋恨编《风琴戏曲谱》第一集,上海震亚图书馆1915年1月版/上海:文汇图书局1922年版。
3.吴调梅《京调风琴谱》,上海文明书局1923年版。
4.陈彦衡编《胡琴韵谱》,北京:菊贤社1924年版。
5.宋寿沛编《风琴戏曲谱》第二集,上海新民图书馆兄弟公司1925年4月简谱版。
6.知音馆主编《大正琴戏曲谱》,按:目前仅见北京中华印刷局1927年4月(简谱)第2版,首版未见。
7.瑞文书局编《大正琴戏谱》(新编第1册),北平:瑞文书局1929年版。
8.许志豪编《风琴胡琴京调曲谱大观》(共8册),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1933年/1935年(工尺、简谱)版。
9.申健生编《风琴胡琴小调大观》,上海:知音乐社版(出版年代不详)。
另,胡琴的“教科书”如惕身馆主著《胡琴正规》(中华印刷局工尺谱版,按:出版年代不详)、陈伟仑编《京胡学习法》(戏学丛书第二集,上海戏学书局,工尺谱、简谱版,按:出版年代不详)、徐兰园校正、嗜菊轩主订《胡琴正宗》(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年代不详)也有面世。这说明学习胡琴有相当“市场”,“它”不但有风琴助威,还步入了“正轨”——教科书系列。这一现象可说是被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者们所勿略一个重要“史项”。而以后如《胡琴研究》(方向溪1938)、《风琴胡琴学习法》(附时调新曲谱,工尺谱,国风社编1948)、《京胡速成》(浦梦古1949)等证明:
其一,国人学习京胡的热情一直在持续高涨之中。
其二,京胡也进入了现代的教育系统,而非仅“口传心授”一途。
其三,京胡与风琴的结合,由于后者是一个多声乐器,在为胡琴伴奏也好,合奏(或齐奏)也罢,有旋律配和声的问题,它们是如何结合及如何相配,胡琴的带“腔”与风琴的无“腔”,及由音律(“平均律”与“非平均律”)的不同所造成音响上矛盾与冲突,是如何解决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其四,上述名目繁多的各类胡琴专谱加“琴戏谱”之“曲目”数量,据不完全统计,已达数千余首之多。
也即是说,刘天华进入北京前后,该地是一个京剧的海洋、戏窝子,“他”作为一个听觉极为敏感的音乐家,受京剧音乐的影响,似成必然。加之刘天华对京剧颇爱,并多得著名票友“红豆馆主”溥侗的点播,会唱很多京剧唱段,一次还曾与弟子程朱溪同演过溥侗亲传的《长生殿》②。张慧元认为:“刘天华的二胡曲中,有些作品的乐句以至乐段结构,是从京剧音乐的相似结构中脱胎衍变形成的。”③如《独弦操》的始句与“西皮快三眼”的过门音乐,句式结构基本相同;再如《病中吟》不但从程砚秋的《文姬归汉》片断中汲取了音调、句式结构框架,在表情、风格、神韵上都与其有渊源关系;《烛影摇红》的第一段,旋律与旋法取自西皮声腔。④即:刘天华在未进北京前,其平生第一首二胡创作《安适》(又名《胡适》,即《病中吟》1915),已经有京剧的成分并延续至他的“天鹅绝唱”——《烛影摇红》(1932),从而映衬出京剧影响的地域“广度”及对刘天华创作长久持续的“深度”。另据刘北茂讲:“天华学习戏曲,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他写的二胡独奏曲《悲歌》与《烛影摇红》了。这两首二胡名曲均借鉴了戏曲音乐中的散板表现形式,并加以发挥创造,从而进一步改进了(他的——引者加)二胡的演奏技巧。”⑤这旁证了刘天华曲调上的创新,是深深根植在京剧曲调的沃土之上的历史实情。但他绝不是对京剧曲调的照搬,而是在烂熟于心的基础上信手拈来,形成一种“不留痕迹”、“润物无声”的样态,故不细心观察、仔细揣摩刘氏乐谱,很难发现。
被四重误读的“阿炳”
笔者认为,阿炳被世人在音乐演奏、道教精神、生活场景、社会身份四个层次误读。
音乐演奏:阿炳的所有音乐遗产,已被学人细致入微地研究过,特别对阿炳本人演奏之“依心曲”——《二泉映月》(按:为杨荫浏后加曲名,该曲本无名,用阿炳的话说,是瞎拉拉的“依心曲”,以下除“引文”——为保“原型”,不能改变——外,均简称《二泉》)的钢丝录音带,“连一个细小的装饰,一次几不可察的压弓,一声微着游丝的滑指,都不被放过。不少人一句一句地模仿阿炳的演奏。也有人不理会阿炳的演奏,自起炉灶,重新处理阿炳的音乐。”⑥各种不同演奏、花样组合、重新配器的《二泉》应运而生,但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这些均不是原来的“阿炳”也未能表达阿炳音乐的“神韵”。冯洁轩甚至极端地说“真正能奏出阿炳原曲神髓的,恕我狂言,至今尚无一人!”⑦笔者认为:阿炳的被曲解,与我们对他了解得不够“深入”,有关。
道教精神:阿炳本不苦,但我们认为他很苦,是曲解之一。换句话说,他的苦状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并且是全面凄苦:从音调到生活,无一不苦。我们不禁要问:事实果真如此吗?起码作为一个道士的阿炳,在他的理想中,“苦”不是“极境”,因道家的最终目的,是“长生不老”,并享尽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还要达到“极致”,正所谓:“登虚蹑景,云轝霓盖,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⑧只是在此种目的受阻、不得已、及赖以生存的道观破败之时,阿炳才行“乞讨”之下策。
生活场景:由于阿炳有“手艺”,并有一个妇人(董翠娣)帮衬,所以他的生活,并不像今人想象得那么凄苦。有学者说,即便“阿炳”死时,下葬得也很风光的。1950年12月病亡之阿炳,是“身着‘鹤擎’头上梳着道士发髻,按雷尊殿当家道士身份和待遇,供竖着由道人施泉根书写的‘先祖师华彦钧霞灵位’葬在只有道士才能安葬的灿山‘一和山房’墓地圈内。阿炳去世后29天,其堂兄华伯扬邀请了道士尤武忠、朱金祥、许坤沼、朱三宝、朱惠泉等人为他做‘五七’,在火神殿做了一日头道场,以祈求神灵保佑阿炳灵魂之安宁。”⑨这难道是平头百姓所能消受的待遇吗?这种场景,也与我们以往想象中阿炳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形象相差何啻十万八千里,所以,阿炳绝不是一般平民,而是一个有产的道长,只是这一历史实情,被杨荫浏出于善意地遮蔽了,而已。
社会身份:钱铁民认为:70年代后期兴起的阿炳热,乃至其后各种有关阿炳的研讨活动中,一些同仁对杨荫浏先生当初介绍阿炳失实之处,议论颇多。这里姑且不涉及《二泉映月》的定名经过及阿炳作品内容的解析。仅把阿炳说成“只能离开了道门,开始以卖唱为生”让华彦钧与宗教绝缘一事来看:杨荫浏凭他与阿炳……近四十年的交往,难道他真不清楚阿炳的身世?不清楚阿炳就是他笔下……拥有庙产……的雷尊殿当家主持这一真实身份?笔者认为,杨荫浏先生完全……为了应顺当时的政治气候,才把阿炳推入民间艺人吹鼓手的行列。救了阿炳,救了《二泉映月》这首感人肺腑的佳作,标树了一位苦大仇深、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民间音乐家。⑩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阿炳到底还有多少被遮蔽的真象?因其身份是假的,《二泉》曲名是别人赋予的,那他那著名的随便拉拉的《依心曲》中,什么,才是属于这位有产“道长”的真情实感及要表达的内容?抑或真的是“随便拉拉”而已——毫无内容可言呢?总之,这绝非凭我个人之力所能解答的问题,它有待时日,更有待大智大勇之人来完成。
余论
1.阿炳与刘天华,均有被读误之处,对阿炳最深的误读,是其“苦”并达“深重”程度。田青在听山西左权盲人宣传队12位盲人演奏(唱)后,感动得涕泗滂沱,而使他最动情的,是盲人们对人生的追求,及回馈社会时在艺术中表现的“真情”奏唱,其最深情处,有光棍对女人的玄想,失去光明后的人生苦痛、个人感悟,及三百年前的一个大荒年,出于无奈的一家人为了活命,而被迫卖儿鬻女的故事。并称这12盲人的演唱,使他看到了阿炳的再生。{11}但这些与阿炳何干!阿炳不愁吃穿,更不缺女人,特别在笔者仔细聆听阿炳的钢丝录音带版《二泉》后,我的个人感受是:并没有那么多悲苦,而更多的是一种“乐天”的声音样态,从而显现出一种特有的“平淡”及“平和”,是“看似平常实奇崛”的别样风范。
2.对刘天华的误读,完全是后人的过分、过高、甚至不切实际的要求所致。
标准之一,是“革命现实主义”。并认为刘天华之所以非此类音乐家,是因为他在创作上,“没有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所以我们不能称他……的二胡作品是现实主义的。”{12}特别当“九·一八”后,以“没有听到刘天华在音乐上的呼声”为由设问:“为什么他的作品不能放射出强烈的战斗光芒呢?”{13}并对刘天华的作品缺乏战斗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仅仅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吗?肯定说,不是的……时代同样为刘天华先生开着一扇通向斗争,通向革命的大门,而刘天华先生没有奔向这座红门。这也不奇怪,主要还是由于他的阶级属性所致。”{14}这种评判完全把刘天华以“革命者”来加以要求,并将他严格地归类于“资产阶级”。
标准之二,以“革命与否”来评判其是否“积极”,认为:刘天华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走向了反革命;可是更多的无产者和知识分子投入了革命。……我们说刘天华在这样的时代里并没有步步向前……没有‘更觉悟’起来,反而对政治和革命采取极为冷漠的态度,这正好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消极性。他那以个人为中心的超阶级的艺术观在此已经暴露出一片消极的因素,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创作。”{15}以上虽是在20世纪的那个“极左”年代里,对刘天华的不切实际的评判,但引以为鉴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在此郑重提请学界同仁:莫以今人度古人!
3.在笔者所提供的京胡书谱中,曾志忞的名字格外抢眼,这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曾喊出“破坏中国文物”{16}的激烈革新派,现又热心提倡京剧,从而显现出一种从醉心西化回归国粹的历史轨迹。无独有偶,刘半农曾坚决反对过京戏,而当胞弟刘天华为梅兰芳出访美国做准备,并为其唱段记谱时,在出版的《梅兰芳歌曲谱》所作“序”中,称:“我可以不打自招: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对旧剧的人。”……现在“对于旧剧,……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于把已往的优点保存着,把已往的缺陷弥补起来,渐渐的造成一种完全的戏剧。”{17}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当我们今天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种音乐类目,重新展现于舞台之上,实际是当代最为重大的“迷途知返”,而它的起始点及代表人物的言行,从何时“启程”、“现身”,又有什么不同既往的举动?一直未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是极不正常的“现状”,也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只有重视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找到民族的根,及文化的安身立命之所。这即是前人的昭示,也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更是我们今天纪念两位国乐大师阿炳、刘天华的本意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天华(记谱),齐如山、徐兰园、马宝明参订《梅兰芳歌曲谱》,北平:铅印暨石印本,朱墨套印。1930年版。
2刘复《梅兰芳歌曲谱·序》,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1935年版。
3方向溪《胡琴研究》,北平:六岚簃印书局1938年版。
4国风社编《风琴胡琴学习法》,汉口:新声出版社1948年版。
5浦梦古《京胡速成》,香港:太阳出版社1949年版。
①蓝玉菘《他体现了传统演奏艺术的精髓:在文化部和全国音协举办的纪念华彦钧(阿炳)诞辰九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李西安《阿炳与刘天华之比较研究》,《中国音乐》1983年第4期;赵砚臣《阿炳的二胡演奏艺术及其形式美:在纪念阿炳诞生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音乐学习与研究》1994年第2期;邱环东《比较分析刘天华与阿炳音乐创作的艺术特征和历史意义》,《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杨瑞庆《比较研究刘天华和华彦钧的二胡曲》,《交响》2001年第2期;孙焕英《华彦钧与刘天华比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张凌飞《刘天华与阿炳之比较》,《器乐》2005年第3期;张晓霞《艺术人生,殊途同归:刘天华与华彦钧》,《当代艺术》2006年第3期;张春苗《刘天华、华彦钧二胡艺术比较研究》,《大众文艺》2010年第23期;等。
②⑤刘北茂(口述),育辉整理《刘天华后期的音乐活动》(上),《人民音乐》2000年第11期,第18页。
③④张慧元《刘天华二胡曲京剧因素的识辩》,《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2期,第94页。
⑥赵晓生《阿炳启示录》,《音乐艺术》1994年第1期,第2页。
⑦冯洁轩《二胡小史》,《乐器》2000年第2期,第30页。
⑧[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卷3)[DB/OL],第317页,转http?押//www.douban.com/group/topic/1261749/
⑨⑩钱铁民《阿炳与道教》,《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4期,第54页。
{11}田青《阿炳还活着:听山西左权盲人宣传队》,《艺术评论》2003年第1期。
{12}{13}{15}原矢《关于评价刘天华的两个问题》,《音乐研究》1960年第3期,第35页。
{14}同{12},第36页。
{16}原文:“中国之物,无物可改良也,非破坏不可,非大破坏而先大创造亦不可!”此话出自曾氏1904年出版于东京的《乐典教科书·自序》。转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17}此文写于1929年12月30日,初发《梅兰芳歌曲谱》(1930),后载《半农杂文二集》(刘复1935),现转《刘半农书话》http?押//www.lantianyu.net/pdf35/ts032049_2.htm
李岩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