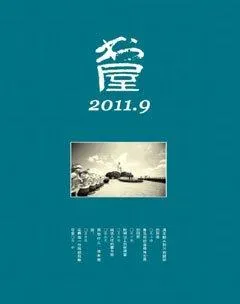“为白人的羞耻付出代价”
2011-12-29罗楚盈
书屋 2011年9期
在美国南方一个白人家庭里长大的马克·吐温,曾有过作为白人的愧疚和持续增长的种族问题意识。为了回应奴隶制度遗留的种族歧视,他创作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小说通过哈克贝利与逃亡奴隶吉姆的友谊故事,诠释了黑白两个种族间的平等意识。小黑奴在这个白人男孩的生命旅途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哈克贝利下意识地触摸到奴隶的价值,进而揭示出两个种族的同等地位,而非人们固有观念中的优劣关系。
在吐温所处的那个时代,奴隶制被普遍接受。在学生时期,他并不觉得这个制度有什么不好。他在自传中写道:“当地的报纸没有反对它,神职人员也说得到了上帝的许可。”用吐温的话来说,那个社会,在他心里,也在故事中的哈克贝利心里,种下了“变形的良知”。幸运的是,故事中的俩人都有一颗“健全的心”,可以战胜那良知变形的心。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赤道环游记》中,吐温还提到当年目睹一个奴隶被活活残杀的经过。在逐渐认清奴隶制的本质后,他获得了最终的结论:奴隶制找不出任何存在的理由。
奴隶制尽管在美国内战后就被废除了,但由它带来的种族歧视持续地禁锢着有色人种的生活和地位。各种文化都建立在偏见和不平等的基础上,尤其是像密西西比河谷(吐温成长和故事发生地)遗存在奴隶制之上的文化。比如说,有一种表演是由白人扮演黑人,模仿他们的言行来达到滑稽的效果。这些表演掩盖并压制了白人对黑人道德和人性的认识。羞耻、无知、木讷、顺从,这些都是与人们心中典型的黑人形象有所关联的词汇。
吐温笔下的吉姆就是按照这种典型来塑造的。在故事里,他得毫无尊严地接受汤姆·索亚对他的愚弄。吐温在揭露这层“典型”面具的伪装之中,展示了吉姆的人性。儿时的种种经历增添了白人作家的内心愧疚,面对战后重建中想为黑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找到位置的失败,吐温决意“为白人的羞耻付出代价”。正如他帮助一名黑人学生就学耶鲁大学法学院一样,撰写《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是他“付出代价”的一种方式。
最初的打算是将这本书写成《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续集。此书是一本深受儿童喜爱的书,现在的续集却严肃深刻得多了。吐温在写给一位图书馆管理员的信里承认,《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供成人阅读的书。的确,虽然是好朋友,和汤姆不同,哈克贝利有他自己的思想。他的经历更加充满真实生活所带来的危险,而汤姆却更多的是出于自己天真的想象。带着更加务实的态度,哈克贝利从现实中学习并建立人际关系,在现实上践行道德标准。
尽管是白人,落魄的哈克贝利并非生活在主流社会里,而是生活在主流道德规范之外。他的局外人的位置,促使他同中心的道德语言相分离。故事里这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男孩,话语里出现很多语法错误,就象征着他疏离主流社会。他的道德水平绝非成熟或文明——他甚至试图振振有词地为偷窃找借口。显然,哈克贝利缺少恰当的理性思考,喜欢根据他与人的关系来自发地认定道德规范。例如,他从未为了其他人或事坚持立场或者做出行动,直到他与玛丽·简的关系和情感超过了他与两个骗子,“公爵”与“国王”的关系,才最终决定帮助玛丽·简结束一场诈骗。
尽管吉姆是个逃亡奴隶,哈克贝利也对他一视同仁,只因他是好朋友之一。这就解释了这个故事有争议的结局。在结尾里,哈克贝利默认汤姆在救吉姆出来时戏谑他,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似乎与哈克贝利应做的以及故事想要表达的思想背道而驰。其实,对于哈克贝利来说,汤姆和吉姆同样是最亲密的朋友,不想为任何一方而忽略汤姆对娱乐的需求或者吉姆对自由的需求,他们之间不分等级先后。他本能地选择沉默,与其说不想拿友谊来冒险,更加表明他自发地把汤姆和吉姆看成平等的个体。
哈克贝利另一次沉默的选择也饱含深意。汤姆受枪伤,哈克贝利与正在逃跑的吉姆进退两难,或者让汤姆就医延误吉姆行程,或者保证吉姆自由但危及汤姆的生命。哈克贝利再一次选择了沉默,但把决定权给了吉姆。“说出来,吉姆”。哈克贝利说。他想道,“我知道他内心是个白人,我也猜到他会说他说了的话……所以现在一切都没事了,我也告诉汤姆我会去找医生”。
这几个事实说明,哈克贝利不老于世故,也没有清晰的是非观。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境界,从一种文化特定的价值观审视普遍的道德原则;他没能从自己意识到“吉姆内心是白人”来得到概括性的“种族歧视是不对的”结论。事实上,他的无修饰的选择与反射正体现了健全的人性——对种族平等本能的感知。我们在此可以窥见吐温的倾向:如果人们没有被社会观念所束缚而随着本能和灵感,就会不带偏见的面对不同的种族。
在刚提到的场景中,吉姆的反应比哈克贝利的显得更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一个黑人的人性,这种白人社会企图掩盖的品质。吉姆对哈克贝利“说出来”的要求作出了回答:“要是不找医生,我一布(步)也不走,即便要等四十年也行!”他不仅把汤姆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自由重要,还提到了四十年的期限。四十年,也就是吐温写作此书的时候,这象征着吉姆愿意将自己的奴隶生涯延长到漫长的历史时刻,甚至他的余生。吉姆也相信汤姆也会为他做同样的事情。这个数字是吐温用来放大吉姆的道德而特意设计的。因为事实是,故事中任何一位白人都不愿意为黑人牺牲这么多。小说故事不仅揭示了吉姆有人性,而且作为一个黑人,有着超出种族的爱心和同情心。
他的人性在其他地方也有所体现。在一个浓雾把河上的吉姆和哈克贝利分开的场景中,重逢时他看到哈克贝利还活着喜极而泣;而哈克贝利却恶作剧地告诉他一切都是他的想象,他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吉姆被触怒了,说:“那边一堆残枝败叶是垃圾;那些把脏东西往朋友的脑袋上道(倒),叫人家为他害少(臊)的人也是垃圾。”骂哈克贝利是垃圾,同时又澄清他们的友谊。哈克贝利明白了黑奴也是有感情并会受伤害。这是哈克贝利和读者一同领悟到黑人人性的开始。后来,在故事里,哈克贝利还观察到吉姆为他的家庭担忧。“他坐在那里,脑袋垂到膝盖中间,独自唉声叹气……情绪低沉,思家心切。”哈克贝利由此“相信他跟白种人一样,爱怜他自己的人。这似乎不合乎自然,不过我看这是实情。”他也有爱心,所以他才有动力要把家人也从奴隶制里解放出来。当他回忆自己曾打过女儿,他满心悔恨。哈克贝利最终得出结论:“吉姆真是个好心肠的黑奴。”这里揭示出作者的信念:没有任何理由表明白种人高人一等。
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思想显然不够健全,用吐温的话说,“人类被习惯和顽固的社会规范所束缚,并进入一个永久的、逃脱不了的自我毁灭的循环”。奴隶制度野蛮而又残忍,但那个时代的社会却不允许质疑。至少三名公开质疑奴隶制的汉尼拔(故事发生地)人被逐出城,并不是极端的例子。尽管如此,马克·吐温还是用他的笔写下了他的怀疑和信念。通过一个记叙种族间交流和友谊的故事,他成功地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证明了种族间、人类间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