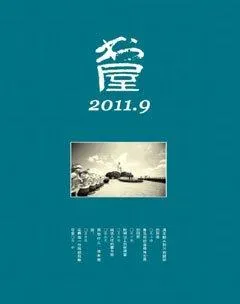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突围
2011-12-29周国清莫峥
书屋 2011年9期
儿童文学是少年儿童成长的精神乳汁,关乎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然而,伴随着传播新技术的极大发展、信息时代的快速来临和消费文化浪潮的空前侵袭,电子媒介对童年生态和儿童文学进行了全方位渗透,其中既有正向的审美生成和价值取向,也更有负面的心理影响乃至精神断裂;在嘈杂而拥挤的现代生活中,在海量信息与媒介轰炸的阅读语境下,一些中小学生连很多常见的汉字都不会写了,很多青少年已经失去了阅读体验,更谈不上从中得到快乐,可见,大众电子媒介深刻地影响了童年和与童年成长融为一体的儿童文学场景和儿童文学活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状和基本体认,谭旭东一直关注特定技术背景、文化生态、媒介与阅读环境下的童年和儿童文学发展,其三十三万余言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一书,站在儿童文化和文化诗学的层面,以童年的历史构建和童年文化的生成作为开掘点,密切联系当下电子媒介对童年生态和儿童文学颠覆的现状(使用很多实例,举证分析当前儿童文学的症状),将电子媒介时代童年如何再现、儿童文学的嬗变和重构等问题,置于儿童、儿童文学与电子媒介交锋的现实时空予以思考。
一
媒介和媒介文化已经影响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正在改变人的情感世界及其表达方式,使人的精神生活与媒体发生不可割舍的联系。一方面是现代电子媒介与消费文化的高度发达和普及,一方面则是美好人性的丧失和人的工具化;一方面是现代人尽情享受着电子媒介带来的便利和愉悦,一方面则是生活的程式化和对媒介的依赖性给人性带上了桎梏。儿童当然也不例外。这种现象,引起了国外人文知识分子较早的关注。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著名媒体文化学家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描述了童年概念的萌芽、形成和正在消失的过程,面对泛滥的电子媒介对童年生态的破坏,面对童年美好记忆的被吞噬,面对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全盘入侵,面对童年美好状态的消失,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大卫·帕金翰教授则的《童年之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对童年与媒体环境的转变提供了清晰的结构图,既反对媒体负面影响所造成的道德恐慌,也就受媒体控制的童年提出了新的战略,重新阐释了儿童与电子媒介的关系,认为儿童不应被隔离于成人世界之外。就国内情况而言,近十年来儿童文学空前发展,但沾上了商业化和娱乐化之风,丧失了儿童文学的本性,其间电子媒介的影响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特别是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促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因此必须从消解走向回归、重构,探寻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突围的新路径。而这,正是《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的追求和有力尝试。
作者认为,“尽管西方学者在探讨电子媒介对儿童的影响和对文学的影响方面有着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但媒介和儿童特别是和儿童文学内在或外在之联系的研究还存在着空白地带”。在西方如此,中国也就更加如此。电子媒介对童年与儿童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盘渗透的,不能仅仅只论其表面与现象,而应保护童年,捍卫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的本质,完成电子媒介时代重建儿童文学的使命。从原始时期没有童年的概念一直到近代儿童观的初步成熟和童年概念的形成,童年本身是一个构建的过程,“童年的建构历程与现代儿童观的形成历程和儿童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童年的历史建构不只是儿童观转变的历史,而是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建构起来的,并以此确认作为文化主体的童年和作为权利主体的童年……儿童“包含着人类发展最高的可能性”,因此“关于孩子所做的以及对孩子做的工作始终关乎未来:怀着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的希望而工作”。
二
先看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重新构造了童年环境,童年的概念以及儿童的日常生活现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无可辩驳的”。娱乐、消费和去独创性作为电视文化的实质,“就像是一个霸权主义者,它强势地殖民到了社会现实的基本层面中”,改变了童年的生活状态:破坏童年的读写文化、危及了儿童教育并使之失去原有的效果,既影响了儿童的成长,又对童年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使“羞耻的概念被冲淡”、“礼仪的意义降低”、“好奇心失去存在依据”,从而使“童年的消失”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而网络文化中的童年境遇则并没有改善,“如果说,网络文化是一座花园的话,那么儿童既是网络文化的设计师和网络文化的参观者,同时也可能是这座花园的迷路者和彷徨者”。网络歌曲、网络游戏、网络交友和网络文学,以网络亚文化的形式影响着童年生活,有其积极意义,但对儿童成长的消极影响无法摆脱,特别是“网络黄色信息、网恋、网络色情犯罪和网瘾等对童年生态的破坏,对儿童教育的负面影响及其对儿童阅读的冲击”往往难于克服。
再看电子媒介时代的儿童文学。正如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阐述的,媒介的高度发达和普及造成了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侵蚀,小读者日益被卡通片、成人电视剧、MTV、网络小说所吸引,视听文化的易操作性、易选择性不可避免地抢走了小读者。电子媒介消解了文化的深度模式,解构了所有的文化秘密,系统完整的文化体系变成了纷飞的文化碎片。在电子传媒环境中长大的一代,普遍失去了政治热情,缺乏对人类和社会的文化关怀。平面化的电子媒介,用强大的、高密度的视听形象冲击人的感觉器官,使人来不及做出积极的反应,思维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这对人的想象力的开发无疑是一种桎梏。电子媒介及其与市场结合形成的消费文化连在一起,开始主宰着社会的一切,深刻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几乎所有的文学类型乃至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如何培养儿童的文化情怀,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次,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随着社会的转型也经历着自己的转型,特别是电子传媒中的色情和暴力对儿童的负面影响更是要解决的问题。有充分的个案事实证明,当今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未婚母亲数量增多、犯罪年龄呈低龄化倾向、恶性犯罪事件大幅度攀升,都与电子媒介的负面影响直接有关。正因为如此,儿童文学作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高科技撞了“腰”,“虽然尽可能地坚守着儿童文学本有的精神高度,但在商业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裹挟中,发生了种种变化”,出现了大批一味迎合电子媒体而失去自我、疏离儿童文学本位的作品。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儿童文学由于其生产和消费与商业文化结合、步入审美后现代性轨道和参与到全球化语境中等原因,发生了重要的艺术转型,对其文学特质、精神高度、艺术维度和民族特色等提出了新的挑战;二是与之相连,出现了在这个特定时期的一些特有的艺术表征:商业化写作、类型化写作、日常化叙事、娱乐化叙事。三是隐藏在这些艺术表征背后的,就是儿童文学创作精神的缺席:诗意危机使儿童文学变得干瘪、想象力匮乏使之走向平面化叙事、人文关怀缺席使作家淡忘责任与使命,带上“都市贵族化”倾向。种种这些,都在呼唤创作主体高扬儿童文学精神,找回电子媒介环境下儿童文学的艺术尺度,实现儿童文学的突围!
三
提出问题是一种敏锐,也是一种批判;是一种现实情怀,也是一种终极关怀,而其最终目标则是解决问题,在对现实的超越与重构中达至理想的彼岸。谭旭东提出了回归童年、再现童年和重建儿童文学这一具有未来高度的课题。“在被电视文化和网络文化包围而面临消失危险的童年的再现也必须从两个维度来切入,一个是从儿童的内部世界的呵护出发,即从维护童年性出发(童年性是儿童天生的);另一个是从儿童的外部世界的改造出发,即重塑童年文化(童年文化是成人给予的或塑造的)”。而维护童年性就要保持作为童年的本质的幼态持续性,坚守作为童年精神特征的幻想与梦想,并通过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等途径为儿童的成长注入活力,使其成长性具有现实的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对童年进行理想的文化设计,尽量建立起新的教育观点和模式,以抵消电子媒介给儿童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或倡导阅读型、学习型社会,优化儿童阅读环境,培育人文主义氛围,在理想与现实的交接点上重塑童年文化。在当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由于数字化媒介的强势覆盖,“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直观遮蔽沉思,快感冲击美感,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叙事。图像文化的视觉冲击不断挤压着文字阅读的市场空间,萎缩了文学消费的读者阵营,引导儿童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实现童年再现的重要方式,因为“优秀的儿童文学能再现童年世界,并将儿童带入他们真正认可的世界。而且儿童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他们就会建立对世界的真善美的信任感,因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逼真地重现了童年。”不管是顺乎儿童的天性来再现童年,还是通过外部文化的塑造来再现童年,都需要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因此,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中国儿童文学,不管是精神向度、写作姿态,还是美学追求和倡导新主流,都应该以重建为主题,以此捍卫童年、回归童年、优化童年生态、构建一个让儿童健康成长、滋养儿童心灵的精神家园,并张扬理论批评的文化功能,以推进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比如在“精神向度”上,“儿童文学为谁而写”?作者提出了“儿童是否喜欢能否成为儿童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或者是媒介形式,小说、新闻、电视剧、电影等等,若单单以受众是否喜欢来判定优劣,本身就太狭隘了。虽然说应该以受众、读者为本位,但作为唯一标准予以肯定是不可取的。现在的很多电视节目完全是以市场为主导而生产,缺乏丰富的文化内涵,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很难有真正的精品力作,正如旭东先生提到的,“色情图书儿童喜不喜欢呢?孩子肯定喜欢,但那就是好书了吗?”一部优秀的作品,无论是印刷的还是电子的,能拥有受众是一个原因,但有时候拥有受众也不是顷刻就能体现出来的,看看那些流传百世的名作,很多在作者生前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作品应该提高受众的鉴赏能力,特别是儿童文学更应如此,因为作为其读者对象的儿童年龄偏小,人生观、价值观处在成长过程之中,对美的鉴赏能力偏低,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不强,儿童文学有责任帮助他们提高审美能力以及认识社会和把握生活的能力。
四
生长在电子媒介蓬勃发展环境之下的一代,几乎难于离开电视和网络,对电子媒介有着难于摆脱的依赖,对其带来的利弊也有设身处地的认识,从小时候购买小人书,看花仙子,到看《快乐大本营》,再到网络世界的海量信息选取,在深深地感受到高科技所带来的快乐和便捷的同时,也会随着越来越宽广的海量信息而变得迷茫,不知所措,甚至麻木,加之电子媒介往往与影像连在一起,读图时代的到来让文本的阅读、体验成为一种奢侈,真像《娱乐至死》中所言一般,在这个电视娱乐时代,人们不需要思考了,也正如波兹曼所认为的,“童年是会随着电子媒介时代而消逝的”,虽不免悲观,但回到现实中,却是十分可怕的现象,值得正视。对此,新时代的儿童文学应该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与审美功能实现文化担当的使命:首先,应该给儿童一个干净纯粹的世界,即一个理想的世界。“儿童文学可以给儿童建立理想世界”,让儿童张扬想象力、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梦想里、满足其自我中心的思维逻辑和游戏精神,从而获得真、善、美的滋养,得到爱和智慧的力量,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和形成新的人格。具体而言,这种新人格的养成有两种重要表现,一是以儿童文学“建立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且和儿童的内心世界契合的‘第三世界’”。这个世界与童心世界相协调,是对儿童审美化人生的向往,是一个独特的儿童审美之境。儿童在这里舒展童心,远离成人的繁复事务,摆脱成人的功利化生活方式,感受创造的想象性力量,获得成长的教益。二是儿童文学构建的这个理想世界具有文化塑造力,让儿童得到生命的张扬,因而必定促进社会“新人类”的成长,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人口素质与生命质量。可以说,这一理想世界正是儿童文化诗学的创构目标!其次,儿童文学要以其特有的文化价值给这个消费主义盛行时代的儿童以精神的提升。儿童处于身心发育和精神成长阶段,儿童文学应从滋养儿童心灵、优化童年生态、支援儿童教育和培养儿童母语意识等方面为儿童成长提供条件,捍卫童年,关注未来。最后,儿童文学可能为成人保留一个美好的童年,引导其回归精神的家园。童年是每个人一生中最纯净无忧、天真烂漫的日子。而在电子媒介时代,工具理性剥离了人的灵与肉,物欲横流泯灭了求真爱美之心,而儿童文学以其独有的诗情画意和审美力量使成人回到儿童的梦想,再次体验童年的生活,在美好的回忆中与童年对话,感受纯洁和良知,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纯粹化,发现心灵中原型的童年,在对现实世界的抵制中建设文化理想。儿童文学若能在飞速发展的电子媒介时代担当起这样一种文化责任,美好的童年不仅不会消逝,而且会成为人生永恒的美好记忆。这样一种理念下的儿童文学,不仅能滋养儿童的心灵,提升儿童的精神,而且能让成年人实现自我的回归,找寻到生命的那片净土。
谭旭东是儿童文化的未来主义者,也是儿童文化诗学的理想主义者,他以批判的姿态面对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和儿童文学,抵制技术思维所带来的实用性价值,以救赎者的情怀呼唤童心的回归,寻找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突围之路,引领儿童文学走向文化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