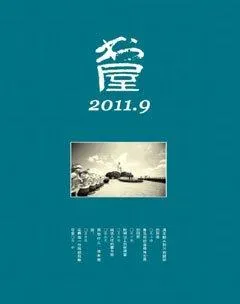陈丹青的鲁迅
2011-12-29艾华
书屋 2011年9期
一
2011年1月,《归国十年:油画速写》一书出版,只顾分身忙碌而厌恶各种身份的陈丹青,终于不再抵赖画家身份,但却继续自我调侃:“总算比较地像个画家模样了”;与此同时,《笑谈大先生:七讲鲁迅》一书也出版,在《序》中陈丹青坦言:自从公开讲过鲁迅后,近年竟不很经常念及老先生了——那么,在鲁迅其文其人面前,陈丹青是否会自嘲:总算比较地像个读者模样了?
读者和作者的关系,从来诡秘的。英国谚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法国的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前一句话说的是读者和文学人物的诡秘,后一句话说的是作者和文学人物的诡秘,如果用文学推理而不用科学推理,第三句“诡秘”的话也就出来了: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作者。
在陈丹青阅读并喜欢上鲁迅的时代,只有毛泽东和鲁迅的书被广泛阅读。这个问题在他学油画时同样遇到,就是他学油画是从画毛主席像开始的。在收入《荒废集》的《从毛泽东到董其昌》一文中,陈丹青这样回顾自己的油画生涯:从毛泽东那张脸一路画到董其昌的山水画,也就是从无处逃遁的“革命中国”一路画到自愿归属的“文化中国”。为了纪念和忘却自己曾经的被动,陈丹青后来主动画了一组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的肖像——模样和表情有“人”的生动,与“标准像”和“宣传画”大不一样了。
也许是为了与“标准像”和“宣传画”相区别,陈丹青将这组毛泽东肖像取名叫《毛润之》。“润之”是毛泽东的字,以字称人,当然是表示尊重的。当所画对象不再是政治脸谱,而是一个“人”的肖像时,陈丹青以画笔和画名消解了盲目崇拜、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并因此保持了一个画家自嘲式的自尊。
微妙的称呼,称呼的微妙——在第一次公开谈论无数人谈论过的鲁迅时,陈丹青一以贯之:笑谈大先生。“大先生”是鲁迅生前亲近者对他的称呼,陈丹青直接拿来,既表达着亲近之意,也暗藏着还原之愿——把身后还原到生前。死生相隔,时代相隔,陈丹青以“不断想念”建立起和鲁迅的“私人关系”,并且公开谈论这种私人关系,这大概与他把“毛泽东”画成“毛润之”一样,是试图在公私之间做一次清理。既然鲁迅被盖棺论定为“民族魂”,进而由文学家升格至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致本应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鲁迅的私人阅读,变成了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鲁迅的公共阅读,那么,叫他一声“大先生”,也许是由“公”入“私”的一个秘诀吧。
二
在“七讲鲁迅”之前,陈丹青写过一篇散文:《鲁迅的墓园》。这篇散文已有句子以“大先生”指代鲁迅,并已开始涉及鲁迅“入土”也难“为安”的问题——不过点到即止,并未深究——这是文体的限制,也是写作的自律。一篇不长的散文,是难以承载鲁迅身后漫长的“变形记”的;几处宕开的闲笔,倒是把这篇散文“闲”出了深长的意味。特别是结尾,陈丹青写到他小时候在鲁迅墓园所在地——虹口公园——玩耍,跟别的游人一样,他被危然对坐在湖边假石上的一对恋人吸引,但他的母亲叫他走开——别看,他们是瞎子。
写得真好。好在哪里?好在“他们是瞎子”。“瞎子”而“别看”,这种教养基于“能看”与“不能看”的不对等——这且不多说;单就文章而言,这一对瞎子的出现,一下就把鲁迅的墓园推到了远处和暗处——这样的“一笔宕开”,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一文中拿鲁迅的文章举过例并盛赞过的。
这篇以“瞎子”结尾但几乎全篇都在写“观看”的文章,在《笑谈大先生》一书中是作为附录收入的,全书读下来,这对“瞎子”简直把“七讲鲁迅”都一下宕开了。如果对照《序》中的闲话,则鲁迅的“入土”也难“为安”,相隔二十年的两种墓碑是最好的说明:1936年万国公墓的“鲁迅先生之墓”,是七岁的周海婴由许广平扶持着写成;1956年迁至虹口公园的“鲁迅先生之墓”,则是当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手书了。两相对照,鲁迅的身后事就这样由家事变成了国事。
然而对那两个瞎子而言,无论毛泽东手书的墓碑怎样金光闪闪,他们都看不见。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在的地方只是一个公园——哪怕公园里有鲁迅的墓园,鲁迅也不会打扰他们。公园就是公园:所有的游人自由而平等。
三
《文学与拯救》,是陈丹青受邀为纪念《狂人日记》问世九十周年而作的讲演;“七讲鲁迅”中,因“周年”受邀而讲的还有:为鲁迅逝世七十周年而作的《鲁迅是谁?》,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的《上海的选择》。七十、八十、九十,这些数字不能小看,因为它们背后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而答记者问式的《民国的文人》,陈丹青一开头就说:“我不是学者,居然一再谈论鲁迅,是为了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诸位同意鲁迅被扭曲,那就有可能同意:被扭曲的是我们自己。”
“被扭曲的是我们自己”?这是关于“我们”的话题,无数个“我”怎样变成了一个“我们”的话题。围绕这一话题,陈丹青的上述讲演所谈的,实际上是鲁迅的前后左右、上下周边——试图把鲁迅放回他的参照系,放回复杂的历史——因为随着鲁迅的符号化,历史也被简写了。这几篇讲演,把“我们”对鲁迅的公共阅读梳理出了前因和后果,而把鲁迅的身后对照到生前,是陈丹青惯常的谈法。
为了把曾经的公共阅读清理干净,陈丹青不得不谈“‘我们’的鲁迅”这一公共话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按照陈丹青的说法,这种变化“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我们’的鲁迅”将不再是一个公共话题。那时候,陈丹青一讲鲁迅的《笑谈大先生》、二讲鲁迅的《鲁迅与死亡》,也许会显出比其他各讲更大的价值;因为这两讲讨还出了阅读的私人性:“一讲”是以“几十年来不断想念”这种私人关系谈出的“私人意见”;“二讲”虽有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背景,但也是陈丹青自己想出的题目。
在这两次讲演中,陈丹青从公共话题中退开身,从公共阅读中掉过头,把自己还原成了一千个读者中的一个。既然只是一千个读者中的一个,话不妨直说,语不妨惊人——只要是“一个”读者,直面鲁迅其人其文,谁不会有自己的那么一点读后感呢?当陈丹青行使一个读者的权利,玩笑着谈“大先生”的“好看”和“好玩”,沉重着谈“鲁迅与死亡”这一黑暗话题,再怎样语出偏锋或者调子暗,都不过是一个读者的读后感。
陈丹青说话作文,本来一贯保持语气的弹性,词句间也留有余地——不是一根筋绷紧,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得紧张,但是上述两篇讲演,陈丹青分别在两处使用了两个“最”:一个是,“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一个是,“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陈丹青的这两个“最”,当然不求“同意”,当然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从最高意义上看“相貌”,从最高道德上看“异端”,透露的是陈丹青看鲁迅的角度。这是两个角度吗?不是,是一个角度,因为相貌便是人,人便是相貌——“天生是个异端”的鲁迅,“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
四
陈丹青“以貌取人”,这样说鲁迅的相貌:“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这一连串有节奏的形容词,把鲁迅的相貌勾勒出了丰富的层次,而这些层次显然是先天和后天共同塑造的结果。
一个人的相貌,先天的因素只能归于先天——俗话所说“爹妈给的”,而“爹妈”无从选择;后天的因素来自后天,那便多了去了:有形的无形的,主观的客观的——随着身心的成长和成熟,一个人不知不觉就拥有了自己的相貌,或者说,变成了他这个人。后天跟相貌的关系,带文艺腔的说法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来自世俗经验的说法是:老夫老妻,越长越像。这些说法,说的是心理对生理的影响,文化对面孔的塑造。
然而,陈丹青看到的鲁迅,并非活生生的鲁迅,而是隔着时代、隔着生死,看到的照片上的鲁迅,甚至是印刷品上的鲁迅——这是鲁迅本人吗?人物、人像,原件、复制品,在一个画家的眼中,它们的关系也许是诡秘的。陈丹青曾躲在纽约这个当代艺术之都,长期依据照片和图片作画,后来干脆摊开画册画静物,回国几年后又悄然对着书帖写生,用油画笔画着毛笔字——真迹的摹本?摹本的真迹?平面的立体?立体的平面?一个写实画家认真地玩着这样的图像游戏,也许是悟透了“画”的真与假,“观看”的虚无与实有?
猜测一个画家的视觉及其视觉思维,是费力不讨好的;不过陈丹青在访谈中说,“我第一次看到鲁迅照片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可是小孩子也会有判断”,这样的“见面”肯定奠定了他对鲁迅的看法——“好看”,多少年后他有机会公开谈论鲁迅,首先就说他“好看”。至于印刷品是否失真,照片毕竟只是二维,一个小孩还不懂得这些;纯真的眼睛没有偏见,但是有偏爱——“他八字胡一弄挺好看”,陈丹青如是说。而对于鲁迅身后由照片、速写、木刻、漫画等构成的图像效应,陈丹青是这样说的:“他的容颜在他陨灭后继续活在无数图像中,以至这些图像竟能以被任意引用的方式,继续捍卫他那张脸。”
“任意引用”,在鲁迅身后被符号化的过程中,的确屡见不鲜。但无论怎样变形、夸张、歪曲,鲁迅的形象都能穿透媒介扑面而来,并且穿透他身后的时代:“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陈丹青如是说,说他的“私人意见”。
五
陈丹青“七讲鲁迅”,第七讲终于讲到了他最熟悉的话题:鲁迅与美术。在陈丹青看来,美术,是认知鲁迅之为鲁迅的另一维度。陈丹青谈到鲁迅的丰富收藏和零星画论——“伟大的业余感”,谈到鲁迅的视觉敏感和版画趣味——“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谈到鲁迅从小迷恋绘画和至死还在倡导左翼木刻——这两点,与鲁迅相貌的后天塑造和身后的图像效应其实大有关系:
前一点,一点即破:一个童蒙时代就喜欢上绘画的人,无疑从小就多了一面可以照见自己的镜子——在经年的观看中,相貌因此得以微妙地塑造。比较一下周氏兄弟的相貌,如果说周树人比周作人更“好看”,那也许是因为周作人跟美术少有关系,而鲁迅跟美术关系很深,几乎沉湎和纠缠了一辈子;
后一点,陈丹青说到了的:“鲁迅死后,年轻左翼木刻家在延安和国统区继续创作了不少泼辣的作品,但渐渐成为政治宣传……”这种宣传延续久远,而“宣传画”中就包括了木刻的鲁迅图像;这些图像广为复制和传播,又不断变形和繁殖,活生生应验了鲁迅生前所看重的木刻的“大众性”。
观看鲁迅生前留下的照片和身后变形的图像,阅读鲁迅其人其文以及阅读“我们”对鲁迅的阅读,陈丹青心目中最终建立起的鲁迅形象,或许可以这样概括:好玩的异端,失败的英雄——他凝固在黑白照片上的相貌,经过时光与媒介的淘洗和注定的继续淘洗,“好看”并将继续“好看”。
所以,陈丹青的鲁迅,在最私人的意义上,是“一个”读者眼中的鲁迅,更是一个“画家”眼中的鲁迅。
当然,这也是一个读者的一点读后感。
(《笑谈大先生:七讲鲁迅》,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