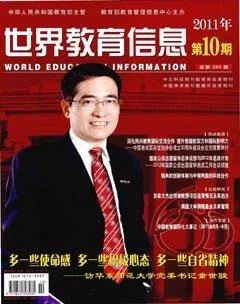民间协会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中的作用
2011-12-29熊耕
世界教育信息 2011年10期
研究型大学位于美国高校金字塔的顶端,是一个名校云集的群体,代表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在美国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德国大学的模式在新大陆落地生根,研究型大学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许多因素都对其产生了影响,其中民间协会对其发展的影响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的民间协会或理事会(associations or councils)主要是指高校或高校中的专业院所自愿组成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组织。这些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精英大学俱乐部”的美国大学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其62个成员中,除了2所加拿大大学以外,其余60所皆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它建立于1900年,几乎是伴随着美国研究型大学成长发展的全过程。除了这个联合会,研究型大学还根据本校的性质加入多个相应的协会组织。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戴维斯、欧文、洛杉矶、圣迭亚哥、圣塔芭芭拉分校都是美国教育协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的成员;同时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是私立院校组织——全国独立学院与大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的成员;加州大学的六个分校也都加入了全国州立大学与赠地学院协会。另外,研究型大学及其所属的专业学院都是经过认证的,而在美国进行认证的机构都是民间协会,研究型大学通过认证后就成为这些认证协会的会员。那么这些协会在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确定公认的标准,开展质量认证
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是高等教育协会产生的高峰期。许多协会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大学设立一定的规范和标准。美国大学联合会就是其中之一。在19世纪晚期,美国“学历工厂”四处泛滥,许多濒临倒闭的大学还在颁发博士学位。大学教育这种缺乏标准、混乱无序的发展状况影响了大学整体的学术质量,也伤害了美国大学的声誉。于是,1900年1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五所颁发博士学位的大学的校长写信邀请另外九所颁发博士学位大学的校长到芝加哥开会,共同讨论面对的问题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就是美国大学联合会。其最初的目标就是在研究生教育特别是高级学位要求方面建立一定的标准,一方面解决学生在不同的大学攻读学位时出现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统一的标准,“提升薄弱学校的质量水平,改善外国人对美国博士学位的看法”[1] 。1914年,美国大学联合会开始对全国的许多大学进行质量认证。这个任务主要由成员大学的研究生院的院长承担,他们广泛收集材料并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公布一份“联合会认可名单”,这份认可名单旨在向国外大学证明名单上大学的毕业生有资格开始研究生学习。这份名单在欧洲高等教育界非常有份量,列于该名单上的大学的质量得到了欧洲同行的认可。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开展认证一直是联合会的主要职能。美国大学联合会的质量标准及其认证过程,在整体上提升了美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国际声誉,对研究型大学群体的逐步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大学联合会后来停止了其认证活动,对研究型大学的认证早已由区域性和专业认证协会接替。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是在1929年就开始接受区域性认证协会——新英格兰地区大学与学院协会(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的认证。各种认证协会组织对研究型大学质量的保证和提高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研究型大学都是大学中的精英,对它们而言,通过认证自然不成问题。关键的是通过认证后,作为认证协会的成员,研究型大学要接受认证协会的长期引导和监督。它们每年要提交有关大学总体情况的年度报告,如果认证组织中相关的委员会特别要求,它们还要提供财政报告之类的专题报告。最为重要的是,研究型大学还要接受认证组织周期性的再认证,周期一般为5-10年不等。如果大学出现实质性变化或者其教育质量受到严重质疑,认证组织则有权打破这一时间周期,随时对其再认证。这一过程也要求大学进行严格自评。自评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是一次自我审视的过程,这种自我审视对于研究型大学定期调整自身、应对外界挑战、不断追求卓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自身的荣誉和地位以及在激烈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都重视这样的过程。认证协会对研究型大学最大的影响在于二者之间长期的互动关系可以避免研究型大学在通过认证之后一劳永逸的懈怠心理,促使其依照协会的标准框架长期关注质量问题,并不断地超越自己,追求卓越。因此,认证协会的周期性再认证可以说是促进美国研究型大学长期持续发展和提高的因素之一。
二、对研究型大学群体进行具体治理
民间协会对研究型大学群体的治理主要是以会员协商的形式,针对这一群体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由于是大学协商制定,因此大学一般也都自愿遵守。
二战后,随着大学科研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迅速提升,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日益增多,在这些合作当中,大学的科研人员则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由于大学和企业在根本目的和基本理念上的不同,许多大学科研又是由政府资助,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就出现了利益冲突。在这种利益关系中,科研人员作为大学的职员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早在1964年,美国教授协会和美国教育协会就发表了联合声明《防止政府资助的大学科研中的利益冲突》。该声明“强调了从大学到企业知识和技术转移的重要性,同时也特别强调大学建立规则和程序保护自身及科研的价值理念。”[2]这一声明至今仍是大学建立相关政策的基础。1978年,美国大学联合会、美国教育协会以及全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协会共同发表了《管理院校补偿费原则:教师从事资助性科研的政策》。1985年,美国大学联合会发表了《大学关于利益冲突和科研成果延迟公开的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为各个研究型大学制定、完善有关利益冲突的政策和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这不仅为大学正常的教育和科研活动提供了保证,而且还维护了大学的使命,捍卫了学术界的价值理念,促进了知识的自由流动和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技术转移和经济竞争力成为国家重点。大学科研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也再次引起了关注,1993年美国大学联合会发表了《处理大学科研中财政方面利益冲突的框架文件》。该文件的目的就是“为大学重新评估本校的利益冲突政策,特别是处理财政方面的利益冲突政策提供一个框架”。该文件认为“只要学术科研解决的是现实世界的问题,某种程度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冲突的程度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从而避免危及大学的目标和使命,保护公众和学生的投入,维系公众对学术活动的声誉”[3]。
20世纪80年代,研究型大学科研中欺骗行为较为严重。1988年,美国大学联合会、美国教育协会、全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协会和美国医学院协会等十来个组织联合制定并发布了《高校处理科研欺骗的政策和程序框架》。该框架认为“对教师科研行为负责的应该是大学而不是科研的资助者。为此,大学应该有责任建立一套公平的、切实可行且反应迅速的程序来处理违反规则的事件”[4]。框架首先明确界定了什么是科研欺骗,然后详尽列出了从开始质询到调查,再到申诉、审理以及最后处理的全部程序,并在每一个环节中都提出了对高校的要求和建议。这个框架对于研究型大学建立和完善处理科研欺骗的机制、减少科研中的不良行为、保证科研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该框架只是列出了一个良好机制所必备的主要元素和环节,这就为大学提供了一定的自主空间,使其可以根据现有规则和程序,寻求更适合校情、效率更高的机制。
研究生教育是研究型大学的另一个重心。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在全世界被公认为最好,但美国大学联合会认为“它仍是离完美甚远。只有不断自省自查,它才能不断地进步提高,才能保持住世界领先的地位。”[5]于是1998年,美国大学联合会针对研究生教育当时面对的批评“博士培养过量,专业狭窄,科研重于教学,利用学生达到学校的目的而不是为其提供良好的教育,导师指导不够,缺乏职业建议和求职帮助”等[6],建立了“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对其成员院校的研究生教育进行评估,而后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考察了国家、院校对研究生教育的观点以及专业情况,提出了有关研究生教育实践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几乎涉及研究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招生录取、学生资助、研究生课程、导师指导、就业指导及毕业、就业信息收集等。另外,报告还建议其成员大学建立博士专业评估机制,或者自我评估,或者外界评估,或者二者结合。这份报告促使研究型大学关注研究生教育中现存的问题,同时也为其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和要求,这对于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障和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间协会对研究型大学的治理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治理。这种非强制性的治理给研究型大学发挥自己个性以及自由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空间。这种宽松的空间对研究型大学来说至关重要。同时由于这种治理的主体——民间协会是大学自愿组织的联合体,因而这种治理是大学群体内部的自我治理。治理的内部性使得治理一来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二来也使治理对象容易接受且接受程度也较高。民间协会对研究型大学的治理可以说是一种点到为止、极为超脱的治理,既起了督促、建议和引导的作用,又不戕害其个性特点和自由发展。
三、参与联邦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
在西方政策科学论中,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民间协会被称为非官方或政府外部的政策主体。所谓政策主体“一般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组织。”[7]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到大学以及其中的教师、学生等的根本利益。民间协会作为政策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会尽力使有利的议案得以顺利通过,阻止不利的议案通过或者将不利程度降到最低。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利益的直接代表者首推美国大学联合会。联合会在1949年初将活动重心转向了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院校的校长其实早已直接参与到联邦决策中,但美国大学联合会作为一个大学的组织在1962年才正式开始对联邦政府的关系。这一年,联合会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常驻办公室,由一位执行秘书长主持工作。这个办公室并非是积极影响联邦的政策,而仅仅起到观察联邦政策动向的作用。1969年,联合会建立了联邦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ederal Relations),这个理事会主要由成员大学的行政人员,一般是副校长或研究生院院长构成,其职能主要是密切关注联邦事务。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入学人数的减少,联邦对于大学的研究经费也进行了削减,而科研比重较大的研究型大学比其他类型的大学更加依赖联邦的资助。联合会认识到在华盛顿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代表来特别关注研究型大学在联邦科研和研究生资助中的特别利益。1976年,联合会为驻华盛顿办公室聘任了一位全职主席,主要负责对联邦政府的关系。1978年秋,联合会又设置了一位执行主任,同时又设立了专业性的职员,负责有关理工科研究、生物研究、研究生教育以及人文学科等方面的联邦资金与政策方面事务[8] 。1982年,联合会与美国医学院协会联合建立了医学科研资金临时小组,其目的就是游说政府加大研究型大学医学科研方面的投入。
民间协会参与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方式主要包括公开致信行政和立法的首脑,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对其施加一定的影响。为了尽早地影响高等教育政策,有时在新一届政府尚未就任,民间协会就开始行动了。如1988年12月1日, 美国大学联合会在老布什当选总统但未就职之前,就给其办公室主任约翰· 萨努努(John H. Sununu)递交了一份题为《致新总统——关于科学、技术以及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建议》。该建议认为“对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资助是对国家安全和福利最核心的投资。”[9]该建议重点要求提高联邦支持科学的效率,在军事和民用研究投入上取得更好的平衡,加强行政部门与科学、技术和教育部门的合作。该建议提出负责协调政府政策的“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应该升级为总统助理,直接向总统汇报。美国大学联合会还指出:科技政策是由“管理与预算局”制定,有必要扩大其自治权并要求在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利用全国科学、工业以及教育组织各自的专长并加强合作。美国大学联合会还提出了28个相关政府机构职位的人选,认为这些都是受到工业界和学术界尊重的人士。这份推荐名单所涉及的职位包括五个部门的行政长官,这包括科学与技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