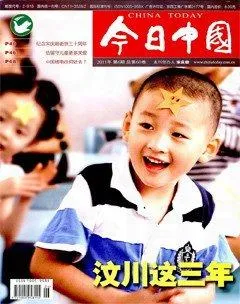孔子的“素面”与“反骨”
2011-12-29张涛
今日中国·中文版 2011年6期
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很重要,也很尴尬。
说孔子重要,是因为后人谈论中国文化,总离不开一个“儒”字。既说到“儒”,就离不开孔子。从儒家文化内部的演变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原儒”,还是后来标榜儒家文化理念却与“原儒”渐行渐远的理学家们,也都离不开孔子这位儒家文化的祖师爷。
说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尴尬,是因为孔子有心“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但却不为政治领袖和政治实践所接纳。尴尬的另一重是,从儒家文化发展出来的理学家们却是“存天理,灭人欲”,失去了人间烟火之气,与所谓的“原儒”大相径庭。一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其最初的文化精神特质渐行渐远,或许有时代与历史的诸多原因,但也不排除这种文化在起源时,就已经埋下了尴尬的种子。还有一层尴尬是,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虽然一直不为政治实践所接纳,却一直不断地被我们的政治实践所宣传。孔子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的“大人物”,这种文化位置几乎没有改变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学热”悄然兴起,几年之内便声势浩大起来。各种“大师班”、“国学班”方兴未艾。到了新世纪,“国学热”的声势依旧不衰。在“百家讲坛”上,于丹教授讲《论语》心得,这股浓浓的“心灵鸡汤”,再一次让孔子在大江南北“热”了一阵子。于丹之后,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以“丧家狗”来解读孔子,考据坚实,解读精细。尽管如此,李零教授的解读,仍遭到了诸多非议,认为他的解读误读了孔子,有辱孔子的形象。
薛仁明的《孔子随喜》,就其内容和风格而言,是介乎于“心得”和“学术”之间:一方面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谈对孔子其人其文的感受;又潜含理论、思想和历史的宏观背景。我以为薛仁明解读孔子其人其文的特点有二,一是“素面”孔子,二是言孔子有“反骨”。“素面”孔子是要穿透有关孔子形象的诸多迷障,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言孔子有“反骨”是价值判断,在温良恭俭让的背后,看到孔子的“激烈”。
薛仁明“素面”的孔子,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生活1W79SegI3gjxVmRK1FVuYe23es/3rHtzZD0+DZ6dsCI=的根基,为其解读孔子提供了别样的视角。薛仁明是台湾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台湾虽然也历经殖民统治和现代化的洗礼,但儒家文化依然是“台湾的根柢”,在都市的喧嚣与光怪陆离之外,日常的台湾依旧是“温良恭俭让”。文化的传承在台湾人身上并没有过明显的断裂,儒家文化是其日常生活的基调与气息。有了这样的背景和经验,解读起孔子,可能就会更有切近之感,更有“人间烟火”味。
在薛仁明看来,“风”、“悦”构成了孔子的“素面”。孔子不仅可以“志于道”,而且可以“兴于诗”。“志于道”是孔子严肃端庄的一面,承继文明,教书育人;“兴于诗”是孔子活泼灵动的一面,“感而遂通”、“闻歌起舞”。这样一来,孔子的面目就鲜活起来了。孔子向来是礼乐并举,丝毫没有后世理学家的“道学之气”,“他的世界,没有道学家与世人那一道道阻隔的高墙”。
薛仁明笔下的孔子,其人其文,生气淋漓,个性彰显,嬉笑怒骂,师生情谊,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样的孔子形象,是否与我们阅读、理解的孔子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解读孔子的“别开生面”。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消息,孔子像被请出了天安门广场。这一进一出,再次印证了孔子的重要与尴尬。哪一天,除却了这层“重要与尴尬”,或许我们才能真的理解孔